第八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作家專訪: 楊慶祥:“我理想的文學(xué)批評是在互動(dòng)中完成一種精神探險(xiǎn)”

楊慶祥
康春華:楊老師,首先向您問好!您在授課和學(xué)術(shù)研究之余,也堅(jiān)守在文學(xué)批評的一線,對新作家、新文本和新現(xiàn)象都有自己的觀察。想問問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狀態(tài),在繁忙的教學(xué)、學(xué)術(shù)寫作過程中,您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深度的思考和高效的時(shí)間管理的?有什么心得或者秘訣嗎?
楊慶祥:目前的工作狀況還是您提到的幾個(gè)方面,一是大量的閱讀。不僅僅是當(dāng)代的作家作品,更多是人文社科的各種著作,我的觀點(diǎn)是,功夫在詩外,只有大量的“非專業(yè)閱讀”才能保持良好的專業(yè)判斷。二是教學(xué)科研工作。每年會(huì)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一門課,研究生的課壓力比較大,因?yàn)槲也辉敢庵v重復(fù)的內(nèi)容,所以每年都要更新教案,當(dāng)然教學(xué)相長,我很多的學(xué)術(shù)思考也是從教學(xué)中獲得的。三是現(xiàn)場批評。需要參加很多作家作品研討會(huì)、新書發(fā)布會(huì)、文學(xué)評審評獎(jiǎng)等等,這些構(gòu)成了當(dāng)代文學(xué)生活的一部分,有些當(dāng)然會(huì)成為過眼云煙,有些卻會(huì)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參與現(xiàn)場”是當(dāng)代文學(xué)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四是一些日常的事務(wù),比如大學(xué)里的一些管理工作,這幾年占據(jù)了我大量的時(shí)間,我記得有一次為了處理一件突發(fā)事件,我從早上8點(diǎn)開始打電話,一直打到晚上11點(diǎn)多,吃飯的時(shí)候都是邊吃邊說,最后幾乎累癱了。所以并沒有你說的心得或者秘訣,不過是勉力而為。據(jù)我了解,我這個(gè)年齡段的同行們大都如此。我的一個(gè)基本原則是盡量少參加飯局——不過跟朋友吃飯有時(shí)候是很愉快的事情,難以抵抗誘惑;另外一點(diǎn)就是,我基本不熬夜,工作干不完就等明天,反正工作永遠(yuǎn)都干不完,不著急那么一時(shí)。這也造成一個(gè)后果,就是拖稿或者拒稿也會(huì)比較頻繁——天下好文章那么多,不差我這一篇!(這里必須有畫外音:謝謝師友們的寬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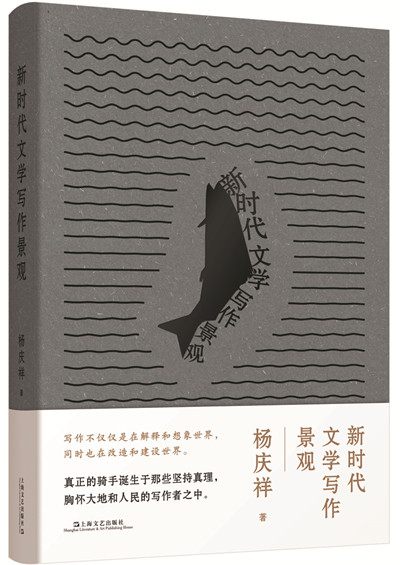
康春華:恭喜您的《新時(shí)代文學(xué)寫作景觀》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理論評論獎(jiǎng)。這本書既有您近幾年對文學(xué)熱點(diǎn)(比如青年創(chuàng)作、科幻文學(xué)、非虛構(gòu)討論、新南方寫作等)的關(guān)注與回應(yīng),也有“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評論,確實(shí)構(gòu)成了一種“新時(shí)代的文學(xué)寫作景觀”。您當(dāng)前的閱讀趣味、研究熱點(diǎn)和理論興趣在哪些方面?
楊慶祥:在研究上我是一個(gè)不太“專一”的人,我?guī)缀跏翘烊慌懦獬蔀橐幻皩<摇保矣X得這一標(biāo)簽是技術(shù)思維泛化的結(jié)果,一個(gè)真正的“人文主義者”應(yīng)該有更縱深的精神空間、更復(fù)雜的思考進(jìn)路和更綜合的表達(dá)形式。
我曾經(jīng)對科幻文學(xué)感興趣,因?yàn)槠鋾r(shí)我覺得它提供了一種方法論,但我現(xiàn)在認(rèn)為我高估了這種方法論;我也關(guān)注過人工智能,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在哲學(xué)上并沒有提供足夠新鮮的東西;我提出過“80后,怎么辦”“新傷痕文學(xué)”“新南方寫作”等等話題,對青年寫作、元宇宙都寫過相關(guān)的文章。我的閱讀趣味和理論興趣在不停地變化,所以研究關(guān)注的點(diǎn)也一直在發(fā)生變化,但不變的是我對“當(dāng)下”和“變化”的興趣,一成不變是多么可怕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千變?nèi)f化才會(huì)有大千世界。
康春華:我注意到,您在這本書中對近來廣泛被討論的“文學(xué)破圈”問題作了回應(yīng),不過這種“破”是針對僵化的、教條的純文學(xué)概念的“脹破”,比如您談到在虛構(gòu)文學(xué)發(fā)展演變譜系里“非虛構(gòu)”的重要價(jià)值、科幻文學(xué)因其獨(dú)特的“越界性”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體裁”,比如青年寫作在何種坐標(biāo)系里對當(dāng)代文學(xué)經(jīng)典化具有價(jià)值意義等,梳理了近十年來文學(xué)發(fā)展的過剩與匱乏狀態(tài)。從您的學(xué)術(shù)文章中能感受到鮮明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從何而來?您的批評觀或者說您認(rèn)為理想的文學(xué)批評是怎樣的?
楊慶祥:問題意識從何而來?我好像沒有特別認(rèn)真地思考過這個(gè)問題,在指導(dǎo)學(xué)生寫論文的時(shí)候倒也是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問題意識,但對它的發(fā)生機(jī)制卻沒有系統(tǒng)性地思考,您的這個(gè)提問對我是一個(gè)很好的提醒。我想這其中大概會(huì)有這么幾點(diǎn)值得重視:第一是敏感性。對一個(gè)現(xiàn)象、一個(gè)文本要有足夠的敏感,這種敏感甚至帶有一點(diǎn)玄學(xué)色彩,或許可以說是一種直覺?我覺得這是一個(gè)人文知識者必須具備的一種天賦。第二是具體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大而化之,用一種套路去討論各種問題,這是目前知識界的通病,結(jié)果就是千篇一律,空話連篇。第三是歷史感。很多人以為歷史感就是去研究過去的資料或者“死去的人”,且美其名曰“學(xué)問”,實(shí)際上,所有不能通向當(dāng)下、不能與當(dāng)下對話的“歷史”都不是“歷史”,也無法建立起歷史感。將當(dāng)下歷史化與將歷史當(dāng)下化是一個(gè)辯證互動(dòng)的過程,問題意識往往在這個(gè)過程中浮現(xiàn)出來。我的概括肯定不全面,但目前想起來的就這幾點(diǎn)。
至于理想的文學(xué)批評,倒是常常被問起,也發(fā)表過一些言論,估計(jì)也有前后不一的地方。我理想的文學(xué)批評或者說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就是說自己的話,呈現(xiàn)自己的問題和思考,我對闡釋某部作品不感興趣,作家在這一點(diǎn)上的發(fā)言權(quán)遠(yuǎn)遠(yuǎn)超過批評家。我要闡釋的是我自己對世界、對文學(xué)的理解和關(guān)切,作家作品是案例,是對話的對象,我們在互動(dòng)中完成一種精神探險(xiǎn)——前提是雙方都有足夠的精神能量。
康春華:我個(gè)人特別喜歡您《社會(huì)問題與文學(xué)想象——從1980年代到當(dāng)下》這部評論集,代后記中形容那種“照亮靈魂與精神”的感覺、“在自己身上終結(jié)90年代”等論述因其切身性而顯得尤為吸引人。這部評論集不僅清晰地表現(xiàn)了您從事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研究的起點(diǎn)與原點(diǎn),也展現(xiàn)了您學(xué)術(shù)軌跡之轍痕:從“80后寫作”到對泛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現(xiàn)場的觀察,從對90年代文學(xué)的再思考到重建21世紀(jì)文學(xué)寫作的整體語境。在“十年”這樣一個(gè)節(jié)點(diǎn)上,您對自己的學(xué)術(shù)道路有怎樣的回望和總結(jié)?
楊慶祥:嚴(yán)格來說我從2007年左右,當(dāng)時(shí)我在讀博士,開始進(jìn)入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現(xiàn)場并從事相關(guān)工作,算起來已經(jīng)快15年了。不過十年也好,15年也罷,在歷史中都不過一瞬。小時(shí)候讀武俠小說,讀到少年墜下懸崖大難不死修得絕世武功十年后重出江湖,覺得十年是漫長的時(shí)間之旅,而在真實(shí)的個(gè)人生活中,十年也不過彈指揮間。我的意思是,“十年”或許并非節(jié)點(diǎn),也難以進(jìn)行總結(jié)和展望,誰在歷史里不是隨波逐流?如果非要回望,或許海子的幾句詩比較切合我的心情:“面對大河我無限慚愧,我年華虛度,空有一身疲倦”。我現(xiàn)在不太敢讀我十年前的文字,覺得不忍卒讀。這也好,說明我的審美一直在更新。
康春華:您在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任教,在文學(xué)教育與文學(xué)人才培養(yǎng)方面有很多舉措,包括在人大文學(xué)院聯(lián)合課堂主持了多期讀書會(huì),這種對于具體的、新鮮的文本的研討操練,讓一批青年作家得以清晰顯見,也向文學(xué)界輸送了不少青年批評與研究人才。您關(guān)于文學(xué)教育的主張是怎樣的?您認(rèn)為當(dāng)下的社會(huì)生態(tài)需要怎樣的文學(xué)專業(yè)人才?
楊慶祥:我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第二志愿才是文學(xué)。但冥冥之中還是和文學(xué)走到了一起。無論是法律還是文學(xué),在我看來都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所有的人文教育都應(yīng)該是一種“養(yǎng)成”的教育而不是一種“灌輸”的教育,讓人在這一過程中覺醒、成為自己、發(fā)現(xiàn)世界是這一養(yǎng)成教育的核心要義。我個(gè)人在大學(xué)的教學(xué)都以這一要義為目標(biāo),當(dāng)然,大學(xué)的教育是系統(tǒng)性的,一個(gè)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好在大學(xué)有龐大的教師群體,可以以各自的智慧來點(diǎn)燃薪火。
職業(yè)院校或者工程院校當(dāng)然應(yīng)該培養(yǎng)更多的技術(shù)意義上的“專業(yè)人才”,我們的高等教育在這一塊還有待發(fā)展,而且這應(yīng)該是未來的一個(gè)大趨勢。但應(yīng)該還有另外一類“人才”養(yǎng)成,不需要緊跟行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也無需考慮市場的需求和就業(yè)率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他們以思考、批判和智性為生命之根底。當(dāng)然,如果我們的“文學(xué)人才”既能滿足行業(yè)的需要,同時(shí)又擁有深切的人文視野,那就太完美了。
- 竺祖慈:我對譯事的基本態(tài)度就是“老實(shí)”二字[2022-11-08]
- 今日批評家 | 李音:外套舊了,只有破洞是新的[2022-11-08]
- “詩歌是我的一個(gè)幻象”[2022-11-08]
- 今日批評家 | 康凌:不寫也可以[2022-11-04]
- 重建批評的尊嚴(yán)[2022-11-03]
- 許小凡: 琢磨翻譯是件快樂的事[2022-11-02]
- 楊鐵軍:翻譯是一項(xiàng)拓寬視野、錘煉語言的事業(yè)[2022-11-01]
- 金春平:意義的延續(xù)與經(jīng)典的準(zhǔn)備[2022-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