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縣小說(shuō)家孫一圣:我怕自己的小說(shuō)會(huì)速朽
曹縣火起來(lái)的那天,曹縣人孫一圣正在曹縣。但是直到現(xiàn)在孫一圣依舊沒(méi)弄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gè)在他看來(lái)平平無(wú)奇,又再熟悉不過(guò)的縣城,會(huì)成為眾人關(guān)注的對(duì)象。
“山東菏澤曹縣 666 我們勒寶貝”,隨著一位短視頻博主帶著濃重山東口音辨識(shí)度的口音,讓曹縣成為了全網(wǎng)揶揄的對(duì)象。
互聯(lián)網(wǎng)從來(lái)不缺少狂歡,網(wǎng)民總是在類(lèi)似的情況下發(fā)揮強(qiáng)大的創(chuàng)作力,沒(méi)過(guò)多久:“曹縣,中國(guó)第一縣。俗話說(shuō)寧要曹縣一張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山東不能失去曹縣,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紐約素來(lái)享有西方小曹縣的美稱,近些年倒也能稍微和曹縣相比較一下。”這樣的話語(yǔ)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夜間已經(jīng)鋪天蓋地。
從此,孫一圣從一位山東作家變成了曹縣作家。他愛(ài)惜自己的羽毛,沒(méi)有在任何宣傳和封面上出現(xiàn)曹縣的特征,他想讓文學(xué)的歸文學(xué),讀者是因?yàn)樽约旱男≌f(shuō)好看才關(guān)注到他,而不是因?yàn)樗遣芸h人。在此之前,孫一圣介紹自己的時(shí)候,都只說(shuō)是山東人,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觀看對(duì)象后,與新朋友介紹起自己,孫一圣改口,就直接說(shuō)自己是曹縣人。聽(tīng)到這兩個(gè)字,對(duì)方往往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臉上露出意味深長(zhǎng)的微笑,回答說(shuō):“我知道,我知道”。
就在曹縣火起來(lái)的這一年,孫一圣出版了自己的新書(shū)《夜游神》,獲得了關(guān)注,這也許是某種巧合。在許子?xùn)|看來(lái),從上世紀(jì) 80 年代開(kāi)始以余華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占據(jù)了中國(guó)文壇的絕對(duì)主導(dǎo),他們直到現(xiàn)在依舊擁有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能力,新作頻出。對(duì)于年輕一代的作家而言,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想被人知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夜游神》的出現(xiàn),讓孫一圣站在焦點(diǎn)的位置上,獲得了公眾的認(rèn)知,開(kāi)始有文學(xué)期刊跟他約稿,他有的時(shí)候也沒(méi)什么時(shí)間寫(xiě),有的就先應(yīng)許了下來(lái)。這是一本中短篇小說(shuō)集,孫一圣大多以“我”的第一人稱展開(kāi)敘事,故事有的是回鄉(xiāng)過(guò)年的中年人,有的是愛(ài)上老師的高中生,也有在奇妙的契機(jī)下發(fā)現(xiàn)彼此真實(shí)情感狀態(tài)的夫妻。在這些故事里,曹縣或是終點(diǎn),或是起點(diǎn),都成為故事重要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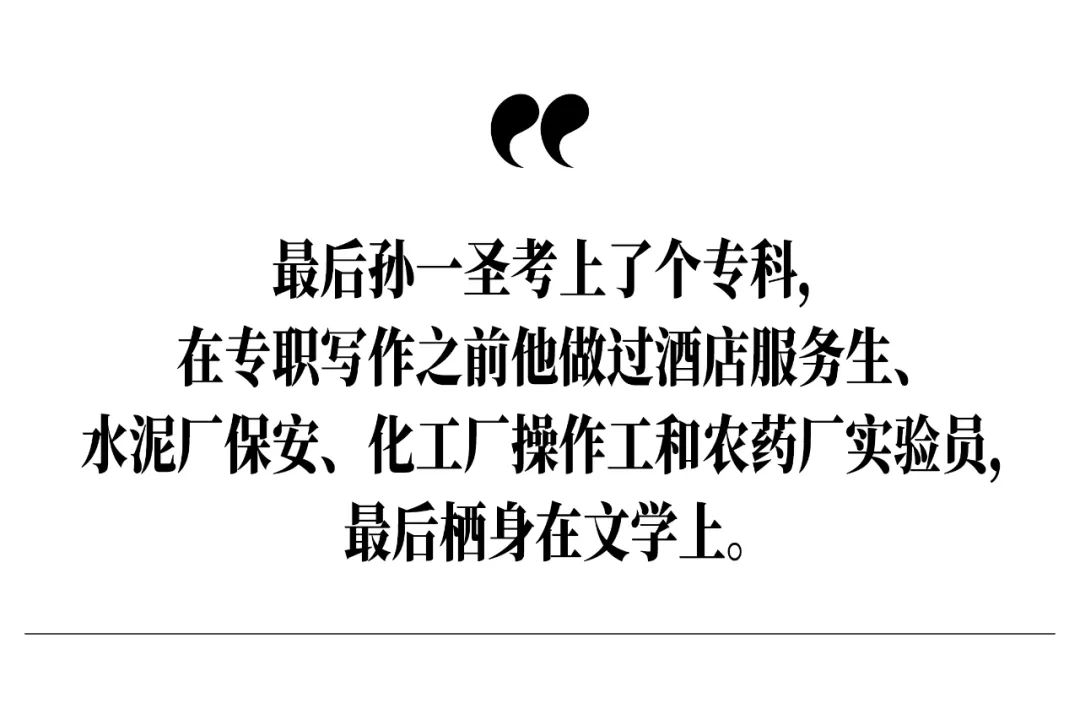
曹縣火起來(lái)的這天孫一圣正好因?yàn)槭虑榛氐搅死霞遥S著高鐵網(wǎng)路的建立,北京和曹縣的物理距離被縮短了。在火起來(lái)的當(dāng)天晚上,孫一圣在縣城里走,聽(tīng)到鄰居喊:“曹縣火啦!”孫一圣以為是誰(shuí)家著火了,沒(méi)當(dāng)個(gè)事兒,也沒(méi)過(guò)多回復(fù)即刻發(fā)來(lái)消息的朋友,直到全網(wǎng)陷入狂歡。
即便已經(jīng)在北京生活多年,但是孫一圣身上還是逃脫不掉故鄉(xiāng)對(duì)他的影響,一張嘴還是能聽(tīng)得出他是個(gè)山東人。而山東的另一個(gè)特征:高考競(jìng)爭(zhēng)激烈,也出現(xiàn)在孫一圣的身上,他按照父親的安排,老老實(shí)實(shí)地參加了四次高考,復(fù)讀、高考,再?gòu)?fù)讀、再高考。他把這段故事,不那么“還原”地寫(xiě)了下來(lái),成為了他的第一部長(zhǎng)篇作品《必見(jiàn)遼闊之地》。
“這是一本年輕氣盛的小說(shuō)”,孫一圣這么描述他的第一部長(zhǎng)篇,里面有死亡、情欲和年輕人們對(duì)未來(lái)的向往,他說(shuō)這是一篇語(yǔ)言帶著情節(jié)走的作品,可能和大眾之間有點(diǎn)距離。
余華看了《必見(jiàn)遼闊之地》,說(shuō)這是一本“突兀”的作品,孫一圣一開(kāi)始也沒(méi)弄清楚“突兀”這個(gè)詞是什么意思,直到他把自己的小說(shuō)重新回頭看了一遍,才發(fā)現(xiàn)確如余華所說(shuō),這個(gè)故事多少有點(diǎn)跳,在前三分之一的部分讀者們可能跟不上故事的節(jié)奏。孫一圣在故事里加入了豐沛的想象力,語(yǔ)言像瀑布一樣傾瀉下來(lái),情節(jié)成為了語(yǔ)言的注腳。
最后孫一圣考上了個(gè)專(zhuān)科,在專(zhuān)職寫(xiě)作之前他做過(guò)酒店服務(wù)生、水泥廠保安、化工廠操作工和農(nóng)藥廠實(shí)驗(yàn)員,最后棲身在文學(xué)上。
直到今天他的父親還是在催著他專(zhuān)升本,父親還在為孫一圣沒(méi)考上個(gè)本科而遺憾,甚至瞞著他報(bào)了名,考點(diǎn)在老家。孫一圣想不明白,自己為什么不能在北京考呢?而這一切,都是發(fā)生在父親知道他已經(jīng)成了寫(xiě)小說(shuō)的,還出了幾本書(shū)的情況下。孫一圣說(shuō),自己的父親其實(shí)一直都是個(gè)文學(xué)青年,之前還寫(xiě)詩(shī)。
孫一圣一直住在北京十里堡附近,這是一個(gè)乍看上去奇怪的站名,像是一個(gè)鄉(xiāng)鎮(zhèn)的名字,但它就這樣兀自地出現(xiàn)在北京地鐵線路圖上成為了一站。在十里堡, 他寫(xiě)完了至今三分之二的作品,每次寫(xiě)完都會(huì)在最后標(biāo)上日期,和“寫(xiě)于北京十里堡”。
孫一圣在寫(xiě)兩本新長(zhǎng)篇,“都沒(méi)有《必見(jiàn)遼闊之地》那么跳了”,在他看來(lái),文學(xué)寫(xiě)的都是十分之一的生活,剩下的十分之九都被排除在外。完成了《必見(jiàn)遼闊之地》后,孫一圣在寫(xiě)兩個(gè)新長(zhǎng)篇,一本快完成了,另一本還不知道。沒(méi)有完成的那本寫(xiě)的就是被文學(xué)忽略的、十分之九的生活。
他想要完成這樣的一個(gè)作品,篇幅是沒(méi)有上限的。孫一圣喜歡《追憶似水年華》,覺(jué)得這就是他想寫(xiě)的東西,他以為還要等很多年才會(huì)開(kāi)始寫(xiě)這樣一部漫長(zhǎng)的小說(shuō),沒(méi)想到今年過(guò)早地開(kāi)始了。至于什么時(shí)候能完成,孫一圣說(shuō):“普魯斯特不也是用了一輩子才寫(xiě)了七本嗎?”
但唯一確定的是,這位出生在曹縣的作家,不會(huì)寫(xiě)一個(gè)曹縣火起來(lái)之后的故事,“我怕自己的小說(shuō)會(huì)速朽”,孫一圣說(shuō)。
以下是我們與孫一圣的對(duì)話:
《WSJ.》:作為自己的第一部長(zhǎng)篇,《必見(jiàn)遼闊之地》呈現(xiàn)出跟之前的《夜游神》不一樣的語(yǔ)言風(fēng)格,它更先鋒,為什么會(huì)呈現(xiàn)這樣的差異?
孫一圣 :《必見(jiàn)遼闊之地》這個(gè)小說(shuō)是五年前寫(xiě)完的。那時(shí)候還處在剛擺脫練習(xí)寫(xiě)小說(shuō)的階段,與現(xiàn)在的語(yǔ)言風(fēng)格也有很大區(qū)別,算是《你家有龍多少回》和《夜游神》之間的一個(gè)過(guò)渡期。寫(xiě)《夜游神》的時(shí)候我是在克制地寫(xiě)一個(gè)故事,寫(xiě)生活剖面的一些情節(jié)和場(chǎng)景,這也決定了《夜游神》相對(duì)比較好讀一些。而《必見(jiàn)遼闊之地》的情節(jié)和故事是跟著語(yǔ)言走的,不是故事帶著語(yǔ)言走的。

《必見(jiàn)遼闊之地》是孫一圣的第一部長(zhǎng)篇。
《WSJ.》:你說(shuō)在這部長(zhǎng)篇里可能是語(yǔ)言帶著情節(jié)走,語(yǔ)言是位居第一位,而情節(jié)是第二位的嗎?
孫一圣 :對(duì),寫(xiě)的時(shí)候是這樣的感覺(jué)。我自己的感受,《百年孤獨(dú)》也是語(yǔ)言帶著情節(jié)走的,一種語(yǔ)言的瀑布拽著情節(jié)向前跑。不過(guò)我的長(zhǎng)篇是一種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情節(jié),但語(yǔ)言比較靈活,有時(shí)會(huì)有點(diǎn)幾乎跳脫現(xiàn)實(shí)邊緣的感覺(jué),所以稍微有一點(diǎn)點(diǎn)超現(xiàn)實(shí)的感覺(jué),但這只是語(yǔ)言帶來(lái)的一種迷幻效果,故事上我已經(jīng)盡量往更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方向傾斜了。
《WSJ.》:你是在逆反傳統(tǒng)意義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嗎?還是你覺(jué)得現(xiàn)實(shí)生活就是找不到頭緒的,采用這樣的文字風(fēng)格是應(yīng)當(dāng)?shù)模?/span>
孫一圣 :我其實(shí)也沒(méi)有說(shuō)要逆反,主要可能跟我最初的閱讀趣味有關(guān)。高中時(shí)我就接觸了先鋒派余華、格非、蘇童他們的小說(shuō),余華在《活著》之前,他的短篇小說(shuō)比如《偶然事件》《現(xiàn)實(shí)一種》《我沒(méi)有自己的名字》,還有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妻妾成群》在語(yǔ)言上也都是字斟句酌的。這些在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是比較不太好讀的小說(shuō)。
這批作家后面轉(zhuǎn)向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寫(xiě)作,不是他們不對(duì)語(yǔ)言不考究了,而是已經(jīng)內(nèi)化了語(yǔ)言,到他們開(kāi)始寫(xiě)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比如余華寫(xiě)《活著》的時(shí)候,即使很樸素的語(yǔ)言,很簡(jiǎn)單的句子,也是現(xiàn)代主義的風(fēng)格,是把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內(nèi)化后產(chǎn)生的句子和講故事的方式,總體來(lái)說(shuō)更平實(shí)有力。
《必見(jiàn)遼闊之地》就是年輕的小說(shuō),年輕的故事。不必到我年老,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寫(xiě)不出這樣的故事和小說(shuō)了,對(duì)這些事情不感興趣了,已經(jīng)沒(méi)有這樣的欲望和蓬勃的想象了。就語(yǔ)言來(lái)講,以后我也不會(huì)寫(xiě)這樣錙銖必較的語(yǔ)言了,這將是最后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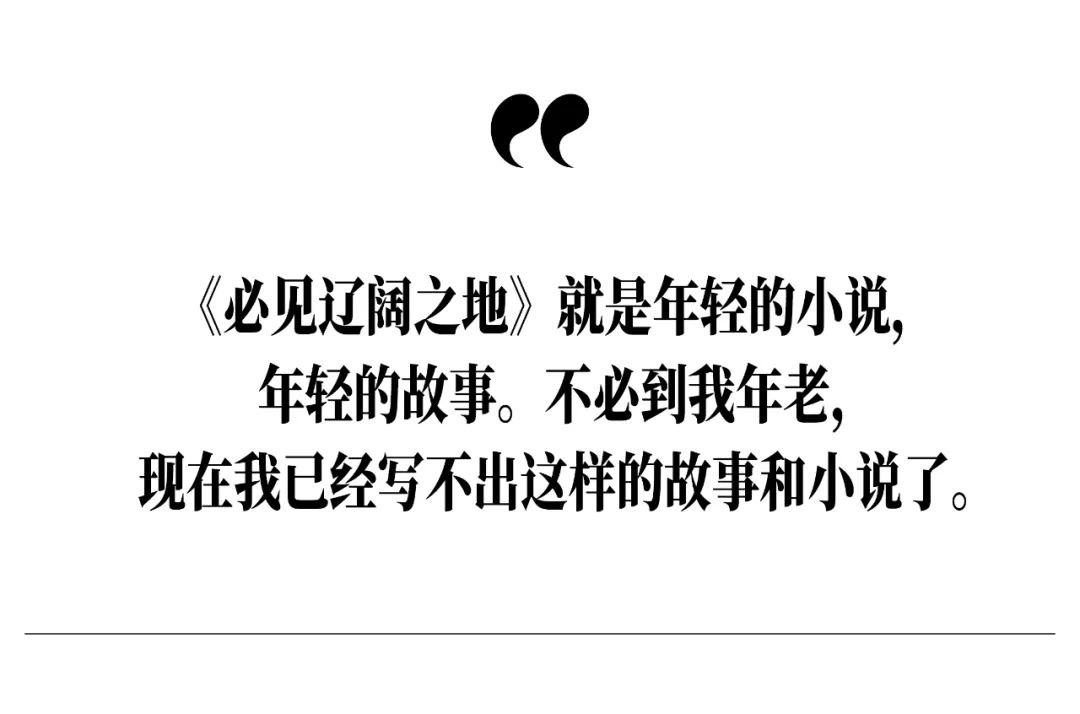
《WSJ.》:余華評(píng)價(jià)這部作品說(shuō),你將突兀演化成了風(fēng)格,以一種三級(jí)跳的形式組成了故事情節(jié)。你怎么看他的這種評(píng)價(jià)?你覺(jué)得現(xiàn)實(shí)生活是秩序井然的嗎?或者就是跳脫的?
孫一圣 :我非常喜歡這一段推薦語(yǔ),不但因?yàn)閬?lái)自我寫(xiě)作偶像的評(píng)價(jià),更因?yàn)檫@段話像是給這本書(shū)定了調(diào),準(zhǔn)確概括了這本書(shū)的風(fēng)格。起初,可能因?yàn)檫@部小說(shuō)寫(xiě)完很久了,我?guī)缀跬袅饲楣?jié)。因此,一開(kāi)始我沒(méi)太能 get 到“突兀”這個(gè)詞,當(dāng)我重新看了一遍小說(shuō),才理解到這個(gè)詞的貼切。
我在寫(xiě)這本書(shū)的過(guò)程中,修改了許多遍,已經(jīng)對(duì)語(yǔ)言風(fēng)格和情節(jié)走向很熟悉了,以至于讓我有種錯(cuò)覺(jué),覺(jué)得整體非常順滑。當(dāng)這本書(shū)面世后,有的讀者說(shuō),看前面 1/3 會(huì)有些跳躍,但是,當(dāng)進(jìn)入狀態(tài)以后,又都習(xí)慣了這樣的表達(dá)方式,直到讀完整部書(shū),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覺(jué),并且已經(jīng)把這種突兀消化掉了。這些反饋,也讓我再一次深入理解了余華老師推薦語(yǔ)里“將突兀演繹成了風(fēng)格”這句話的意思。
《WSJ.》:你如何看待文學(xué)作品中的秩序感?讀者們會(huì)天然地喜歡那種有秩序感的作品嗎?
孫一圣 :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有一個(gè)具體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樣的故事,從頭講到尾,有開(kāi)頭,有結(jié)尾,有高潮,有起伏,這樣的小說(shuō)是作家經(jīng)過(guò)修改出來(lái)的。它有邏輯,講因果。其實(shí)我們現(xiàn)實(shí)的生活不是秩序井然的,只有一個(gè)東西是有秩序的,那就是一天一天的重復(fù)感,而時(shí)間則是一天一天過(guò)的。
如果沒(méi)有一個(gè)衰老的過(guò)程,我們其實(shí)都相當(dāng)于在經(jīng)歷一個(gè)又一個(gè)重復(fù)的一天。有的時(shí)候生活就跟我們玩撲克牌一樣,過(guò)的就是一個(gè)洗完牌后秩序雜亂的人生。如果沒(méi)有衰老的自然更迭作為坐標(biāo),我們很難找到其中的秩序。
小說(shuō)如果寫(xiě)一個(gè)人的一生,主要是寫(xiě)這個(gè)人一生中比較重大的事件,比如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有孩子了,寫(xiě)了一個(gè)人的一輩子,只是寫(xiě)重要的事件和人生的轉(zhuǎn)折點(diǎn)。
其實(shí)小說(shuō)寫(xiě)出來(lái)的是十分之一的人生,忽略的則是十分之九的普通生活。我很想寫(xiě)那種十分之九的小說(shuō),就是沒(méi)有重大事件,把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者想法,從身邊或者心靈深處捕捉到。我想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就是我想學(xué)習(xí)的范本。不過(guò),一旦以這樣的想法來(lái)寫(xiě)一部小說(shuō)的話,這個(gè)小說(shuō)必然非常長(zhǎng),可能保底也 100 萬(wàn)字。這也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不可能是一兩年之內(nèi)就能寫(xiě)出來(lái)的,普魯斯特用了一輩子也才寫(xiě)出了他的七卷本嘛。
我以為會(huì)拖好多年才會(huì)開(kāi)始寫(xiě)這樣一部小說(shuō),很意外我已經(jīng)過(guò)早地開(kāi)始了這個(gè)漫長(zhǎng)的寫(xiě)作計(jì)劃,這真的是一部沒(méi)有盡頭的小說(shuō)。如果說(shuō)從篇幅上接近《追憶逝水年華》的話,那么創(chuàng)作心理上更接近卡夫卡的思考(不是卡夫卡表面上呈現(xiàn)出來(lái)的變異)。簡(jiǎn)單點(diǎn)說(shuō),這可能是用一種卡夫卡的創(chuàng)作方法來(lái)寫(xiě)那種普魯斯特長(zhǎng)度的小說(shuō),這本書(shū)我仍然很忐忑,知不道能不能寫(xiě)成功,只是先試著寫(xiě)著。即使不成功,也沒(méi)關(guān)系,這是另一種寫(xiě)作,我還有比較熟悉的保守寫(xiě)作沒(méi)有停止,那便是以《夜游神》為代表的一類(lèi)小說(shuō),這類(lèi)寫(xiě)法則更向契訶夫靠攏。

《WSJ.》:在你的創(chuàng)作中,能讀出某種意義上的荒涼和悲傷。這種悲傷是來(lái)自于故事發(fā)生地的嗎?我們談到北方的時(shí)候,在當(dāng)下我們都會(huì)覺(jué)得有點(diǎn)蒼涼之感,為什么?
孫一圣 :不單是在華北或者是東北,在南方也會(huì)有,對(duì)人來(lái)說(shuō),可能每個(gè)階段都有每個(gè)階段的絕望。年輕的時(shí)候,考不上學(xué)的學(xué)生,喜歡一個(gè)女生而得不到回應(yīng),都會(huì)有某種意義上的痛苦。即使一輩子沒(méi)有外出過(guò),但那種情緒也是有的。可能在某個(gè)時(shí)間點(diǎn),我們對(duì)這個(gè)情緒就釋?xiě)蚜耍匀淮嬖谶^(guò)。
如果說(shuō)北方或者說(shuō)華北讓人有那種感受,可能跟氣候和環(huán)境有一定的關(guān)系,這些地方有遼闊的土地,一眼望不盡,而南方有山有水,有山林阻擋我們的視線,沒(méi)那么一望無(wú)際,可能是另外一番感受。
《WSJ.》:你在作品的最后都會(huì)寫(xiě)上“作于十里堡”,其他作家要么是哪個(gè)大學(xué),要么就是一個(gè)特別文雅的地方,十里堡是北京的一個(gè)地名,這個(gè)地方對(duì)你來(lái)說(shuō)意味著什么?
孫一圣 :我在十里堡住了五六年了,租房子到期了,會(huì)換一下房子,就是換也會(huì)換在十里堡附近的房子。我一旦熟悉一個(gè)地方,就不太愿意離開(kāi)。
于我來(lái)說(shuō),離開(kāi)一個(gè)地熟悉的地方需要花費(fèi)很大的勇氣,留在一個(gè)地方,反而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呆著,按部就班就好了。起初,我從鄭州來(lái)到北京,離開(kāi)鄭州的時(shí)候就很困難,費(fèi)了極大的力氣才來(lái)北京,不是客觀上的費(fèi)勁,就是我需要說(shuō)服我自己去到另外一個(gè)地方。
當(dāng)年,來(lái)北京找工作面試之前的每一秒,我都在想要不要來(lái)北京。即使我坐上了開(kāi)往北京的火車(chē),甚至到了北京之后,我還在猶豫。我記得那天我早早下了火車(chē),來(lái)到面試地點(diǎn)旁邊的一個(gè)小區(qū)里面,思考了一上午要不要去面試。直到下午,不是我想通了,是將近的時(shí)間像個(gè)馬達(dá)推著我往前走,我才不得不走進(jìn)了那個(gè)面試的咖啡廳。
到現(xiàn)在,我三分之二的小說(shuō)包括《夜游神》和《必見(jiàn)遼闊之地》都寫(xiě)在北京的十里堡。于我來(lái)說(shuō),北京作為一個(gè)寫(xiě)小說(shuō)的地方,比作為一個(gè)生活的地方的意義更大。
《WSJ.》:很多人在一線城市生活,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但卻無(wú)法直接書(shū)寫(xiě)它們。你覺(jué)得問(wèn)題出哪里?
孫一圣 :我現(xiàn)在也基本上寫(xiě)不了城市生活。我在鄭州上了大學(xué),畢業(yè)后又留了一兩年,差不多生活了四年,我也沒(méi)有寫(xiě)鄭州。在北京也待了十年左右了,也沒(méi)有寫(xiě)北京。一是因?yàn)樯畹貌粔蚓茫词故鞘晡矣X(jué)得也不夠久,我抓不住城市社會(huì)的脈動(dòng)。
有一些作家寫(xiě)城市生活的空巢,反而會(huì)寫(xiě)得比較好,比如韓國(guó)作家。這可能跟韓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比較早有關(guān)系。但是,就城市書(shū)寫(xiě),韓國(guó)也沒(méi)美國(guó)寫(xiě)得好,美國(guó)有很大一批寫(xiě)城市題材的高手,比如卡佛,比如福特,更早的菲茨杰拉德尤甚。
他們的城市文學(xué)發(fā)展已久,他們的人情關(guān)系也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化的了。可能我們對(duì)這類(lèi)題材的生疏,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年頭不夠長(zhǎng)久有關(guān)系。我們農(nóng)業(yè)社會(huì)持續(xù)的時(shí)間非常久,對(duì)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關(guān)系網(wǎng)非常熟悉了,只是寫(xiě)我們所熟悉的東西。

孫一圣在《必見(jiàn)遼闊之地》的分享活動(dòng)上。
我覺(jué)著,不必拘泥于是否是農(nóng)村文學(xué)或者城市文學(xué),只需要寫(xiě)下自己熟悉的文學(xué)。就像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文學(xué)就不能以此簡(jiǎn)單類(lèi)比。我們寫(xiě)小說(shuō),說(shuō)到底寫(xiě)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人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人自己內(nèi)心的深入探討。我們需要抓住的是生活的肌理或者人內(nèi)心欲望的搖擺等等轉(zhuǎn)瞬即逝或者容易被我們忽略的一些東西,一旦被表述出來(lái),則有可能是一種決定性的重要的東西。
那種深入生活肌理的質(zhì)地才是我們最難捉住的。
我前面說(shuō)一開(kāi)始受先鋒派小說(shuō)(包括現(xiàn)代主義的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等)影響很大,那是前期。后來(lái),隨著寫(xiě)作越多,我不得不花費(fèi)大量時(shí)間補(bǔ)讀過(guò)去的經(jīng)典,諸如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等。余華的一篇隨筆里說(shuō)當(dāng)初他寫(xiě)小說(shuō)陷入了川端康成的細(xì)膩,后來(lái)是卡夫卡解救了他。我則恰好相反,一開(kāi)始我被絢爛的現(xiàn)代派技巧迷惑了。后來(lái),反而是契訶夫是解救了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閱讀次序,沒(méi)有捷徑可走。你以為你討厭的東西到頭來(lái)可能需要更大的力氣補(bǔ)回來(lái)。當(dāng)我讀完契訶夫十卷本的大部分小說(shuō),我才真正有意識(shí)地去理解了小說(shuō)中生活的質(zhì)地。
《WSJ.》:你很喜歡用第一人稱來(lái)完成敘事,為什么會(huì)有這樣的選擇?
孫一圣 :其實(shí),我對(duì)人稱敘事沒(méi)有特別的偏好。只是《夜游神》和《必見(jiàn)遼闊之地》這兩本書(shū)恰好大部分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主要因?yàn)楣适卤旧砘蛘邤⑹銮徽{(diào)的選擇。
對(duì)于虛構(gòu)而言,故事情節(jié)可以是假的,或者說(shuō)是從別人那兒聽(tīng)來(lái)的、挪用進(jìn)來(lái)的。有的小說(shuō)也從真實(shí)案件或者新聞里借來(lái)故事。不過(guò)以第一人稱寫(xiě)小說(shuō),確實(shí)容易帶入情緒,能讓讀者迅速的進(jìn)入到小說(shuō)里面去。
但是,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是最寶貴的,不是說(shuō)非要把真實(shí)的事情來(lái)挪進(jìn)小說(shuō)里面,而是把個(gè)人的真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和情緒帶進(jìn)去,這樣就使得小說(shuō)在個(gè)人情感和感性經(jīng)驗(yàn)上更具有真實(shí)性,即使是細(xì)微的差別也能體會(huì)出來(lái),能夠使讀者信任這篇小說(shuō)。
《WSJ.》:你怎么看待全民對(duì)于曹縣的揶揄?你怎么看這件事?
孫一圣 :曹縣火了之后,當(dāng)我們用一個(gè)放大鏡去看它的時(shí)候,原本曹縣人的日常生活就會(huì)顯得更夸張一些。其實(shí)在沒(méi)有火之前,縣城的生活一直就是這樣。2021 年的 5 月,曹縣突然成為了一個(gè)熱點(diǎn)。那時(shí)候我正好在曹縣。第二天,有朋友給我發(fā)了個(gè)消息說(shuō),“北上廣曹”,大概意思是說(shuō)曹縣是一個(gè)跟北京一樣的城市。
直到現(xiàn)在,我在北京遇到一些人說(shuō)起曹縣,對(duì)曹縣仍然有深深的誤解。他們的印象是曹縣做棺材生意或者說(shuō)做漢服的。其實(shí),那只是個(gè)別鄉(xiāng)鎮(zhèn)。曹縣還有其他大部分鄉(xiāng)鎮(zhèn),過(guò)著與其他縣城和鄉(xiāng)鎮(zhèn)一樣的普通生活。
而且,當(dāng)有人知道我家開(kāi)靈車(chē)和賣(mài)壽衣生意,他們也覺(jué)著這是曹縣傳統(tǒng),覺(jué)著大部分曹縣的家庭都在做這個(gè)。其實(shí),做這些生意的人也是極少數(shù)的。只不過(guò)我家碰巧是開(kāi)靈車(chē)和賣(mài)壽衣生意的。
我當(dāng)時(shí)不知道曹縣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gè)被觀看的對(duì)象,以為他在諷刺我,以為他知道我回家了。隨后,這個(gè)朋友給我發(fā)來(lái)了一張圖片,那是一張城市夜景圖,說(shuō)曹縣的夜晚看著跟紐約似的。我當(dāng)時(shí)以為他在玩笑,沒(méi)當(dāng)回事。后來(lái),又有不少朋友發(fā)了同樣一張圖片給我,我才意識(shí)到曹縣火了。即便是這樣,我也不知道曹縣為什么火的、是以什么機(jī)制火的,一直沒(méi)太搞清楚。
《WSJ.》:曹縣的老百姓知道曹縣火了嗎?
孫一圣 :知道,當(dāng)天我的鄰居就在喊火了火了,他只知道火了,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這只是聊天的一個(gè)話頭。好像第二天,縣長(zhǎng)也及時(shí)跟進(jìn),開(kāi)了新聞發(fā)布會(huì)說(shuō)這個(gè)事情,借此機(jī)會(huì)推廣曹縣。那是一次正面且良好的推廣,盡力在宣傳曹縣特點(diǎn)的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了曹縣其他方面的特點(diǎn),希望得到更多人關(guān)注。而在絕大多數(shù)非曹縣人看來(lái),可能這只是一個(gè)好玩的事情。
《WSJ.》:你會(huì)覺(jué)得荒誕嗎?
孫一圣 :也還好。我那時(shí)候正在曹縣,如果我在北京的話可能會(huì)不一樣。我在曹縣則感覺(jué)不到荒誕,多少有點(diǎn)莫名。
之前在北京當(dāng)被問(wèn)到我是哪里人的時(shí)候,我就說(shuō)是山東人,因?yàn)闆](méi)人知道曹縣在哪里。現(xiàn)在曹縣比山東名氣還要大,別人再問(wèn),我則直接說(shuō)曹縣了。主要是圖方便。

《WSJ.》:所以你會(huì)寫(xiě)一個(gè)關(guān)于曹縣火了之后的故事嗎?
孫一圣 :那不會(huì),小說(shuō)是一種滯后的文體,它不趕時(shí)髦。我一般對(duì)網(wǎng)絡(luò)詞匯、熱點(diǎn)現(xiàn)象什么的進(jìn)入自己的小說(shuō)都會(huì)比較警惕。至今,我可以說(shuō),在我所有的小說(shuō)里,還沒(méi)出現(xiàn)過(guò)微信、微博、抖音、直播等之類(lèi)新興的東西,不可避免需要出現(xiàn)微信的通信交流,我也盡量寫(xiě)發(fā)來(lái)“信息”這個(gè)模糊的詞匯,而不是說(shuō)發(fā)來(lái)“微信”。準(zhǔn)確地說(shuō),我還沒(méi)找到一個(gè)合適的方法,將新興的東西納入進(jìn)我的小說(shuō),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我前幾年連手機(jī)都不敢出現(xiàn)在小說(shuō)里面,現(xiàn)在當(dāng)手機(jī)和電話一樣普遍了,才把手機(jī)和短信寫(xiě)進(jìn)小說(shuō)里。但是,有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每次我用手機(jī)給別人的手機(jī)打過(guò)去,我都會(huì)說(shuō)打電話這樣一個(gè)古老的詞匯,而不會(huì)說(shuō)打手機(jī)。
《WSJ.》:這是刻意的嗎?
孫一圣 :是刻意的,因?yàn)槲矣X(jué)得很多新興的東西有可能很快就衰落了,我們將很快就不討論了。如果把這些東西寫(xiě)進(jìn)小說(shuō)里面,我會(huì)有一種錯(cuò)覺(jué),好像我的小說(shuō)也將是很快衰落的作品了。
(本文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轉(zhuǎn)載時(shí)略有改動(dòng)。)
- 從青春文學(xué)到青年寫(xiě)作[2022-10-10]
- 三三×王輝城:小說(shuō)是與時(shí)間的一種對(duì)抗方式[2022-09-27]
- 青年作家文學(xué)寫(xiě)作如何戳到痛點(diǎn)與破圈?[2022-09-21]
- 寫(xiě)小說(shuō)的牧民[2022-09-21]
- 小飯:為懂你的人而寫(xiě)(自問(wèn)自答)[2022-09-15]
- 王晨蕾 張惠雯:縣城寫(xiě)作,追尋記憶中的“櫻桃園”[2022-09-07]
- 楊知寒:人世間的復(fù)雜起落,讓我迷戀[2022-08-26]
- 徐小雅:“直到現(xiàn)在”及“那時(shí)候”與“當(dāng)時(shí)”[2022-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