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的文學觀與《應物兄》的接受

李洱 (1966~) 原名李榮飛。河南濟源人。198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0年加入中國作協。曾任河南省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中篇小說《導師死了》《縫隙》《尋物啟事》《鬼子進村》《現場》《葬禮》,小說集《饒舌的啞巴》,文學對話錄《集體作業》(合作)等。長篇小說《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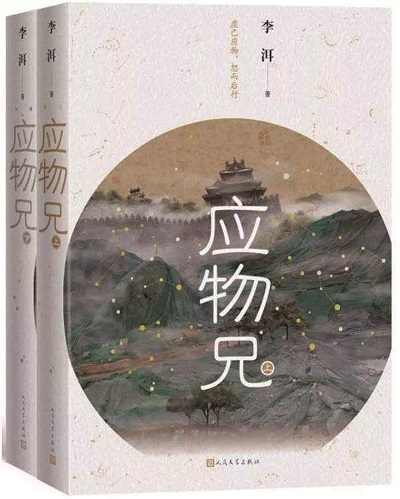
長篇小說《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一、“新的寫作”
關于《應物兄》,我們將為它的奇異與駁雜而吸引。在當下浩如煙海、魚龍混雜的小說創作格局中,李洱的敘述個性而獨特,那是可以打上“高辨識度”的“李洱式”書寫。對于“知識者”的鐘情專注,與身在其中、眼餳耳熱的書寫姿態,讓讀者感受到了他手中之筆既描繪破碎又勾勒整體,既委頓于現實又刺向現實,既反叛傳統又茫然無期。
李洱說,“由于歷史的活力尚未消失殆盡,各種層出不窮的新鮮的經驗也正在尋求著一種有力的表達,如布羅茨基所說,‘它來到我們中間尋找騎手’,我們是否可以說有一種新的寫作很可能正在醞釀之中?”李洱的寫作過程及至《應物兄》的出現,正是他始終探索與實踐著的“新的寫作”,而他也在努力,試圖成為那一個負載使命的“騎手”。無疑,這樣的實踐并不容易,也很有價值,正如《應物兄》磅礴浩瀚的體量、直面時代的勇氣與所呈現的紛繁蕪雜的問題,李洱的嚴正與雄心賦予了它無法被忽視的“實感”;但亦如所有帶有“新”之屬性的事物一樣,它也必將是富于爭議的,如有的批評家所言,這是一部闡釋空間非常遼闊的作品,它將帶給批評家們高度的興奮。
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應物兄》面世后的讀者接受似乎也在映照著《應物兄》的殊異,當然,作品完成之后,短期內讀者的接受與作品創作成效的考量功用之間并不構成正相關或必然性,因為時代性、社會性、政治性、市場性等不同因素總在制約與平衡著評價標準,形塑著個體接受趣味。但完全忽視讀者反應似乎也取消了文本所面對的客體、對象,畢竟真正的“孤獨之書”是無法獲得存在之重的。而《應物兄》的接受形成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評論圈的狂歡與大眾的接受無力呈現出較明顯的兩極分裂;未出版前的圈內叫好與出版初期的眾聲喧嘩轉向客觀中和;“作家之書”的誘惑,與詩人、作家對該書的熱烈擁護不斷昭顯著這部作品所帶來的多重闡釋維度。
二、類型、接受分化及問題
《應物兄》是李洱在創作實踐上的集大成之作。以濟州大學“太和”研究院的籌建為中心,在應物兄的視角下,三代知識分子洋洋灑灑登場,程濟世、姚鼐、喬木、雙林院士、蕓娘等在機鋒交織的言語世界里不斷呈現歷史、世事、文化,進而通過一些細小的世俗化故事設置,以學界為中心延伸至欒廷玉、雷巴山、鐵梳子等政商界人士,形成復雜的社會觀察場,情節也在不同的空間與時間維度里折疊穿梭。小說在以非線性敘述語流、大量的文獻知識引證、龐雜浩瀚的問題思辨,融入片段式、分解式的生活感受中,夾雜噴涌而出,形成對當代正面強攻的書寫。面對如此復雜磅礴的鴻篇巨制,評論圈普遍報以熱情的期待。在《應物兄》刊登之前,歷經13年長跑的《應物兄》在作者交際的文友圈內已經獲得許多關注,李洱在《后記》中說,小說不斷自己生長,“當朋友們問起小說的進展,除了深感自己的無能,我只能沉默。”李洱之前創作形成的良好口碑與身處文學中心的位置,都帶給他的創作更多注視與目光。
2018年《應物兄》在《收獲》長篇專號秋冬卷上刊登時,附帶的評論《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裂變及其他——從李洱長篇小說〈應物兄〉的開篇方式說開去》(王春林)與《臨界敘述及風及門及物事心事之關系》(王鴻生)在兩卷上同步刊發,由此關于《應物兄》的各種評論在文學圈內正式開始登場。該年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應物兄》單行本。12月24日,程德培、金宇澄、吳亮、王鴻生、何平、金理、張定浩等評論家、作家對《應物兄》展開熱烈討論,首先在上海批評界引發震動。“《圍城》升級版”“現象級作品”“注定要長期占據書架”等評價撲面而來。很快,這部小說先登上《收獲》年度長篇小說榜首。12月26日,長篇小說《應物兄》發布會在京舉行,李敬澤、潘凱雄、周大新、臧永清等作家、批評家圍繞該書的寫作態度、敘事特質、闡釋空間等對《應物兄》作出了高度評價。2019年1月,《揚子江評論》2018年度文學排行榜發布,《應物兄》榮登榜首;2月,該刊“名家三棱鏡”欄目推出程德培《眾聲喧嘩戲中戲》與李宏偉的《應物兄,你是李洱嗎?》兩篇風格獨特的評論文章,程文對李洱從《花腔》到《應物兄》的創作進行了與其小說具有同等詮釋特質與哲學思辨的長文,李文則以戲仿的方式直接給“應物兄”寫信交流,應物兄、李洱與李宏偉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再次穿行。隨后,文學研究類刊物《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文藝論壇》《當代文壇》《文藝爭鳴》等紛紛組織專欄對李洱的新作予以關注,囊括了孟繁華、賀紹俊、謝有順、敬文東、馬兵、項靜、熊輝、徐勇、邵部、李音等一眾老中青批評家,他們從《應物兄》的知識分子寫作題材、百科全書式寫作風格、在中西文化融匯創新上的巨大成就、解構主義與憂患意識、詩學問題、世俗生活建構、儒學傳承等不同層面展開全方位立體化的剖析,肯定了作品在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地位。2019年8月,《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作品帶來的話題與關注持續發酵,直至當下。
值得一提的還有,除評論圈的熱議外,李洱還獲得了作家同道和詩人的熱切反應。在《應物兄》之前,魏微寫作過的《李洱與〈花腔〉》盛贊其創作。《應物兄》面世后,詩人杜綠綠的《李洱和他才能的邊界》再次肯定“李洱小說的出現,對于提升中文品質”的意義。至此,《應物兄》從登場直至摘得茅盾文學獎,在文學圈內獲得了相對較為一致的肯定。
與文學圈與批評圈的擁護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應物兄》在普通讀者接受上遭遇的滑鐵盧。在普通網民云集的讀書平臺豆瓣和知乎上,對于《應物兄》的評價相對較多地呈現出否定性。豆瓣短評內點贊數最高的短評中,punkpark寫道,“李洱的確設下了某種野心版圖,但也僅限于此。這是一本專門寫給評論家,以至于可以讓評論家借題發揮自己理論知識的小說……”;而長評中,寶木笑在《從圍城到失敗之書:誰動了當代知識分子的書桌?》一文中寫下“《應物兄》確實很盡力,但天命之年的李洱想要追求那種躍遷——憑一己之力寫盡世間百態,實在是個充滿曖昧誘惑但難度系數實在太高的指標”。其他還有諸如“一部非常奇怪的小說”“難免匠氣”“在整體上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是先天不足的,并且后程確實乏力”等帶有負面色彩的大眾閱讀評價。當然,也有肯定之語。“對中國傳統文學繼承與發揚的一次勇敢的嘗試,也是未來中國文學發展方向的一種可能”“一部我們時代的大作品”等,但相對還是處于弱勢的。
《應物兄》的讀者接受的這種鮮明反差本身構成了當代文學“生產—接受”環節的一個有趣現象。在這些批評、叫好與接受中,我們正得以窺見當下文學創作的分流曲線,這既是學院化教育作用的結果,更是文學觀念與價值多元化導向的解構與失重。
三、李洱的“文學觀”之于讀者接受
作為“60后”的小說家,李洱曾被歸為“晚生代作家”中的一員,他對自己這一代人以及經由學院式教育造就的明晰的文學意識有著深入思考,而這些思考在其寫作風格與寫作氣質上則形成了堅固的意識堡壘。
他在理解“60年代作家”這一整體時將其定位為“有希望,沒確信”的“懸浮的一代”。在談到文學創作的敘述方式時,他認為“沒有受過現代主義訓練的作家,無法成為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作家,而這個時代的現代主義作家,一定會具備著現實主義精神”;他放棄“對世界的整體性感受”,認為“作家進行情感教育和道德啟蒙的基石被抽走了”“整體性的感受如果存在,那也是對片段式、分解式的生活的感受”。同時,他拒絕線性的敘述,拒絕完整地講述一個故事,他認為,“完整地講述一個故事所必須依賴的人物的主體性以及主體性支配下的行動,在當代社會中已經不再具備典型意義”。他十分鐘情于文本間性造成的相互闡釋,對于將注釋引入小說創作中,他始終樂此不疲。他曾說,“想寫一部書,由正文和附本構成,有無數的解釋,有無數的引文,解釋中又有解釋,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從樹上摘一片葉子,砍下一截樹枝,它順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長出新的葉子,新的樹枝。或許人的命運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內外……”,而他也確切地在《花腔》與《應物兄》中實踐了這一理念,可以說,注釋這種行為與對非線性敘事的堅信、對反諷的力量認可、對道德書寫的摒棄,形成了其形式探索、敘事方式與對小說之“道”、對現實與真實等內外兩層的思考。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摘錄李洱在以《問答錄》為主體的書中所呈現出的文學認識與創作思想,是因為李洱不僅有著清醒的寫作意識,同時也有著深刻的闡釋意識。他的文學實踐與文學觀念之間形成了鮮明的交互性,而這種交互經由他的自我認知與闡釋,已經在文本層面和理念層面構成較為完整的體系。在當下的作家里,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類自發性創作,這類作家經由生活經驗、地域性滋養與豐富的歷史時代因素催化,最后交由天性的敏感與后天的培植形塑呈現其文學創作的最終景觀。而另一類作家,擁有傳統主流的寫作意識,主動擁抱文學的道德要求,在文學觀念上有思考但深度不夠,其創作往往也時有與觀念不協調之處(往往是觀念大于創作)。而李洱顯然與前述兩類均不同,他的文學經驗更多交由理性思考處理,在不斷重組、割裂與對話中,將意義與價值“提純”,并以此提供了一條當代作家超越由經驗有限性所造成局限的路徑。可以說,這類寫作在李洱這里不僅形成了完備體系,同時在文學觀念與文學實踐上也表現為總體同步,對于文學寫作思想與技術手段的思考,在小說實踐中得到了較好的呈現,并使得其小說具有極鮮明的“研究特質”。
無疑,《應物兄》是李洱文學觀的實踐結果。布爾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中提出具有“二重性結構”的文學場域概念,一個專為同行精英進行創作的“有限生產場次”,一個面向普通大眾的“大生產場”。“有限生產場次”的自主化追求“通過形式的功能在美學上創造一切”,而這兩種場域也會型構文學接受與消費上的二重性特征。李洱的創作正好與布爾迪厄所說的兩種文學場域形成對照,即便李洱創作本身無意于割裂作品所面對的二重性結構。但在作家的“形式功能”探索、結構創新與超越道德寓言的“創造力”中,其小說的先鋒性是確屬無疑的。即便在《應物兄》中他試圖通過一個基本的故事內核調和先鋒與大眾之間的痕跡,并以此完成對世俗百態的反映,但其非線性的講述、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性、道德解構完成了“異質性”探索,獲得了超凡脫俗的氣質——一種區別于慣常的、傳統的“新的寫作”。這種寫作因無法抹卻的先鋒性,成為“大生產場”的逆子,這也就是在讀書平臺上所說的“讀不下去”“太痛苦了”等評價的根源,同樣也是同道、同行高呼的“不可復制性”與“無限延伸性”的根源。但在其文學觀中,所說的“故事完整性”與作為手段的非線性敘事是否構成邏輯悖反,小說總體性、道德建構與“情感教育”是否帶來小說面對現實的失效,種種命題依舊值得討論。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6月20日第5版。)

相關文章:
- 李洱小說中的“費邊幽靈”[2022-06-20]
- 曾鎮南:我所看見和親歷過的“茅獎”[2022-06-16]
- 《牽風記》:“回返未來”的美學呼喚[2022-04-20]
- 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2022-04-20]
- 《應物兄》詞、物、人關系爬梳[2022-04-01]
- 梁曉聲小說與當代文學中的兩種知青形象[2022-03-18]
- 《人世間》的敘事雄心和史詩傳統的再興[2022-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