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最公正的評論家—— 曾鎮南:我所看見和親歷過的“茅獎”
開創性的首屆“茅獎”
茅盾文學獎這個獎項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1982年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年了。第一屆是1982年評的,評上的作品我大都看過。那時候,雖然我還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但已開始寫點評論文章,因此很快就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當時我參加了茅盾文學獎頒獎會之后的長篇小說創作研討會。那次會議的地點是在華僑飯店,一共三天,周揚提議評出來的作品還要請大家作獎評。會議由張光年主持,丁玲等人也都講了話。參會的人員既有獲獎作者,也有不少在長篇小說創作方面寫出了有影響的作品但這一屆還未能獲獎的作者。
作為一個讀者,我覺得第一屆“茅獎”評得很好。魏巍的《東方》,我細看過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前十章,寫主人公回到家鄉的一段生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華北大地上新生活的時代氛圍寫出來了,人物形象鮮明,故事生動,語言有味,充滿了泥土氣息,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茅盾先生1981年去世,1982年就開始評獎,評的當然只能是在此前已公開出版或發表的作品。
《李自成》(第一卷)20世紀60年代就出版了,據說毛澤東同志還看過,給了比較好的評價,關照并鼓勵作者姚雪垠繼續寫下去。后來第二卷是在新時期之初發表的,茅盾寫了很長的細致評點,文章是用與姚雪垠通訊的方式寫的,這是“茅獎”獲獎作品中唯一經茅盾本人過目的作品,當然,“茅獎”的評獎本來是矚望于青年作家的,《李自成》的獲獎也是為青年作家提供一個榜樣。還有北大中文系的嚴家炎老師也寫了非常長的一篇論文,記得是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可能有兩萬多字,他研究《李自成》就跟研究《三國演義》一樣認真。那時候出現了不少寫農民起義的作品,這部小說一出現,即轟動文壇。它與其他農民起義題材小說不太一樣:不是光寫李自成農民起義,而是把它寫成明晚期整個社會生活非常廣闊的一個畫面,氣魄宏偉,所寫人物就有幾百人。它讓我們見到久違了的功底深厚的中國老一代作家的文筆,因為久違,所以感覺新鮮,我覺得他不愧是大作家,心里十分敬佩。
關于李國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我不但看了,還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評論。這篇論文因為篇幅太長,當時找不到刊物發表,后來收入在我的第一本評論集里,題目叫作《對一個嚴峻的時代的沉思》。記得我是看的作者手稿寫的評論,李國文的字就跟刻蠟版似的,非常工整。我當時感覺他腦子就像個電子計算機,能夠編織那么復雜的情節,而且是過去和現在交叉,寫法很新穎。現在看來,應該說他這個小說還是打上了“文革”時代的烙印,所以就不像當時閱讀的時候那么有歷史意味了。
周克芹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但他去世得太早了。他的生活始終很艱苦。《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據說是四川一個刊物的編輯發現后推薦給周揚的。小說發表后引起了文藝界好評和讀者共鳴。當時描寫不曾遠去的那一段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還比較少,作者對書中人物的命運又注入了深摯的感情,行文細密清麗,婉曲有致,藝術性是比較高的,后來還改編成了電視劇,深受觀眾喜愛。
有的評委說,評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時候,優秀作品不多,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當時巴金是評委會主任,沒有設副主任,評委絕大多數是資深老一代革命作家和文藝評論家。他們很及時、負責地作了開創性的工作。我覺得首屆“茅獎”老一輩的評委、作家、理論家給這個獎開了一個很好的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首屆“茅獎”既有像魏巍這樣的老作家的作品,也評出了一些新人。評委中,謝永旺是最年輕的評論家。他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屆“茅獎”發現了好幾個年輕人,指的就是周克芹、莫應豐和古華。當時,張光年提出了四個標準:要反映時代;要創造典型人物;要啟人心智;在藝術上要感人肺腑,能夠打動讀者的心。作為首屆“茅獎”評選出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都有自己的歷史位置。
少而精的第二屆“茅獎”
第二屆“茅獎”是在1985年11月評選的,當時評的是1982年至1984年之間的作品。這屆獲獎作品特別少,只有三部: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劉心武的《鐘鼓樓》。這三部我認為即便放到現在看都是好作品。
當時,李準的《黃河東流去》是在《十月》上發表的,他已經是比較有名氣的作家,大家都很喜歡讀他的《不能走那條路》《李雙雙小傳》和《耕云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我更是讀了兩遍,這部作品在《十月》發表時,我覺得它寫得并不像長篇小說,因為生活場面都是在一個工業部門的機關里展開的,寫了很多人物,大都是機關干部,筆力比較分散,里面有很多議論,很尖銳、很犀利,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一篇改革開放新時代要來臨的政治宣言書似的,充滿了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后來,張光年親自找張潔談話,讓她修改,張潔在修訂本中作了很大的改動,幾乎好多篇章都重寫過,所以,這是開了“茅獎”作品有修訂本得獎的先例。張光年還給張潔的修訂本寫了個序,在序言里,他很明確地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第一,有些議論是不妥的,有些議論是不一定準確的;第二,這個小說的毛病也就在于議論太多,塑造的人物不集中。修訂本出版時,我正幫張光年準備第四次作代會的報告。看到張光年的序言后,我就給這部小說寫了一篇將近4000字的評論——《蟬蛻時期的痛苦和希望》,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劉心武的《鐘鼓樓》,是講述改革開放以后住在鐘鼓樓下的工人家庭、干部家庭之間的生活故事,感覺充滿了對實現現代化的渴望和希望,透出時代行進的節拍,我覺得這是劉心武最好的代表作。
佳作云集的第三屆“茅獎”
第三屆“茅獎”是1991年才評的,也就是說隔了6年,評的是1985年至1988年之間的作品,評委也還是以老藝術家、作家為主。當時,北京評論界專門閱讀長篇小說的評論家有社科院文學所的蔡葵、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韓瑞亭、《文藝報》的孫武臣,還有一個是曾在作協創研室、后來到魯迅文學院工作的何鎮邦。像我們這些當時被稱為比較活躍的評論家如雷達等,更熱心于評論中短篇小說。當時中短篇小說確實是如萬斛珍珠似的噴涌而出,好作品也比較多。所以,我們對長篇小說創作了解得較少,更談不上熟悉,當然也就沒有進入評委的資格。好像這一屆只有蔡葵和韓瑞亭是正式評委,他們對于新時期長篇小說的研究和闡揚,是作出了較大貢獻的。
第三屆“茅獎”的獲獎作品有《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都市風流》《第二個太陽》和《穆斯林的葬禮》。這屆“茅獎”的特別之處是設立了一個榮譽獎,給了老將軍蕭克的《浴血羅霄》和徐興業的《金甌缺》。蕭克是一位老紅軍,《浴血羅霄》寫的是井岡山斗爭這個題材,他寫自己親身經歷的戰斗生活,這是很難得的,好像是第一部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填補了表現井岡山斗爭的空白。徐興業那時已經逝世,但據熟悉他、了解他的評論家們說,他的這部歷史題材小說書寫了宋代的興衰之史,描繪了封建文化發展到純熟程度的宋代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藝術上是很精湛的,是作者傾畢生精力寫成的傳世之作。“茅獎”一般是不評已逝作家的作品的,給徐興業頒發榮譽獎,也是為紀念他為中國歷史題材小說作出的貢獻。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出版)是我認真閱讀和評論過的一部作品。這部長篇小說寫成后,據說是南方《花城》雜志副主編謝望新來北京約稿時,由李炳銀推薦,在《花城》上發表了。我們在陜西駐京辦事處參加路遙《平凡的世界》研討會時,每個人手里拿的都是《花城》初刊本。那時圖書出版還很困難,每本書都要新華書店看有沒有訂數,訂數夠不夠,訂夠了才能付印。最早出版《平凡的世界》的出版社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該社有個姓金的女編輯,非常欣賞這本書,她從路遙那里得到手稿,向社領導力薦,《平凡的世界》這才得以出版。這是我們不能夠忘記的。
雖然路遙那時因中篇小說《人生》和同名電影已經有了一定名氣,但在《平凡的世界》研討會上,連陜西的幾個評論家都不太看好,不少人都認為小說的寫法太傳統、太陳舊,還是按照1975年至1985年這十年間的編年史來展開生活故事,這使小說的節奏變得緩慢、松懈了,等等。其實主要的意見是覺得小說對中國農村社會變動的看法局限于固有的傳統觀念,缺乏創新精神。有人舉例說,單看小說的開頭就很沉悶,讓人看不下去,我倒不這么認為。孫少平在中學食堂打飯,不敢打甲級菜,打的是丙級菜,讓人感受到那種普通鄉村中學的農家子弟讀書的辛酸。然后,田潤葉托孫少平送一個東西給他哥哥孫少安,故事一展開立刻就吸引了我。小說寫到田潤葉被迫跟一個叫李向前的小干部子弟結婚,對他們的婚姻悲劇寫得極有震撼力。這種農村青年在愛情婚姻中的缺憾,此前似乎還沒有人這樣寫過。記得高中時,我看過一本劉澍德寫的《歸家》,觸及到這方面,但也沒有像田、李悲劇那樣哀而無告、痛而難言,到了讓人在戰栗中警省的程度。我當時就沒有附和會上多數人的看法,而是簡單地說了幾句肯定的意見,會后很快就寫出了長、中、短多篇評論,詳盡地談出了我的看法,但在當時也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待到聽說這個小說獲獎了,我當然非常高興,舉行頒獎會時特地趕去聽了路遙在會上的講話,沒想到那是他留給我的最后一面。第三屆“茅獎”評上了《平凡的世界》,應該說對中國當代文學作了很大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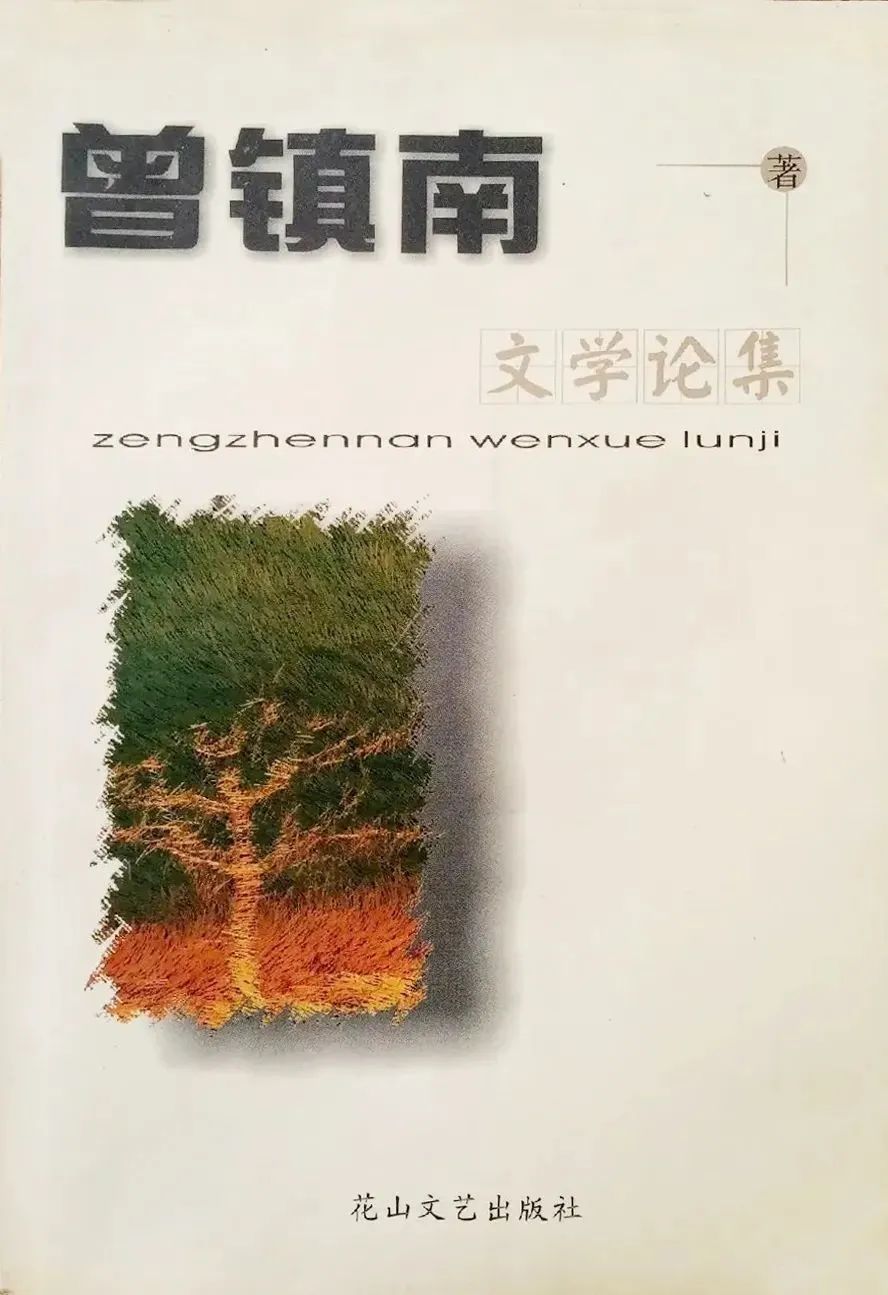
曾鎮南:《曾鎮南文學論集》
另外一部《都市風流》,是孫力、余小惠夫婦合寫的一部小說。他們二人都是新聞工作者,小說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生活,當時被認為是改革小說,實際上他們寫的面比較廣,是把改革開放之初的時代背景、各種各樣的人物經歷都寫出來了,展開了一幅時代畫卷。《都市風流》剛評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陌生,這部小說是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后來才知道可能是當時任出版社總編輯的溫小鈺推薦過來的。溫小鈺是新時期出現的被各方面都認可的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朱寨、陳涌等老評論家都曾經評論過她和汪浙成合寫的中篇小說《土壤》。朱寨是延安時期出來的老評論家,陳涌是文藝理論家,他倆都是第三屆“茅獎”中比較有影響力的評委,也可能因為這些機緣,《都市風流》才進入了評委會的視野。這部小說顯然在創作思路上、在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上,都很契合溫小鈺、汪浙成等人的創作思想,就是從倫理道德、從人的心靈污染、從社會上的腐敗現象這些很敏感的時代課題上來寫這一代改革者們遇到的艱難。我認為《都市風流》經過文學史上的所謂“風水輪流轉”,現在看起來反而是比較好的作品。盡管這兩位作者在文學圈里根本不出名,因為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們沒有別的作品。但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先例,有很多作者,一生就一兩篇代表作。后來,我還問過陳涌,那一屆“茅獎”評上《平凡的世界》就挺好,但《都市風流》好像大家還是感覺寫得單薄和粗糙了一點。陳涌回答,不能那么說,茅盾文學獎初始的要求就是要反映當下的時代,所以他認為《都市風流》的獲獎是可以的。
這屆評獎,我當時感覺有點意外的是《少年天子》。作為歷史題材小說家的凌力,她也是從寫農民起義出來的,到《少年天子》就變成描述清朝順治皇帝了,書中寫順治少年登基,青年主政,后來卻差點為情所困而出家。在當時對于創作潮流的變化,尤其是歷史題材小說創作潮流的變化,這個角度好像是一個風向標,后來出現了大量新作品,我覺得跟“茅獎”的示范作用有關系,像唐浩明的《曾國藩》、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我認為《少年天子》在藝術上還是比較好的,把人物寫得都是活生生的,作者對清史也是有研究的,這對歷史題材小說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拓展。
頗具戲劇性的第四屆“茅獎”
我真正擔任評委是從第四屆開始的。這屆參評范圍是從1989年到1994年,按理說應該1995年就評,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到1998年,距離上一屆的評獎時間(1991年)相隔有7年,已經有大約1000多部作品要參評,所以一些作品沒能進入評委的閱讀視野,而沒有被推薦上來。也就是從這屆開始,除了蔡葵和韓瑞亭等人,我和雷達第一次被選為評委。
這一屆爭論比較大的是《白鹿原》。《白鹿原》最后是以修訂本的名義得獎的,與《沉重的翅膀》一樣。但是具體經過我覺得很有戲劇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爭論很激烈,有點相持不下。由于老評論家陳涌在關鍵時刻作了一個支持《白鹿原》的較有說服力的發言,因此大多數評委已趨向于《白鹿原》,但在行將投票時,有評委提出,是不是請陳忠實就大家議論較多的缺點——?一個是朱先生關于國共兩黨斗爭是“翻鏊子”、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殊途同歸于“公共”主義是徒逞口舌之爭等的議論;另一個是小說性描寫的筆墨太濃太重——進行修改、刪減,以便將來出個修訂版。那天主持會議的評委會副主任陳昌本就提議給陳忠實打個電話,把評委們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轉達給他,問他愿不愿意修改,若同意修改,大家就投票了。大家都說這個辦法好。陳昌本當即出去打電話,過了一會兒即返回,喜形于色地向大家報告說,陳忠實聽了大家的意見很高興,立刻表示可以修改。這些缺點他自己也早已意識到,本已計劃在再版時作一次修訂。大家一聽,都為作者的這種從善如流、自我修訂的嚴謹態度感動了,一投票就通過了。大家都說,真是皆大歡喜呀,好一陣熱烈鼓掌。
因為我也是評委,對別的評委說些什么不便談,但我可以說說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是主張一定要讓作者修改這兩個缺點,而且我和我的同事蔡葵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得很激烈。我當時對《白鹿原》的看法是這樣的:評選的時候已是1998年了,90年代初《白鹿原》送到北京召開討論會的時候,陜西方面來的評論家,以及北京的一些評論家對這部小說的評價都特別好,說是史詩性的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是有創新的。但我當時的發言可以說調子比較低,我覺得這部小說前半部寫得比較集中、有力,有一種開闊的氣勢和震懾心靈的藝術效果。而且每一章人物故事的展開和收束都很有章法。比如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白鹿原上掀起的農民抗捐抗稅斗爭(朱先生發起的“雞毛傳帖”、“交農”事件、罷耕種風潮);軍閥劉瞎子治下受苛政、瘟疫、煙土荼毒,哀鴻遍野、民疾深重、暗無天日的社會圖景;乃至第一次大革命背景下,黑娃、鹿兆鵬在白鹿原刮起的“風攪雪”,等等,真實地呈現出一幅舊中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淚斑斑的圖畫。那種酷烈和血腥、那種因受精神虐殺而發出的控訴和復仇的絕叫(田小娥),都令人戰栗和窒息。但是,小說的下半部乃至結尾,卻因場景轉換、人物分散、情節隱晦、題旨淺表化而力弱,有些塌下去了。白鹿原有共同血緣祖宗的白、鹿兩家兒女們的命運和人生走向各不相同,或跟著共產黨先是參加西北紅軍后奔赴延安,或經過曲折的道路投入國民黨反革命陣營,他們之間的聚散、對峙、互滲、斗爭,基本上都是走出白鹿原,到更大的歷史現場去搬演了,只從遠處時斷時續地傳過來他們的言動聲息,顯得撲朔迷離,未能展開逼真的現實主義的藝術繪狀,只好憑借白鹿原兩位性格已定型的家長及朱先生、冷先生這兩門姻親的反應和議論來評判、展示,很多地方就流于理念化、概念化了。小說結尾雖然寫到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但感覺不到人民革命勝利的時代氛圍,而小說描寫的所有人物,除鹿兆鵬遠赴革命漩渦中心不知所終外,幾乎都得到各種各樣的死亡和悲劇的下場。白嘉軒因土改前把土地賣掉、長工辭去而僥幸沒被劃為地主,從而得到烈士家屬的待遇(因其女兒白靈)。他的浪子回頭的大兒子白孝文,因善于投機,暗害黑娃而穩穩地當上滋水縣縣長。這樣的結局隱伏著此后新的斗爭和禍患……小說前半部描寫“一個民族的秘史”的深邃主題,越往后越淺表化地往演繹朱先生一系列“警世恒言”方向發展。這是作者主觀政治理念的某些失誤的結果。
基于這種看法,我認為作者過于鐘愛朱先生這個近代“關學”的末代人物及其觀念,為渲染并證實朱先生的實證見解和理學觀念,作者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地犧牲了他對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的高度要求。如果把朱先生這個人物過于尖苛的議論刪節一些,并站得更高一點,稍稍對這個白嘉軒奉為神明的大姐夫采取一種俯視的客觀態度,也許小說的整體藝術性會更好一些。這就是我堅持讓作者作些修訂的原因。至于大家所說的性指向問題,我倒沒有太多的意見,因為只要讀懂了小說的第一章,就會明白這個人類傳宗接代、繁衍生息的問題,實際上幾乎貫穿了全書的每一個章節,是作者探索“民族秘史”所取的非常深邃的一個藝術觸須,也是一個獨特的直擊現實的、社會的、宗族的、人的現實的藝術角度,幾乎是無法刪節的。但在這一點上,有些老評委比較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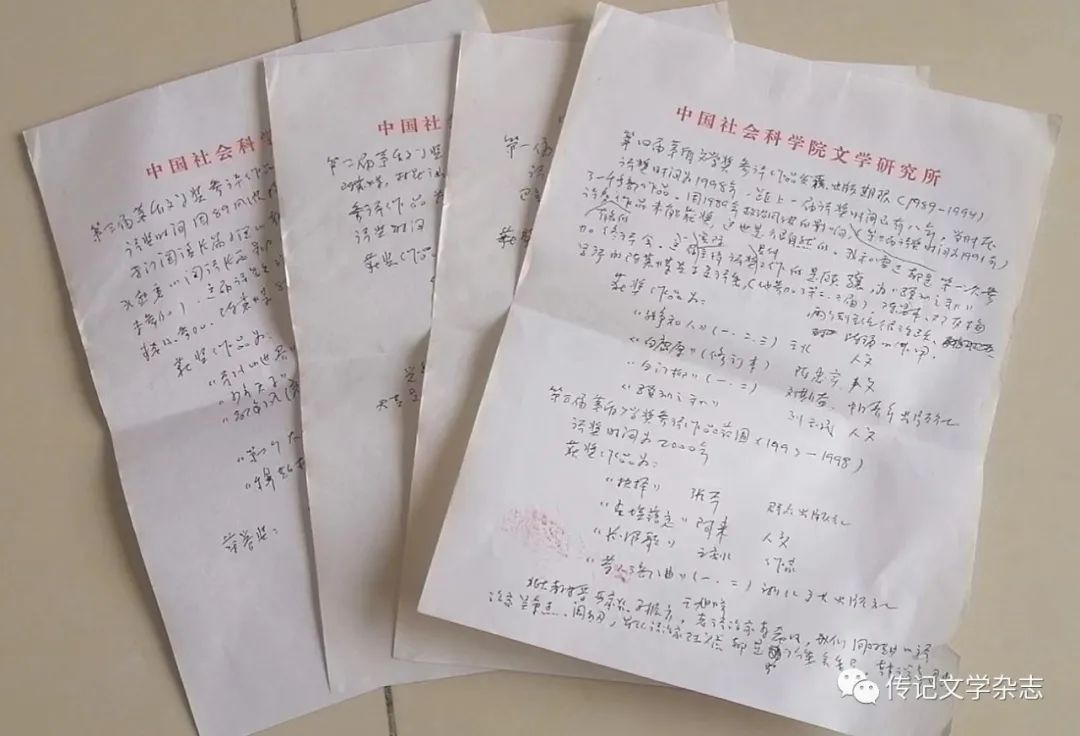
曾鎮南為準備本次口述采訪所作的提綱
我記得,就在大家就這兩個問題討論得比較熱鬧時,陳涌作了一個比較詳細、獨特的發言,大意是說,《白鹿原》把白嘉軒、鹿子霖這兩個地主身份的人物作為小說主要人物來描寫,不回避封建宗法制度在黃土高原上幾千年形成的特殊形態的復雜性,不回避階級斗爭的殘酷性、長期性和紛繁糾結、相互滲透的真相,敢于正面地描繪中國封建社會在革命勝利前夕的黑暗和血跡斑斑的狀態,這在描寫中國舊社會農村的小說中是前所未見的,顯示了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勇氣。從白嘉軒、鹿子霖、朱先生等看起來身處革命陣營之外的反面人物的角度,來描繪社會歷史畫面,這有點類似《靜靜的頓河》,主人公葛利高里是一個走到反對紅軍的白軍營壘里的哥薩克,但也同樣寫出了十月革命前后蘇聯頓河地區階級斗爭和人民史詩的浩博的生活畫卷。但是陳涌沒有多講《靜靜的頓河》,他說,白嘉軒作為一個主要人物本身是可以那么寫的,一部描寫中國革命進程的小說,也可以把地主階級的人物當作主角,而且他認為在這個小說的情節發展過程中,最后還是寫出了中國革命在北方的發展態勢——共產黨力量在北方慢慢擴大,還是把中國革命要勝利的趨勢寫出來了。所以,陳忠實正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性的作家,這個小說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傾向性的問題。當然,小說在主觀上想表達的觀念也可能有些缺失,小說中某些人物,如朱先生的議論也未必就代表了作家自身的看法,我們的討論應當善于把小說實際寫出來的現實主義畫面和小說中一些主觀理念的表達區分開來。陳涌的這個說法在當時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他的意見一出來大家就不爭論了。但是陳涌當時所在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很多同志意見非常大,因為在此之前,這個雜志發表過好幾篇批評《白鹿原》的文章。作為這個刊物的主編,他好像把同事們“閃”了一下。陳涌當時又為什么會持這個觀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陳涌在張煒的《古船》發表以后,曾在《當代》上寫了一篇文章《我所看見的〈古船〉》,肯定了作者藝術才華的同時,也對《古船》中關于“土改”的描寫作了比較重的批評,而且還直接點名批評了雷達對《古船》的評價中提出的“觀念轉換”說。后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陳荒煤寫了篇反駁陳涌的文章,二陳之間的論爭,外面是不太知道的。陳荒煤的文章是在《當代》上發表的,然后陳涌又寫了一篇文章答陳荒煤,這篇文章更尖銳,《當代》就沒發,后來拿到《真理的追求》上發表了出來。這些相互論爭的文章,后收入陳涌的評論集《在新時期面前》。這幾個回合的論爭其實在當代文學史上應該記錄下來,但是現在幾乎沒什么人知道了。所以,由于發生過這個情況,當時《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有些同志認為,陳涌不應該肯定《白鹿原》這樣明顯地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的作品。陳涌自己也感覺到了,他曾說,因為支持《白鹿原》,把好多朋友得罪了。
因為當時我還在《文學評論》當副主編,所以就親自去找陳涌約稿。我跟陳涌說,你在評委會上的發言非常好,對我啟發很大,但是有一些東西我還不太理解,你能不能寫一篇評論陳忠實的文章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陳涌非常認真,他不但看了《白鹿原》,而且自己花錢去買了一套當時已經出版的《陳忠實文集》,把《白鹿原》之前的那些中短篇小說都看了,給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論陳忠實的小說創作》,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這可能是陳涌從大西北重回北京后,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我記得很清楚,他大概寫了一個多月,都是一片一片貼成的手稿,寫好后他通知我要親自送來。我再三勸阻他,馬上登門去取,他卻堅持要坐地鐵親自送來。這篇文章我親自當責任編輯,我不知道手稿是否在《文學評論》存檔。這篇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與現實主義的文藝標準評論《白鹿原》的文章,應該說是當代文學批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是應該保存下來并引起更多人注意的。《文學評論》評選優秀論文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應該給這篇文章評上,但最后由于各種原因,還是沒有評上。
至于王蒙的《活動變人形》,我始終認為是一部好作品,當時我寫《王蒙論》的時候對這個作品作了專章分析,我認為它早就應該評上的,也不知什么原因沒有評上,但是這部小說后來還是入選了“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在第四屆“茅獎”的消息發布會和討論會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年輕編輯提了一個很尖銳的意見。他說,茅盾文學獎有一個永遠治不好的“癌癥”,就是《古船》和《活動變人形》漏評了,希望以后能夠把這個“癌癥”治好。所以,從我的角度看,我認為《白鹿原》應該得獎,因為表現了文化領域里思想又重新開始活躍了,我們的文藝批評標準在改變魯迅所說的“太狹窄”方面又出現了新氣象。但就這部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藝術方面來說,我并不是很滿意,評上“茅獎”的作品本身也會有缺點,這應該說也是正常的,但懾于眾論,我并沒有再就這個問題寫文章了。
第五、六屆“茅獎”——歷史題材小說的“歸去來”
第五屆“茅獎”的評獎時間是2000年,評選范圍是1995年到1998年之間的作品。這屆爭論比較大的主要是《長恨歌》,有評委對這個作品提出了批評意見。我很早也評論過王安憶的小說,認為《長恨歌》還不錯,因為那時整個社會都是寫帶點憶舊情緒的題材,但如果從作為一個讀者的角度來說,我的熱情是不高的,不過在討論中大家都說好,我也就沒發表什么不同意見。
還有一篇是藏族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我也看了,沒感覺到有特別激動人心的地方。他的文筆不錯,但討論的時候受到了比較多的批評意見。另外一篇《茶人三部曲》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報送的,這部小說在之前開過討論會,當時我參加了,我仔細看了第一部,第二部出版的時候也翻了翻,覺得不錯。作者是歷史系畢業的,歷史觀比較正,藝術上也是有力的,駕馭了一個龐大、復雜的家族這種題材,主要人物是早期民族資產階級中很軟弱的茶人,這個小說最后也通過了。
這一屆“茅獎”參評的歷史題材小說不少,呼聲較高的兩部是唐浩明的《曾國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討論了半天最后都沒通過。討論《曾國藩》時的意見是,這部小說既要寫曾國藩的偉大、了不起,又要寫太平天國斗爭是正義的、革命的,所以在歷史觀上造成了一種矛盾的狀態,不能自圓其說。曾國藩這個人物在這種情況下被美化了,無論作為理學名人、古文大家,還是作為軍事家,過去有對他評價很高的,也有評價很低的。比如,歷史學家呂思勉就認為曾國藩的文章很庸俗。所以,討論來討論去,其實還是由歷史觀決定了這部小說當時意見不能統一,就沒選上。
《雍正皇帝》也是如此,盡管寫得比較好看,但這部小說還是有些問題的。那一屆“茅獎”評委北大有嚴家炎、馬振芳兩位老師參加,馬振芳是研究小說史的,主要批評的不僅是《雍正皇帝》里上朝送的公文不像《李自成》里的那么嚴謹,另外詩詞也不合格律,更致命的問題,是小說的結尾非常離奇,還有很多情節嚴重地違反了歷史現實。這些理由當然對評委會有影響,起碼我聽了以后就不投票了。評委會的討論很重要,對評獎結果影響是很大的,認真讀過小說的,討論的時候發表意見會比較具體、比較有說服力,但凡是涉及到思想與藝術標準等這些方面分歧的,評委互相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由評委自己本著自己的良心去投票,每個人都很有主見,我覺得就是這么一個過程,不存在哪個人的意見救贖了哪一部作品或者推薦出哪一部作品。就我所參加的第四、五、六屆評委工作而言,我認為評委會的工作是很嚴肅的,討論是充分發揚民主的,非常認真的。評出的結果也是大家認可的。第五、六兩屆評獎結果出來后,我都及時寫了評論文章,對全部獲獎作品都作了肯定性的評論。這兩篇文章都收在我的評論集《播芳馨集》里,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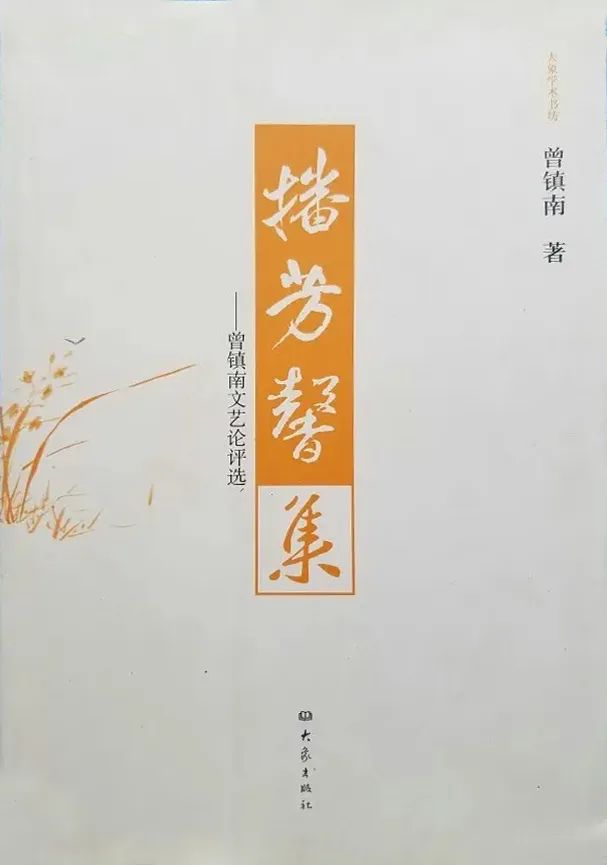
曾鎮南:《播芳馨集——曾鎮南文藝論評選》
第六屆“茅獎”評的是1999年至2002年的作品,頒獎時間為2005年,這一屆歷史題材小說又回歸了,即熊召政的《張居正》。在評獎的三年前,作者在北京組織了一次討論會,我是那個時候看的這部小說。而張潔的《無字》、宗璞的《東藏記》,大家對她們的作品看得比較多,討論起來幾乎沒有什么不同意見,《無字》的獲獎推薦詞還是我寫的。此前,我還寫過《茶人三部曲》的獲獎推薦詞。《歷史的天空》是軍事題材,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涌現的革命英雄主義很好地展現了出來,也沒什么爭議。還有柳建偉的《英雄時代》,是寫改革開放中一些改革家的悲劇和一些干部的腐敗,是現實生活題材的,因為當時正面描寫改革開放時代的作品太少了,這部作品就彌足珍貴。
關于“遺珠”“硬傷”與“癌癥”
后面幾屆“茅獎”評選,我都沒有參加,但有些作品還是比較認真看了,并寫了評論。像《生命冊》,我花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讀得很仔細,然后寫了一萬多字的評論,在《文藝報》上發表了4000多字的節選版。后來這篇評論又在河南《莽原》雜志上全文發表。其實這篇評論本身對《生命冊》有很多批評,《生命冊》的作者盡管也不太滿意,但他還是把它推薦給《莽原》發表了。
總的來說,“茅獎”評選有它的歷史依據,是當時整個社會政治思潮、文化思潮、藝術思潮的一個自然發展的結果,它是各種意見的融匯、互補、綜合,是每一位評委集體工作的勞動成果,當然更是在黨的有關部門指導下產生的重大成果。所以,現在“茅獎”的影響越來越大,我是樂見其終有大成的。“茅獎”評出來的結果也都是符合當時文學思潮,比較能夠得到各方認可的作品,盡管不見得各方的意見都一致,如果站在單一方面的立場來看,可能不一定很理想。也有人會說這屆作品有“遺珠”了,那屆作品有“硬傷”了,甚至什么“癌癥”了,有種種說法,但是真正綜合起來看,我看“遺珠”不一定是遺珠,“硬傷”不一定是硬傷,“癌癥”也不一定就是癌癥。隨著社會的發展、時間的推移,讀者的口味是變化的。經典不經典,主要還是看時間,時間才是最公正的評論家。文學不文學,最終還得由歷史學來校正。回顧了我所經歷的“茅獎”評獎情況,我想起了魯迅當年所說的:“文壇是無足悲觀的。”我們應該自信而樂觀地前行。

曾鎮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原《文學評論》副主編、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曾任第八、九屆全國短篇小說獎評委,第四、五、六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論證專家。出版專著、論文集:《泥土與蒺藜》《生活的痕跡》《王蒙論》《繽紛的文學世界》《蟬蛻期中》《思考與答問》《人生·文學與法》《曾鎮南文學論集》《平照集》《微塵中的金屑》《播芳馨集——曾鎮南文藝論評選》《現實主義研習錄》。《泥土與蒺藜》《王蒙論》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一、二屆科研成果獎,《論魯迅與林語堂的幽默觀》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采訪 / 整理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文學》編輯部,采訪時間:2022年4月23日)
- 葉立文:“茅獎”雜憶[2022-06-23]
- 李洱的文學觀與《應物兄》的接受[2022-06-20]
- 李洱小說中的“費邊幽靈”[2022-06-20]
- 《牽風記》:“回返未來”的美學呼喚[2022-04-20]
- 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2022-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