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 ——從讀徐懷中長篇小說《牽風記》想到的

徐懷中 (1929~),河北邯鄲人。1945年參加八路軍,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協。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委員、第五屆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天使》等。長篇小說《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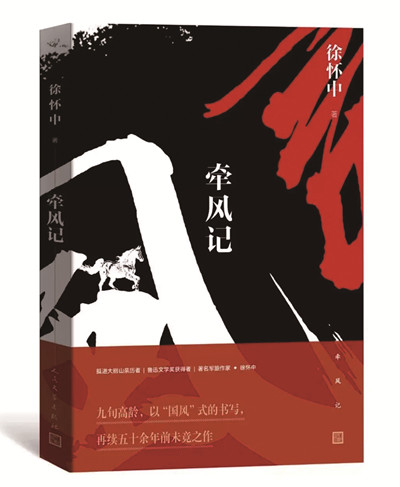
長篇小說《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在小說出版之前,我就有幸讀到了《牽風記》的電子版,這是作為我老領導的徐懷中部長,在作品未曾付梓之時希望聽一聽一眾后學晚輩的意見。一種先睹為快的喜悅,閱讀之后所產生的震撼以及對這位老作家的崇敬之情,皆可謂充盈于內心。當小說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中以高票獲獎,深感此乃實至名歸。老作家在其鮐背之年,竟能寫出如此具有青春態、高質量的作品,內心里除了欽佩還是欽佩。這部小說的創作與出版無疑具有雙重的意義與價值:一是其本身就是我國文學創作一個值得推重的新收獲,能夠獲得國家文學最高獎“茅獎”這一殊榮即是明證;二是這部作品的創作實踐與經驗,對我國戰爭題材文學創作具有特殊的推動和啟示意義。
徐懷中是我真正從內心里尊敬的老作家、老領導,他的人品、官品和文品有口皆碑。在抗日戰爭烽火中加入革命隊伍的他一生戎馬又筆耕不輟,直至任職原總政文化部部長,銜授少將。他一路走來,或輾轉許多崗位,或身居高位,都始終勤勉奮發,坦蕩謙和,待人以誠,對部隊的老中青作家皆多有熱心幫扶、無私提攜與誠懇指點,其親和力與感召力令人印象深刻。同許多迭有新作、著述等身的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數量也許并不能算多,大致有《地上的長虹》《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西線軼事》《阮氏丁香》《沒有翅膀的天使》《那淚汪汪的一對杏核眼兒》《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底色》等。但這些作品皆為名篇刻石有痕,其中《西線軼事》名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首位,1983年獲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大獎;長篇報告文學《底色》則于2014年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其作品不僅顯示出獨具的創作風格與文學特色,在文壇獨樹一幟,而且在文學創作的觀念與意識上,對我國的軍事文學也具有啟示性和領風氣之先的意義。在其遲暮之年,雖然身體多病,仍以充沛的激情、時不我待的急迫,堅持著緩慢堅忍的“爬行”與掘進,“盡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擊”,終于推出《牽風記》這樣一部杰作。
也即是說徐懷中在其卸任之后,仍以極大熱情恪盡推動軍事文學發展之責,率先垂范。這部飲譽文壇的《牽風記》只有19萬字,從其篇幅及獲獎的事實來衡量,堪稱一部超級精短的長篇小說。作品以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的革命戰爭歷史為背景,講述了青年學生汪可逾、一號首長齊競和騎兵通訊員曹水兒等主要人物和一匹名叫“灘棗兒”戰馬的故事。作者雖然不是對戰爭進行全景式的描述,但憑借其槍林彈雨、血火交并的親身經歷,“盡可能勾畫出這次戰略行動的悲壯歷程”,并試圖以自己豐富的戰地生活積累,剝繭抽絲地制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使小說中幾位主要人物在這樣的背景下慢慢顯影。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汪可逾是個亮眼的人物,作為意欲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途經齊競所在的“夜老虎團”駐地時,被陰差陽錯地留了下來,一場混響著戰爭鋼鐵旋律的真純美好、凄婉動人的人生戲劇就此拉開了大幕。懷抱一把古琴,彈奏一曲《高山流水》,無事愛對人笑,見誰都是一句“你好”,構成了這個人物冰清玉潔、人見人愛的外在形象基調。但她又是一個單純倔強、做事認真的女孩,在戰爭環境中依然堅持在睡覺時將脫下的鞋子擺放整齊,固執地要給貼錯對聯的房東糾正錯誤,寫宣傳標語時努力增加其知識性和生動性并在字體上花費心思,對不堪入耳的無聊流言坦然笑對等等。她身為政治部文化教員或司令部參謀,又是眾人矚目與心儀的女神般的存在,是殘酷戰爭環境中的“一道明麗燦爛的戰地風景”。她雖被認為毫無心計,且有夜盲癥和平足腳這兩個對于軍人而言明顯的生理缺陷,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與人們所習見的軍隊及戰爭生活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緊要關頭她卻能果斷率領120多位身處窘境的女性北渡黃河,顯然又具有膽有識、超凡脫俗、高貴完美的理想人格。作品賦予其“紙團兒”的乳名,是否包含著某種潔白而褶皺,脆弱而剛強的寓意與宿命呢?
齊競似乎是置于汪可逾對面的一面鏡子,是最懂得欣賞其天然美質的一個人物,同時也是因其而毀滅的一個人物。他與她之間并非是常見的英雄和美人的落套模式,這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留洋歸國者既是軍隊團旅級有勇有謀的指揮員,又有著古典文化的深厚修養,他與汪可逾在戰地環境中談論古琴及樂譜詩詞等話題,他所作的敵我態勢觀察報告她可以完整背誦其中多個自然段,他將自己的戰馬“灘棗兒”借給她騎等等,一次裸照事件使他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兩人既是異性相吸更是同氣相求,從而逐漸成為精神與心靈上的真正相通者,達到了神仙眷侶般相互欽慕的境地。汪可逾成為十分契合齊競心中選擇人生另一半的最理想的標準。可能讀者對兩人的情感走向會有一種極為自然而合理的期許,即按照終成眷屬的圓滿結局往下推想和演繹這首戰地浪漫曲。但這個看似勇敢果決、英武完美的男人,正因為其內心過于追求完美,使其最終走向感情上的背叛之路,即當汪可逾同眾姐妹們遭敵伏擊被俘而被解救歸來時,齊競并不是首先關切和憐憫汪可逾的被迫跳崖受傷,而是質疑其于劫難之中貞潔的可能失去。齊競的這種心理對汪可逾來說是無法面對和饒恕的。她清澈地洞明了他的這種卑劣心理:對于這個曾經深愛的而如今傷重在身的女人,要么是完好“干凈”的,要么應該是一具尸體。因此她隱忍著巨大的悲痛表達了其極端鄙夷的情緒:“齊競!我從內心看不起你!”這是小說最為沉重而沉痛的一筆。這樣一個在戰場上可以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亦不能突破某種觀念的陳腐藩籬,置心心相印的愛情和生死與共的戰友之情于不顧,從原有的情感立場徹底退縮,其本屬完美的形象在傷痕累累的汪可逾面前轟然坍塌,進而一生都在追悔中過活,直到生命盡頭。
騎兵通信員曹水兒這個人物似乎與齊競的性格與生命軌跡截然相反,也與我們常見的戰士形象大相徑庭。這個因逃婚而出走從軍、身材高大威猛的士兵,被齊競看上后用一把勃朗寧從教導團團長手下換來做貼身侍衛。他在用心履職盡責的同時,私人生活上卻頗為放浪不堪,其以白面換馬料的伎倆沾花獵艷處處留情,行為上屢有出圈犯忌之處,以革命隊伍的紀律來衡量無疑是個品質敗壞的“問題”人物。就是這樣一個士兵卻慨然承擔獨自轉運重傷在身的汪可逾的任務,從而反映出其勇敢機智、重情重義、鐵骨錚錚的鮮明而閃光的特點。在長期男女獨處洞穴危機重重的艱難日子里,這個原本登徒子式的風流人物,對汪可逾挖空心思、想方設法、無微不至地關懷和照顧,從未產生過任何跨越雷池的非分之想。這個人物因從內心“自慚形穢”,對汪可逾有一種“頂禮膜拜”的偶像化的效應,使其身體里存在的原欲因此蕩然無存,才在那樣的時刻和環境做出種種非常之舉,其精神境界無疑是因情感的真摯和偶像的崇拜而神圣化了,其自身形象也變得越來越圣潔和高大。與其相關的就是那匹“灘棗兒”戰馬,它不僅能夠讀懂屬于人類的情感,同人類進行心靈合一的交流,汪可逾彈奏的樂曲《關山月》居然也是其“最熟悉不過的”。汪可逾在曹水兒的指點幫助下,獲得了對“灘棗兒”的“乘騎感”,并成為戰爭中生死相依的戰友。這匹通人性的戰馬,還在隊伍無奈射殺馬群的驚險時刻,因曹水兒的放水而幸運地逃出生天;更為神奇的是,當汪可逾傷重不治離開人世后,這匹在大別山游蕩已久的馬兒,竟匪夷所思地找到了她,并將其尸身運到她生前最喜愛的銀杏樹的樹洞里安放,自己卻在奄奄一息、不曾氣絕之時,就被成群的鷹鷲于瞬間啄成一副白骨。男人與女人、人類與戰馬,在烽火連天的大別山中,共同書寫了一曲生命與人性的壯歌和悲歌。
汪可逾、齊競、曹水兒這三個主要人物在小說中既是個性化的與過往戰爭小說中的人物有著明顯不同的特點,又具有某種符號化的色彩,代表了不同的人性和側面,表達了作家欲寄寓和傳達的認知與觀念。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寫的這些人物命運和情感以及所涉及的種種場景,都是植根和依憑于其戰爭生活經驗所進行的符合生活本身邏輯的書寫;但又都是為達到小說藝術旨歸的需要,進行了卓越、放膽的想象、虛構和夸張。如寫120多位女性因過河載重的原因而褪去身上的所有衣裝,寫在危境之下為了不讓戰馬群落入敵手而將其統統擊斃,寫汪可逾去世后遺體奇異地出現在樹洞的魔幻場景,無疑都是作者虛構所為,使作品充滿了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但這些情節都有極強的動感和文學張力,超越了我們以往對中國戰爭文學的閱讀經驗,充分體現了在作者內心一貫葆有的純凈的審美趣味和對美好事物的真愛,以及在他的創作中始終堅持和體現的典型風格,即從人性、人情的角度切入戰爭生活,使其筆下的戰爭題材既殘酷又傳奇浪漫,反映出作者對真實美好生命的珍視與憐惜,讓讀者透過戰爭的狼煙、風云與血污中盛開出的真實生動、抒情唯美、質地異樣的文學之花,認識和體驗極端環境下的“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同樣應予注意的是,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其寫作不是大河奔騰般的,更不是毫無節制的,而是字斟句酌、含英咀華般的,華彩而堅實、靈動而雋永,顯示出作家非凡的才思與韻致,經得起仔細而反復的品讀與欣賞。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呼喚具有更高質量的中國軍事題材作品的出現。因為我們并不缺少戰爭的歷史,不缺少戰場生活的細節,也不缺少戰爭題材應有的內含。但我們似乎缺少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缺少對戰爭題材更為文學化、審美化的過程。審美能力的相對薄弱一直是中國的戰爭文學和以這一題材為主要方向作家的創作之短。《牽風記》所提供的有益啟示或許是,作家不僅要把本身在寫作上的優勢通過作品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即作為戰爭的親歷者要有一顆細膩而非粗糙的內心,有一種個性化的而非共同性的視角,既看到戰爭中各種宏大和細小的影像,更看到戰爭中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把戰爭中的人、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意義,作為凝視戰爭生活的真正焦點,將通過觀察和認識所獲得的那一切,以文學的形式頑強執著地展現出來。而且不是僅僅從社會的或道德的角度去作機械的判斷,而是根據文學創作的自身規律與審美需要,努力打破軍事文學創作的諸多認知窠臼、思維慣性和同質化傾向,按照歷史與人物的性格邏輯與固有樣貌去寫,甚至調整和放寬對特定情境中特定人物行為所持的評價尺度,進行具有極致意義的夸張與放大,進入寫作上另一番可以縱橫馳騁的自由空間,完成中國戰爭文學具有蛻變意義且影響深遠的審美建構。《牽風記》所進行的就是一種戰爭題材文學新的審美建構,既體現了這位老作家的刻意追求,也是其寫作實踐的一次了不起的勝利。這次勝利是其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而“回返零公里”的重新創作:“我的小紙船在‘曲水迷宮’里繞來繞去,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才找到了出口。”這是一段苦盡甘來式的創作心路歷程的真實表達,也應是所有的中國戰爭題材作家應當持有的追求姿態。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4月20日第5版。)

相關文章:
- 《牽風記》:“回返未來”的美學呼喚[2022-04-20]
- 梁曉聲小說與當代文學中的兩種知青形象[2022-03-18]
- 《人世間》的敘事雄心和史詩傳統的再興[2022-03-18]
- 河水與招魂:從《河岸》到《黃雀記》[2022-02-21]
- 《黃雀記》:作為性格悲劇的美學建構[2022-02-21]
- 培育中國當代文學新經典——茅盾文學獎40周年芻議[2022-01-26]
- “博物”美學與情感記憶的光澤[2022-01-24]
- 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202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