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小說中的“費邊幽靈”

李洱 (1966~) 原名李榮飛。河南濟源人。198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0年加入中國作協。曾任河南省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中篇小說《導師死了》《縫隙》《尋物啟事》《鬼子進村》《現場》《葬禮》,小說集《饒舌的啞巴》,文學對話錄《集體作業》(合作)等。長篇小說《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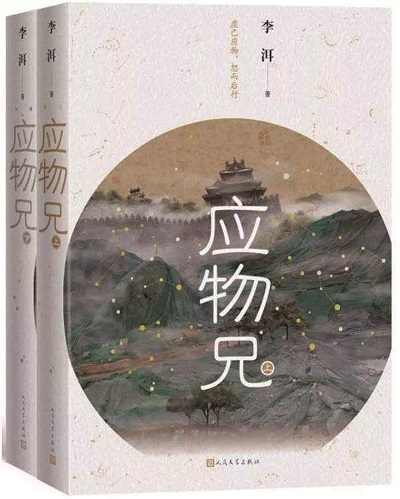
長篇小說《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整體閱讀李洱的小說,會發現他的作品有一些相對穩定或反復出現的元素,比如濟源、濟州是常見的地理標識,滿腹經綸而又夸夸其談的大學教師、詩人或記者,風流成性的男人和妖嬈性感的女人,破敗隱忍充滿背叛的婚姻,以及生存的尷尬和精神的懸浮是常見的“人的風景”。一個職業化的寫作者在其創作生涯中往往會自覺重視自我的內在連續性,這些連續性和穩定性常常又能通往作家敘事與思想上的總體性。在李洱從《福音》(1987)至《應物兄》(2018)的寫作歷程里,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相對穩定的李洱式的寫作經驗,比如聚焦或重視日常生活、知識分子、對話關系、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等內容,呈現反諷、互文、復調、悖論的詩學特征。李洱曾說,他的小說是相互關聯的,也有某種連貫性,他直言《饒舌的啞巴》《花腔》《午后的詩學》之間是一種“衍生關系”,他總想在后面的小說中把前面寫作時產生的一些想法往前推進一點,盡量豐富一點。如果從小說人物的連續性來看,費邊、費鳴、孫良、張亮、杜莉無疑是反復游蕩在李洱作品中的人物“幽靈”。相對于吳之剛(《導師死了》)、葛任(《花腔》)和應物兄(《應物兄》)這些被讀者闡釋較多的知識分子形象,邊緣人物費邊并未得到太多關注。而看似邊緣的“費邊人格”與“費邊視角”,對于理解李洱的寫作和詩學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
在李洱1990年代至今的小說中,《黝亮》《國道》《午后的詩學》《喑啞的聲音》《應物兄》中直接出現過費邊這一人物,在這些小說中,費邊有時是配角或邊緣人物,有時以費邊作為視點人物或小說主角,有時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我的朋友費邊”的生活內容。如果從人格氣質上看,有些小說的人物即使不叫費邊,實際上也與費邊共享著類似的人格氣質,比如《饒舌的啞巴》中的費定、《錯誤》中的張建華、《縫隙》《光與影》《懸浮》里的孫良。李洱是一個對于文學細節非常考究的作家,對于小說人名常常不是隨意為之,他曾說,給小說中的人物取名比給孩子取名難,因為小說中人物的名字要符合特定的環境,還要考慮到小說的主題、小說的人物關系和結構方式。那么,“費邊”這個人物的命名是否也有類似的匠心?這一人物的氣質與小說的主題表達之間是否存在隱秘的關聯?無疑是頗為有趣的話題。費邊,這一名字很容易讓人想到古羅馬權傾一時的貴族費邊氏族,尤其是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采用拖延戰術打敗漢尼拔,挽救羅馬于危難之中的費邊·馬克西穆斯。與此相關的是被人們所熟知的“費邊主義”(Fabianism),作為誕生于19世紀后期的英國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費邊主義”主張知識人以獨立身份參與到社會改良實踐中,同時主張通過理性思考提出解決方法,并提倡漸進實現。那么,李洱筆下的“知識分子費邊”與“古羅馬英雄費邊”之間是否有某種內在的關聯?當代費邊在精神氣質上與費邊主義是否有賡續或歷史反諷?
費邊之名的來源及其含義在李洱以前的文字中并沒有直接的闡釋。盡管“作者意圖”被新批評、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視為文學批評之敵,但很多時候知曉作者意圖可以避免不著邊際的臆測、過度闡釋并帶來批評的準確性和公正性。因而,我就費邊之名問題請教了作家本人,并由此獲得了一些很有啟示意義的信息,在此與讀者諸君分享,這應該也算與李洱文學創作相關的一點新材料或新線索。李洱說:費邊這個人物,在幾篇小說中都比主人公年齡小,但部分地參與主人公的生活。他是參與者、觀察者、審視者、分析者,有時也充當不可靠敘述人。這個名字是一個綜合印象的結果。起緣是格非有一部長篇叫《邊緣》。當年格非選擇題目時,經常向我講起這個詞。至少,他當時有邊緣、中心的概念,但我的感覺與他有差異,我覺得,世上沒有中心與邊緣之別,自認為處在邊緣的人腦子里先有中心的概念,我們應該廢除這種二元概念。沒有廢姓就取了個費姓。從李洱的這段敘述可以看出,費邊之名最初包含了李洱對中心/邊緣二元論的反抗,這種反抗和拆解情緒被李洱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以小說人物之名持續貫穿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從這個角度看,費定、費鳴、費禮也是這種自覺文化立場和反抗意識的派生物。
在另一段話中,李洱坦承了自己為費邊這些小說人物起名的“秘密”,他說:有古羅馬的費邊,還有一個數學家費馬,我在給人物取名時習慣拿出字典查一下(當時還沒有網絡),覺得與我的感覺相符,就把這個名字相對固定下來。我喜歡給人物起一些似乎有歷史依據,又相對復雜,可能包含解構意味的名字,這使我寫起來似乎能獲得一種現實感。有一段時間,我喜歡用孫良這個名字,后來知道有個畫家叫孫良。《花腔》里,有名字叫白圣韜、田汗,大致都出于這種考慮。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李洱的“費邊”不僅有“廢除”某種二元文化意識的訴求,更有與歷史對話,并在氣質、美學和精神上使小說人物和歷史人物實現接通的意味。李洱對費邊這一人物的命名先有對歷史人物費邊的文獻查詢,再有“與我的感覺相符”,即理想中的小說人物與歷史人物在氣質上的接近,這種氣質大致應該是指知識人在真理、精神和話語領域所具有的知識自信和英雄氣場,以及知識精英所具有的分析能力與反思意識。
但很顯然,從《黝亮》《國道》《午后的詩學》《喑啞的聲音》中走出來的“費邊們”并不是秉持理想主義圣火與啟蒙重任并在社會事務中積極介入現實的強勢知識人。實際上,費邊、孫良、張亮們是一群“失敗”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充斥著悖謬與荒誕。一方面,他們學識淵博,對中西知識話語信手拈來,知識與理性帶給他們一種高貴的精神幻覺,另一方面,豐沛的知識與思想理性并沒有必然為他們帶來“好的生活”,這些“話語貴族”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處于尷尬與困境之中。言說知識的玄妙自負與現實生活的狼狽局促,語言上的饒舌狂歡與行動上的無力孱弱,構成了費邊們的悖論境遇。可以說,李洱的“費邊敘事”帶來的這種悖論式經驗、分裂式知識分子群像、混沌小說美學,形成了一種新的小說寫作倫理。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最為成熟的“李洱體”,并不是《遺忘》和《花腔》這些文體探索較強的文本,而是以費邊和孫良為人物的中短篇,因為這些小說內部具有對話性和反思性。我很贊同這個觀點。李洱的寫作總體上是一種智性寫作,重思辨性,關注文化、秩序、時代這些總體性概念下人的境遇,有時對文化、秩序和時代的總體性關切成為思考重心,他迷戀事物的復雜性,人的不平衡性和生活的悖論性經驗成為他經常表述的內容。費邊敘事無疑包含了李洱的這些小說詩學。費邊既聯接著日常生活與知識人的“失敗史”,同時又聯接著知識者的精神生活和理性反思。李洱不愿將費邊簡單植入到新寫實小說那種毫無詩情的庸常生活里,而是賦予費邊“歷史理性”與“詩性自負”的特質。《午后的詩學》中的費邊、《抒情時代》里的張亮、《喑啞的聲音》中的孫良,他們在現實中的失敗史或卑污史是小說的重要內容,但李洱更在意的顯然是他們對“分析”“說話”的堂吉訶德式的堅持。客觀上,這種悖論和不平衡造成一種極強的反諷效果,帶來敘事的張力。但我更愿把費邊人格看成李洱1980年代文化情結的歷史余緒。費邊長于對生活的詩性言說和理性分析,他的詞語閃爍著智慧,分析包含著真理。但李洱一定要將費邊的這種智性和詩性推向極致,于是,費邊華麗的分析氣質在小說里蔓延為一種無處不在的饒舌,他對事物“條件反射地作出分析和判斷”已有近乎學究的病態。費邊這種夸飾性的知識人氣質成為李洱小說中知識分子的一種辨識度很高的特征,在《國道》《午后的詩學》《喑啞的聲音》中是重要的敘事動力或敘事裝置,而到了《應物兄》中則將這種知識饒舌和理性狂歡鋪衍成了普遍的人格氣質。費邊、孫良、應物兄們試圖通過語詞重建文明的燦爛和理性的力量,試圖重建一種精神性的自足世界。實際上,他們無力完成這種形而上的歷史重任,他們發達的智性無益于現實的種種困境。在這種知識分子的悲喜劇中,我們能夠看到李洱對知識分子浪漫理想和啟蒙理性傳統的深深的追懷,還有那種難以抵達的隱痛和哀嘆。
費邊們是這個時代的“分析者”,他們的清醒分析、華麗引證和精彩判斷使我們誤以為他們仍是這個時代的啟蒙者和引領者。但他們身處的20世紀90年代與新世紀,曾經公共生活中的先鋒已經收縮到日常生活的邊緣處。但費邊們似乎不甘心從理性世界中退場,他們在懷疑、反思、分析,這是李洱的反向堅持和獨到思考,即在“知識人的黃昏”時分知識人的生存圖景是怎樣的,以及被市場、資本打散了的知識精英,如何延續或再造知識人的歷史傳統,成為李洱的敘事重心。對于知識分子在世界范圍之內的“式微”之路,李洱是非常清楚的。《午后的詩學》中多次提到法國的“五月風暴”。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這場學生運動,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被視為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這場風暴標志著“預言家知識人的黃昏”。很顯然,李洱內心是有精英主義情結的,對于知識精英曾擁有的那種烏托邦理想和先知式角色難以釋懷,他寫出了費邊們作為精神導師和文化自省者走向“黃昏”的生存圖景。李洱并不嘲笑他們,因為費邊的文化處境既是費邊的,也是李洱這一代人的。
費邊們是“失敗者”,但洋溢著詩性和思辨精神,他們在日常秩序中失位、尷尬,但他們在精神世界試圖重回理性、知識至上的時代。費邊是李洱自我精神的一個“分身”,費邊敘事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1980年代特有的那種由客廳、廣場甚至廢棄兵工廠構成的文化空間,這里盛放著李洱對那個年代文化場景和精神生活的回憶,在這種知識人形成的圍爐夜話、集體作業或是縱情辯駁里,爭論的問題無所不包,知識人的理性與激情得到盡情釋放。李洱的精神起點是作為文化黃金時代的1980年代,費邊未嘗不是1980年代的精神在1990年代的錯位安放,這種錯位存在看上去不合時宜甚至窘態百出,而其深層包含著李洱對于一代人主體精神退場的凝視與憑吊。李洱曾說,這類小說寫著寫著會覺得“周身寒徹”。在李洱的小說世界里,費邊們的生活史體現為知識分子虛弱的抵抗史,他們擎著理性火炬與生活搏斗、與自己搏斗,但這種光似乎沒法照亮他們自己的未來,至多偶爾“黝亮”一下。李洱曾寫過一篇題為《懸浮》的情愛題材小說。在這里,“懸浮”不僅指小說中的情愛、婚姻和他們庸常的生活,還有他對他們這一代人的精神自況。他甚至將“懸浮的一代”歸納為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共性。李洱說,與下一代作家相比,他們與商業社會有較多的隔膜,有抵觸、有憤怒、有妥協、也有無奈。對主流的意識形態他們不認同,同時對于反主流的那種“主流”他們也不認同。他們好像一直在現場,但同時又與現場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的感覺、意念、情緒、思想懸浮在那里,處于一種“動”的狀態,而這種“動”很多時候又是一種“被動”。可以說,受惠于1980年代并由此開啟自己“文化童年”的李洱,通過費邊這樣一種典型的80年代氣質的知識分子,寄予了對于80年代文化人格的懷念。費邊發達的理性思維和卓越的分析能力散發著迷人的魅力是李洱這代人曾有過的精神的輝煌,費邊敘事里有著李洱對一個光榮時代的記憶。
最后我想說的是,文學能否成為一種救贖力量,小說能否重建知識者的精神肖像和主體能動性,是文學值得回應的話題。為時代召喚一種闊達雄強的知識分子人格,賦予他們社會先知式的“浪漫理想”或是積極進世的“事功精神”,使他們從費邊、孫良這些饒舌卻低能、孤傲卻卑微的形象群體中重生而來,也未嘗不是現時代所稀缺的一種寫作倫理。我期待費邊重生。我渴望在李洱未來的寫作延長線上再次看到這個出色的詩人哲學家。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6月20日第5版。)

相關文章:
- 李洱的文學觀與《應物兄》的接受[2022-06-20]
- 曾鎮南:我所看見和親歷過的“茅獎”[2022-06-16]
- 《牽風記》:“回返未來”的美學呼喚[2022-04-20]
- 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2022-04-20]
- 《應物兄》詞、物、人關系爬梳[2022-04-01]
- 梁曉聲小說與當代文學中的兩種知青形象[2022-03-18]
- 《人世間》的敘事雄心和史詩傳統的再興[2022-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