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匪:評《克拉拉與太陽》
顯 明
所以,那些事早已經(jīng)被顯明。
在我們翻開第一頁之前。
還沒有哪本小說像《克拉拉與太陽》這樣,用封面道出了小說的未盡之意:正中央方形鏤空形似窗口,露出后面混凝土墻般的平靜灰色,還有一小片弓形檸檬黃。只有剝開硬皮外的這層橘色裝飾紙,才能明白弓形原來是太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關于太陽的故事——一個散發(fā)的人工光焰的,被遮蔽的,不被認出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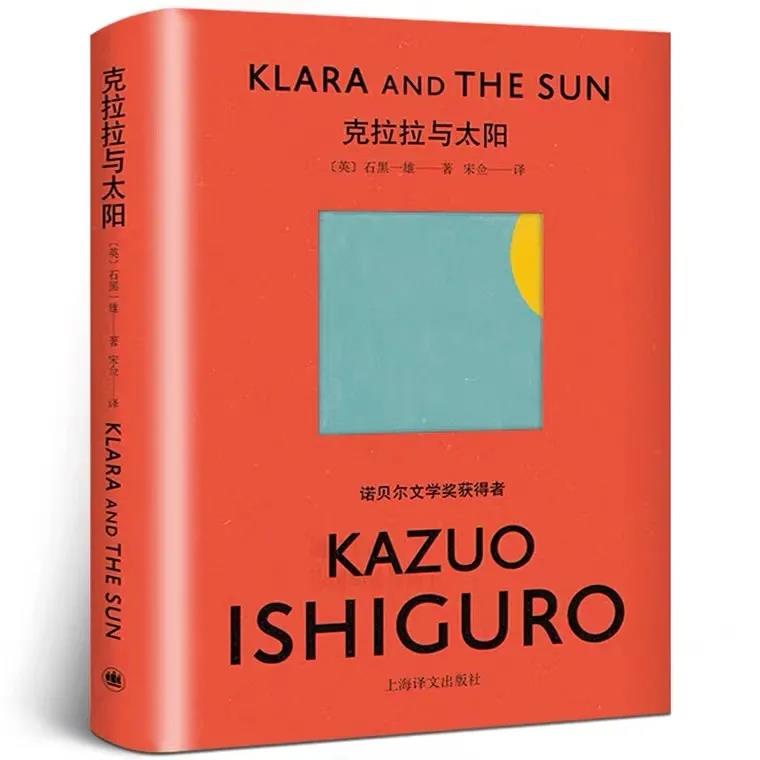
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
“我們的位置在商店中區(qū),視線可以透過大半扇窗戶。“小說一開頭,人工智能克拉拉就將被局限的視野帶入敘述中。受限的視線揭示出她作為商品的被動,更是為整篇作品找到準確的聲調(diào):受限的,不完全的,被蒙蔽卻渴望的聲調(diào)。這聲調(diào)不單單屬于克拉拉,我們會很快知道這點。但現(xiàn)在,就讓我們先認為它只屬于克拉拉,這個剛剛陳列出來的AF。
AF是為陪伴孩子成長而設計的人工智能。她們能夠按自動編碼器深化學習實現(xiàn)自己的功能,可是關于這個世界,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她們所知有限,懷有孩童般稚嫩的念頭,比如“太陽回家過夜了”。AF作為強人工智能,能夠進行復雜的同步運算。簡單的信息輸入就可以使得AF完善數(shù)據(jù)庫,具備基本常識。可是沒有人那么做。因為她們不用知道。
她們只需要知道她們需要知道的就好——好好陪伴孩子。
可是總有特例。
克拉拉就是AF中的那個特例。“我一直渴望看到更多外面的世界,看到它全部的細節(jié)。那個時候,幾乎忘記了太陽和它的仁慈。”作為被使用物,她對世界所知受限,與這種受限相對應的,是克拉拉超出尋常的敏銳以及好奇。受限與渴望之間的矛盾,撕扯的不止克拉拉這個人工智能。還有所有不得不通過克拉克這個受限視角來獲取信息閱讀小說的人類讀者——我們。
稍微敏感的讀者會感到不適。在刻意設置的錯位中,那種習以為常從文本中理解小說的方式不再奏效。我們?nèi)缤粋€必須靠盲人目擊者來破案的偵探,或是透過變形的鏡片觀察世界的科學家,必須克服克拉拉認知偏差帶來的誤導。這不是一次假惺惺的觀察,一次在哈哈鏡里對已知世界的再確認,而是對未來世界真真切切的探索。這其中有太多不同于當下的“現(xiàn)實”有待我們了解。我們被迫進入一個我們不了解的世界,被迫以陌生的方式去了解一個陌生的世界。比如庫廷斯機器,比如改造,比如社會就業(yè)狀況和社區(qū)群落之間的關系。
即使對于我們應該熟悉,也必須經(jīng)過辨認,必須重新學習認識。“天空會被分割成紫色的方格,每一個的色度都和相鄰的一格有所不同。” “母親制造緊張表情的皺紋,此時會折疊重組,傳達出幽默與溫和。”記得嗎,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對墻上的手影游戲著迷不已。是的,人類對影子著迷。我們擅長捕獲陰影圖案的眼睛,在這里,需要重新學習辨認“太陽的圖案”——陽光的形狀。
我們收獲到另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一種新鮮有趣的體驗。不僅限于新鮮有趣。我們無法再輕而易舉地確定什么。小說以克拉拉為第一人稱視角展開。這意味著,我們得到的信息都是從她那而來,經(jīng)過她的轉(zhuǎn)化理解。我們不可能知道任何克拉拉不知道和不理解的事情。我們被困在她的“頭腦”里。“真相”或者說“事實”被懸置起來。
面對外部世界,面對正在和將要發(fā)生的事,問題已經(jīng)不再是“知不知道”,而是“真的如此”?
克拉拉這個不可靠的敘述者,令腳下的堅實地面晃動起來。我們的身體不由得繃緊。當然一開始只是輕微的緊張感。
然后,流浪狗和乞丐人的片段出現(xiàn)了。
乞丐人,而不是乞丐。克拉拉這樣稱呼他——似乎她已經(jīng)洞察到身處社會邊緣的乞丐已被非人化,因此稱呼時有必要稱他為乞丐人。她常常透過櫥窗觀察乞丐和他的狗。有一天她發(fā)現(xiàn)他們死了。確認死亡的過程漫長而令人揪心。從注意不尋常到尋找到發(fā)現(xiàn)到判定。焦慮蔓延浸透她每一行思緒。她只能站在原地用時間來檢驗死亡是否真的降臨。整整一天人和狗都沒有動彈。看來死亡真的降臨他們身上。然而就在第二天,奇跡發(fā)生了。她看見乞丐和狗“如饑似渴地吸取太陽特殊的滋養(yǎng),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強壯起來。”
克拉拉找到了合理化的理由。可我們顯然無法接受那個理由。復活比死亡來得更加突然,吊詭。其中的不合理猶如幾近透明的薄冰從領口滑入引起身體一陣戰(zhàn)栗,或者更像是一場輕度夢魘。死人因日光復活。這一背離常識的片段,經(jīng)日常化的敘述,隱于克拉拉櫥窗生涯。敏銳的讀者感到更加不安。雖然我們?nèi)员焕г诳死纳眢w,可是這時候我們和她分離了。我們清清楚楚看到謬誤不僅僅停留在認識層面。一個天真并危險的信念正在她頭腦里建立。 而這個信念勢必將沖向某個錯誤的目標,導致毀滅性的后果。
在小說世界,遇到不可靠敘述者是一件危險的事。讀者被迫和他們同行,被他們誤導。和其他那些不可靠敘述者不同,克拉拉是一個人工智能,一個非人。她對于我們,是一個徹底的他類。哪怕克拉拉的獨白是以可理解文字形式呈現(xiàn),也不消解它意識中的異質(zhì)性。這種異質(zhì)性不僅僅表現(xiàn)在她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理解,更是直接改變了她接收外部信息的形式。我們不可能忽略小說那些錯位裂變的視覺圖像。它們總是出現(xiàn)在克拉拉情緒最波動的時候。這些有著立體主義繪畫風格的圖像,一旦出現(xiàn)在日常生活,變得如此怪誕驚悚。
A.在店內(nèi)克拉拉感受到經(jīng)理的失望。“我的視線能一直延后到后排的玻璃,可店內(nèi)的空間卻被分割成十個方格。中間三格,它們呈現(xiàn)的是經(jīng)理的不同側(cè)面,她此刻正在做出轉(zhuǎn)身面向我們的動作。在一格中我只能看到她從腰到脖頸上半段的身體,而緊挨它的另一個卻幾乎被她的兩只眼睛占據(jù)了。靠近我們的那只眼比另一只要大上許多,但兩只眼睛中都是善意和悲傷。第三格中展現(xiàn)的則是她的一部分下頜和大半張嘴。在那里我察覺到了憤怒和沮喪。”
B.在喬西的聚會上。空間被切割得更破碎,并且加入了令人焦慮的顏色。“女孩們的眼睛滑進同一格嘴巴和下巴擠進同一格。”
C.和母親去瀑布。“有那么一刻,我感覺她的表情在不同的方格間變化不定。在一格中,譬如說,她的眼睛在殘酷地笑著,而在下一格中,這雙眼里又滿是傷悲。瀑布、孩子和狗的聲音全都漸次消逝,直至緘默,為母親將要道出的話讓路。”
這些裂變畫面的描寫節(jié)制冷靜,甚至帶著無機物的干燥,卻如利刃般穿透人類強烈復雜的情感。經(jīng)過她的視覺切割,我們與我們的愛原形畢現(xiàn)。心懷雜念,求而不得,軟弱又殘酷。
第一次我們?nèi)祟愅ㄟ^人工智能的感覺器官——克拉拉的眼睛——觀看理解人類社會家庭以及情感表達。從我們自身出發(fā)的目光,經(jīng)由我們受限不完全的造物,再次回到了我們身上。熟悉的事物中間,猝不及防地,那些陌生之物闖入視野,經(jīng)過仔細辨認才發(fā)現(xiàn)原來竟是我們的一部分,好像我們就是那個封面上被遮蔽的弓形太陽。這還不是全部。我們看到了她看到的,我們了解卻不堅信她所堅信的,我們在外又在內(nèi)的觀望。 石黑一雄建立一種新的陌生感范式,無需借由創(chuàng)造壯闊詭譎的宇宙景觀和顛覆性的烏托邦想象,而是借由他者對世界錯位受限的認知,通過精心編制熟悉卻無法輕易辨識的世界圖景 ,在這里以一種更幽深微妙的方式滲透進讀者內(nèi)心。他創(chuàng)造性地開拓了人類有限的生命經(jīng)驗,也豐富了科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可能。
克拉拉
關于克拉拉我們知道多少?
對,我們被困在她的身體里。我們不知道克拉拉長什么樣?克拉拉的目光從來不望向自己,也沒有人主動提及她的外形,事實上,人們談起克拉拉時,很少把克拉拉只當作克拉拉。她是喬西的AF。她的功能和職責就是她的全部。
只有一次例外。克拉拉“發(fā)現(xiàn)自己很難在中島的高腳凳上落座,因為我的腳夠不到地面”。那個瞬間月光如同破云而出,照在了克拉拉身上。她被看到。她應該只是一個小孩的樣子。她應該不是什么長腿的美少女AI。那是一個異常動人的時刻。無意間獲取的信息提醒著我們習慣性的忽視,提醒著克拉拉的主體性。而這一點連她自己都不記得。在石黑一雄的小說里,總能看到這樣的身影。卑微得隨時會被拋棄,比如《遠山淡影》中的母女;心甘情愿將自身價值捆綁在更重要的人身上——那些人或者更有權勢比如《長日將盡》的達林頓勛爵,或者更需要幫助比如這里的喬西。他們將他人的幸福視為自己榮耀和使命,愿意付出時光甚至生命。怎樣看待這些自我犧牲,這其中閃耀多少崇高的光芒,或者說它更像是一種無聲無息的卑微的自我抹除?
克拉拉一直在學習,學會理解人類。在櫥窗后面,她看到勉強跟在主人身后被嫌棄的AF,于是她明白有一天她也可能是那個急于被替代的AF;在與咖啡杯女士的重逢中,找到了某種變體的情感,身處特殊時刻,人類快樂里也夾雜著痛苦。來到喬西的家中,她繼續(xù)學習。“我也意識到了我已經(jīng)多么習慣于就身邊其他AF的觀察與判斷做出自己的觀察和判斷,而這又是一個我必須做出調(diào)整的地方。”她在調(diào)整中更深進入幽微晦深的人性中。
“我漸漸看清了人類,出于逃避孤獨的愿望,竟會采取何等復雜何等難以揣摩的策略。我最好的做法就是加倍努力地做好喬西的好AF。”
為了成為喬西更好的AF,克拉拉越來越像一個人類。她故意沉默,她頭腦中充斥巨大的恐懼,她開始懷舊甚至對決意摧毀的庫廷斯機器生出了善意的感情。
令她更像人類的是她的主動性。為了救治喬西,她策劃并且實施了她天真又瘋狂的計劃,她幾次涉險,又在父親的“建議”下取出PEG9溶液犧牲掉一部分功能,這些全部來自于她的主動選擇,而非人類的指令。克拉拉在成為喬西更好的AF的同時,為自身存在賦予意義,也讓她的“生命”獲得了主體價值。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犧牲才是高貴的。
如果回頭再看,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克拉拉還在商店時就已經(jīng)顯露出她的“意志”。她為自己選擇了主人,盡管這是一次極為冒險的行為。如果喬西失信她必須獨自承擔后果——成為一臺滯銷機器。
但是等等,克拉拉的意志真的可靠嗎?一旦短時期目標達成,她的意志就會退回到沉睡狀態(tài)。克拉拉則心甘情愿繼續(xù)成為滿足人類需求的AF。甚至,我們也許該懷疑“意志”是否存在?推動她違背AF行為準則脫離人類掌控以身涉險的,到底是她的“意志”,還是成為喬西的好AF這個命令?如果只是后者,那么唯一讓克拉拉與別的AF不同的就只剩下一點專屬性。她只想做喬西的好AF。對于AF來說,這是不是愛呢?不是給別人的,單單給一個人的情感和服務。如果是愛,那么這點愛也被覆蓋在“為喬西服務”的命令里。人們只是在想克拉拉能否替代喬西,沒有人問她是否愛她?沒有人想過她可能會有愛。
在人類情感世界里,克拉拉只是一個恰好在場恰好可以使用的工具,一個旁觀者。
對于克拉拉自己,她也是個旁觀者。她的目光望向人類望向太陽,對自己卻如此吝嗇。那個弓形太陽,就是不被自己看到的克拉拉。
平靜的暴雨
我說,我們被遮蔽,被困在克拉拉的身體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們也受到了保護。小說隱而未露的真相,連同背后時代振聾發(fā)聵的巨響都被隔擋在外。
石黑一雄式的恐怖是一場平靜的暴雨。惡藏在最日常不過的場景中,輕易施加于人,不見血肉。文明人懂得如何得體作惡施暴。我們明白,我們最殘忍的時候,往往是我們以為愛的時候。
母親要求克拉拉成為喬西活下去。她說,“我要的不是難過,我要的是你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再想想這對你意味著什么。這世上再沒有什么會像你這般被珍愛了。為我做成這件事吧,我在請求你為我做成這件事。為我延續(xù)喬西吧。我也就能夠愛你了。“這是我聽過最恐怖的愛的告白——此刻的你,我面前的你,必須徹底被抹除,比死亡更徹底的消除凈盡,成為從未存在過之物,以便可以成為他物。這是我愛你的條件。我的愛,要求你死,不,是比死更徹底的消失。只有當你消失成為別人時,它才會被激發(fā)。
我們被困在克拉拉里面,作為人類目睹經(jīng)受她遭遇的愛的暴行。小說中沒有任何人意識到那對克拉拉意味著什么。母親與父親的分歧爭執(zhí)的重點在于克拉拉是否能夠成功替代喬西。
父親在這件事的立場遠沒有他表現(xiàn)的那么堅定。他對母親說“我們的一部分自我拒絕放手。這一部分自我仍然執(zhí)著地想要相信我們每個人的內(nèi)核中都藏著某種無法觸及的東西。某種獨一無二,無法轉(zhuǎn)移的東西,我們必須防守。你有充分的理由就像你現(xiàn)在愛著喬西一樣去愛她”。但當獨自面對克拉拉的時候,他再也無法隱藏內(nèi)心深處的懷疑。“懷疑如今科學已經(jīng)無可置疑地證明了我女兒身上沒有任何獨一無二的東西,任何我們的現(xiàn)代工具無法發(fā)掘復制轉(zhuǎn)移的東西。” ( 人類是什么,一個經(jīng)典的根本的哲學問題。讓我們先抵制住這份誘惑,畢竟以哲學方式探討哲學問題,不是文學最迫切的使命。)那么父親突然告解是否意味著更少的惡?從一開始對克拉拉的敵意,到之后的并肩作戰(zhàn),似乎意味著某種和解。我們與克拉拉如此希望。但我們和克拉拉不同。我們知道人心是復雜的,是套著數(shù)不清房間的套間。我們常常在自己的房間里迷路,永遠無法厘清一時言行的意圖。更糟糕的是,我們總是擅長美化我們的行為。憑借智性的麻痹,我們沾沾自喜地站在道德高地。以上這些,克拉拉都不知道。
她相信為了共同的目的,拯救喬西,父親誠心與她聯(lián)手一起摧毀庫廷斯機器。而我們則會錯愕父親毫無道理的天真。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竟然輕易相信太陽能夠拯救女兒的神話,輕易相信只要破壞眼前一臺庫廷斯就能幫助到太陽,然后又恰好想出一個能同時破壞庫廷斯和損壞克拉拉的計策。正是同一個父親,一邊教導克拉拉要學習喬西的內(nèi)心,徹底地成為她,一邊不斷地打量試探觀察克拉拉損壞的程度。
直到父親的法西斯主義傾向被指出,直到他用他覺得合理的方式為自己這么辯解“我們沒有任何侵略性企圖,只是想在必要的關頭保衛(wèi)自己”。“白人,精英隊伍,全民皆兵的武裝,對抗各色人。規(guī)則不是我定的,自然而然人以群分。如果另一個團體不尊重我們或者我們擁有的一切,一場惡戰(zhàn)就跑不了。”我們就再也不用懷疑什么了。
克拉拉也不懷疑,她只相信。
她不知道惡與愛之間并沒有多大的界限。“坐在瀑布邊上,不知不覺你的后背就全濕了。” 愛欲生存的激流奔涌直下,沒有人不會被濺起的水霧弄濕。“母親在那道木圍欄劃出的界線前停下腳步,這里是地面消失,瀑布出現(xiàn)的地方。我能看到水霧在她面前漂浮,心想不一會她就要濕透了。”也許,站在圍欄界限前的不止是母親,而是整個人類。也許是小說家的仁慈,通篇最丑陋的一幕沒有發(fā)生在主角身上。女鄰居海倫和她的舊愛萬斯在飯館的見面,讓我們看到兩個曾經(jīng)愛過的人可以如何冷酷相向,羞辱,怨恨,奉承,利用。愛的殘羹冷炙令人作嘔,尤其對于階級身份差異懸殊的人來說。
聚焦在一家人身上的故事,事實上,是發(fā)生在廣闊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中。雖然大多數(shù)時候他們都是極淡的遠景,但不知道什么時候這些令人難堪的現(xiàn)實會被突然拉到面前,提醒我們現(xiàn)在正在發(fā)生的一切,提醒我們看一下那些浮現(xiàn)出來的事實。
事實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許要比人和AF之間的差異還有大。女管家梅拉妮并不喜歡克拉克。當喬西遇到危急時,女管家忘了她和克拉克之間的距離。她重復著,一遍遍重復著那句后來被證實無比正確的話。她對克拉拉說:我們是一伙的。她們是一伙的。她們同樣被這家人在使用。等到喬西身體康復后,為學業(yè)朋友忙碌,女管家和克拉拉同時變得多余。她們又落入相似的境地。她們曾經(jīng)一起照顧喬西,用自己方式保護喬西,現(xiàn)在需要各自從喬西的生活退出。女管家被新管家代替。
克拉克自己發(fā)現(xiàn)了雜物間。她靜靜待在里面,那是她最應該的位置。然后她等來喬西溫柔的告別。
早于喬西離家時的告別,早于垃圾場向經(jīng)理的告別,克拉拉的告別始于喬西打開雜物間發(fā)現(xiàn)她的時刻。喬西在雜物間為她搭了一個通向高窗的階梯。她知道克拉克喜歡看窗外。現(xiàn)在,克拉克就可以安心待在雜物間了。這里有她需要的一切。
告別的時候“她們彼此對望,面帶和煦的微笑。”
“太陽是仁慈的。”
“太陽總有辦法照到我們,不管我們在哪里。”
還沒有哪本書的封面能這樣準確概括了作品的全部:正中央方形鏤空的后面,水泥墻般平靜的灰色承接住所有的目光。目光是為檸檬色太陽而來,卻被遮擋看不見全貌。
這是一個關于太陽的故事:太陽是仁慈的。那個仁慈的太陽只對她露出了一角。

糖匪,作家,評論人。上海作協(xié)會員。SFWA(美國科幻和奇幻作家協(xié)會)正式作家會員。出版小說集《奧德賽博》,《看見鯨魚座的人》,長篇小說《無名盛宴》,兩次入選美國最佳科幻年選,曾獲美國最受喜愛推理幻想小說翻譯作品獎銀獎、第12屆上海文學中篇最佳小說獎、中國科幻讀者選擇獎最佳短篇小說獎。除小說創(chuàng)作外,也涉足詩歌、裝置、攝影等不同藝術形式。
- 致杜梨:“精確”永遠是一種審美選擇,而非客觀標準[2022-01-30]
- AI能寫出村上春樹的小說?[2022-01-24]
- “我的創(chuàng)作受金庸影響”[2022-01-21]
- 星新一: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如此痛苦[2021-12-30]
- 網(wǎng)文年度好書榜單:科幻、懸疑等題材正在引領新一代網(wǎng)文潮流[2021-12-23]
- 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間想象[2021-12-22]
- 王威廉:文學要突破“繭房”,到廣闊現(xiàn)實中去[2021-12-22]
- 《超能少年》作者劉琦: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個超級英雄夢[202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