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寧:小說(shuō)不是記憶,是現(xiàn)實(shí)的一些陰影
和周嘉寧約在一家有露臺(tái)的咖啡店,隔著蘇州河,我們能望見(jiàn)對(duì)面高樓聳立的中遠(yuǎn)兩灣城——全上海最大的居民區(qū)之一。
“這里以前是上海的一個(gè)棚戶區(qū),叫潭子灣,差不多在2000年前后全部都拆掉了。”周嘉寧在2004年搬來(lái)這一片,當(dāng)時(shí)周邊還很荒蕪,小區(qū)綠化也少,她眼看著那些小樹苗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長(zhǎng)大,長(zhǎng)成今天綠意盎然的樣子,“原來(lái)還有一個(gè)昌化路碼頭,據(jù)說(shuō)今年又要重新通船了。”
這番講述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她新書《浪的景觀》里的一些場(chǎng)景:碼頭、工地、高架、隧道、混凝土叢林、光禿禿的綠化帶……它們正源于世紀(jì)初的上海,總給人一種灰撲撲的感覺(jué)。
那時(shí)周嘉寧剛上大學(xué),經(jīng)常騎著自行車四處亂逛,也在深夜望著工地里的龐然大物一臉迷茫:這個(gè)世界將通向哪里?會(huì)變成什么樣?而回到復(fù)旦,校門內(nèi)外也總在轟隆隆地建設(shè),反復(fù)提醒著她到復(fù)旦第一天看到的一行字:THE FUTURE IS NOT SET(未來(lái)是不確定的)。
“但小說(shuō)不是記憶。記憶包含了被篡改的現(xiàn)實(shí),而小說(shuō)是現(xiàn)實(shí)的投影。小說(shuō)可能就是現(xiàn)實(shí)的一些陰影部分,或者說(shuō)一些鏡像的部分。”在《浪的景觀》出版之際,周嘉寧接受了澎湃新聞?dòng)浾邔T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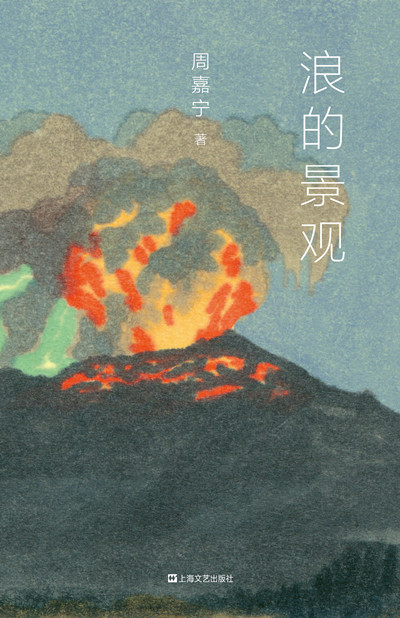
《浪的景觀》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繼2018年的《基本美》之后,周嘉寧推出了最新小說(shuō)集《浪的景觀》。這本書收錄了三篇發(fā)生于千禧年前后的中篇小說(shuō)——《再見(jiàn)日食》《浪的景觀》《明日派對(duì)》,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世紀(jì)初的漫游介于即將逝去與正要開(kāi)始的時(shí)代之間。身處其中的人們既為舊世界的顛覆感到不安,又暗暗期待新世界帶來(lái)的希望。在周嘉寧的筆下,二十年前有人在失戀中寫作,有人在地下商城賺到了第一桶金,有人在電臺(tái)回溯二十世紀(jì)的搖滾歷史,有人以特稿記錄新世紀(jì)的一切……她在自己和他人的記憶里,寫下時(shí)代之間的印跡。
三年來(lái),周嘉寧放慢了寫作速度,日常喜歡約上朋友在蘇州河邊散步,一走就是兩三個(gè)小時(shí)。她熟悉蘇州河四季流水的變化,熟悉兩岸的植物與蟲鳴,也在一些艱難或憂傷的時(shí)刻遇見(jiàn)了很美的月亮。每當(dāng)這時(shí),現(xiàn)實(shí)退得遠(yuǎn)遠(yuǎn)的,她不再說(shuō)話,任思緒飄得更遠(yuǎn)。

周嘉寧
大伙湊在一起,想著“學(xué)校之外的事情”
作為年少成名的作家,周嘉寧的履歷在互聯(lián)網(wǎng)早已不是秘密:連著兩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jiǎng)、考取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19歲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2007年碩士畢業(yè)后去北京和張悅?cè)灰黄饎?chuàng)立文學(xué)MOOK《鯉》、2010年回到上海成為專職作家……但我還是很好奇,世紀(jì)之交時(shí)那個(gè)不到二十歲的女孩,都在想些什么?
她從不寫日記,但就在上個(gè)月,她找出了一張寫于1999年12月31日的小紙條,上面只寫了一個(gè)新年愿望:考上復(fù)旦。
和其他高中生一樣,那時(shí)的周嘉寧以看書和學(xué)習(xí)為生活的主題。但有點(diǎn)不同的是,因?yàn)槭乔嗄陥?bào)學(xué)生記者團(tuán)的一員,她從高一就跟著一群高年級(jí)同學(xué)和大學(xué)生報(bào)選題、做采訪、寫城市觀察。直到考上復(fù)旦,她也沒(méi)有選擇任何一個(gè)校內(nèi)社團(tuán),而是繼續(xù)待在記者團(tuán)里。那是她學(xué)生時(shí)代最早的一個(gè)自己選擇的“集體”,周圍都是一群對(duì)文學(xué)或者流行文化感興趣的人,大伙湊在一起,想著“學(xué)校之外的事情”。
那時(shí)她還喜歡聽(tīng)樸樹的專輯《我去2000年》,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會(huì)和新世紀(jì)的到來(lái)聯(lián)系在一起。樸樹不算當(dāng)時(shí)學(xué)校里最火的歌手,只有一小部分人會(huì)聽(tīng),但這一小部分人能因此成為很要好的朋友。考試結(jié)束后,她既放松又興奮,和朋友們一起騎車回家,一群人就在馬路上旁若無(wú)人地唱起那張專輯里的歌。其中一首《媽媽,我…》,周嘉寧現(xiàn)在還背得出歌詞:“在他們的世界/生活是這么舊/讓我總不快樂(lè)/我活得不耐煩/可是又不想死/他們是這么硬/讓我撞他/讓我撞他/讓我撞他/撞得頭破血流吧/知道嗎/我是金子/我要閃光的。”
“我覺(jué)得集體主義在我們這代人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個(gè)東西不僅是你和學(xué)校的關(guān)系,也包括了你和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包括整個(gè)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是怎么影響到你的。”她說(shuō),“我們這代人的成長(zhǎng)時(shí)期已經(jīng)改革開(kāi)放了,能感到各種西方流行文化和自由主義思想的涌入。但從本質(zhì)上說(shuō),你從父母、老師那里感受到的氛圍仍然是一種集體主義,所以當(dāng)時(shí)你本能地想要逃離,想去追尋個(gè)人的意義。”但她感到有點(diǎn)微妙的是,等真的來(lái)到一個(gè)更為自由的個(gè)人主義時(shí)代,她又覺(jué)得集體主義在人生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
想象中的“集體”,不再是現(xiàn)實(shí)中的東西
讓周嘉寧對(duì)“集體”別有感覺(jué)的,還有一群伙伴。無(wú)論在《浪的景觀》還是《明日派對(duì)》,抑或往前追溯《基本美》《密林中》,周嘉寧都寫到了一種僅僅閃耀于世紀(jì)之交的關(guān)系:論壇朋友。對(duì)于今天還在寫作的一批小說(shuō)家而言,“論壇”仿佛是一條打開(kāi)秘密通道的暗語(yǔ)。
高三暑假那年,周嘉寧家里買了電腦,她很快成為“暗地病孩子”“黑鍋”“晶體”幾個(gè)文學(xué)論壇的常客。這些論壇頁(yè)面簡(jiǎn)陋,設(shè)計(jì)單一,卻引來(lái)一群人在此流連忘返,肆意揮霍時(shí)光。論壇里有人寫小說(shuō),有人寫詩(shī),也有畫漫畫的、做設(shè)計(jì)的、玩樂(lè)隊(duì)的、拍照片的……大家似乎都很喜歡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發(fā)出來(lái)的文字大都奇奇怪怪,很短,很不“現(xiàn)實(shí)主義”。周嘉寧也在論壇上寫了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那時(shí)她愛(ài)打“三角洲特種部隊(duì)”,就在文字里模擬自己是游戲中人,在槍林彈雨中穿越各地。
當(dāng)年的“刷論壇”很像現(xiàn)在的“刷微信”,她習(xí)慣性掛在上面,不時(shí)看看有沒(méi)有新的帖子或留言。一旦有新的展覽或演出,論壇里馬上有人貼出消息。“那個(gè)時(shí)候小型展覽和演出特別多,但很簡(jiǎn)陋,也不需要審核或許可,酒吧表演和live house都很繁榮。”每每去看展覽或演出,很容易碰到論壇中人。大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來(lái)回走動(dòng),看完了就一起吃飯,很快成為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朋友。
“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最珍貴的應(yīng)該就是認(rèn)識(shí)了張悅?cè)弧!敝芗螌幐嬖V我,她們?cè)谡搲J(rèn)識(shí)時(shí)不到二十歲,雖然因?yàn)槲膶W(xué)認(rèn)識(shí),但其實(shí)都還沒(méi)開(kāi)始真正的創(chuàng)作,都身處一個(gè)無(wú)意識(shí)的狀態(tài)。“最初的相識(shí)和任何利益無(wú)關(guān),甚至和文學(xué)本身也沒(méi)有什么關(guān)系。我總覺(jué)得是論壇時(shí)期奠定了友誼的基礎(chǔ),有那個(gè)基礎(chǔ)在,即使后來(lái)各自的人生境遇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也能讓這段友誼經(jīng)受住時(shí)間的考驗(yàn)。”
她也隱約感到集體主義的含義在今天發(fā)生了一些復(fù)雜的變化,她難以描述清楚。她唯一清楚的是,她在小說(shuō)里寫到的“集體”已不可能在現(xiàn)實(shí)中存活,包括論壇,包括她在《了不起的夏天》里寫到的以她個(gè)人經(jīng)歷為底色的北京申奧成功之夜——“迎面走來(lái)的陌生人互相致意,市民組成的鑼鼓隊(duì)來(lái)自四面八方。一些年輕人站在空的公交車頂上唱《國(guó)際歌》和《戀曲1990》”。
“這個(gè)夜晚再也沒(méi)有被復(fù)制過(guò),更不要說(shuō)它變成一個(gè)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延續(xù)下去。它只能是一個(gè)想象中的‘集體’,不是我們現(xiàn)實(shí)中的東西,我覺(jué)得我寫下這一段,是因?yàn)槲曳浅G宄@一點(diǎn)。”
等到運(yùn)氣耗盡,如何面對(duì)接下來(lái)的人生
上一本書《基本美》出版后,一個(gè)“90后”朋友好幾次和周嘉寧說(shuō)起:你們這代人運(yùn)氣真好。
她一開(kāi)始本能地想要反駁,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錯(cuò)過(guò)嗎?她也會(huì)想起自己高中時(shí)聽(tīng)到了很多復(fù)旦傳奇,比如中文系男生會(huì)找三輪車運(yùn)來(lái)一架鋼琴,然后去女生宿舍門口彈奏,但這樣的浪漫永遠(yuǎn)僅存于她的聽(tīng)說(shuō)和想象里。“高中時(shí)吸引我考進(jìn)復(fù)旦的那些東西,似乎等我進(jìn)去了就都沒(méi)有了。”
但后來(lái)寫起《明日派對(duì)》里的三個(gè)中篇,尤其寫到《浪的景觀》和《明日派對(duì)》時(shí),她越來(lái)越意識(shí)到她這一代在世紀(jì)之交迎來(lái)青年生活的人確實(shí)擁有很大的運(yùn)氣成分。回想自己的青年時(shí)代,她現(xiàn)在也常用到一個(gè)詞——“不可思議”,包括她的朋友每天放學(xué)回家要先聽(tīng)一兩個(gè)小時(shí)的磁帶,包括她自己會(huì)在高二會(huì)考前一個(gè)晚上跑去聽(tīng)鄭鈞的演唱會(huì),以至于激動(dòng)得難以入眠……這些在今天的她看來(lái),都是不可思議的。
仔細(xì)想想,《浪的景觀》里的兩個(gè)男孩都沒(méi)有很明確的商業(yè)目標(biāo),他們就是趕上了地下城的黃金浪潮,如有神助地賺到了第一桶金。《明日派對(duì)》里的兩個(gè)女孩也不是專業(yè)出身,她們只是碰上了千禧年的電臺(tái)光輝歲月,就做成了紅極一時(shí)的節(jié)目。《明日派對(duì)》里寫道:“我想所謂好運(yùn),就是專心致志的愿望終于得到來(lái)自宇宙的回應(yīng)。 ”
但許愿的人太多,宇宙永遠(yuǎn)來(lái)不及一一作出回應(yīng)。好在,“不成功”在那時(shí)候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寫小說(shuō)、玩樂(lè)隊(duì)、排話劇、做當(dāng)代藝術(shù)……誰(shuí)有興趣就可以加入,既沒(méi)有管理,也沒(méi)有標(biāo)準(zhǔn),文學(xué)也不像現(xiàn)在有這么多的引進(jìn)書和五花八門的獎(jiǎng)項(xiàng)。一群并不明確自己想做什么的年輕人還有大把的時(shí)間可以嘗試,或者說(shuō),他們可以在某種混亂和無(wú)序里非常盲目地生存下去,甚至可以在一些意外的情況下收獲好運(yùn)。
“問(wèn)題在于,好運(yùn)是不會(huì)持久的,它只在很短暫的一段時(shí)間里出現(xiàn)。等到運(yùn)氣耗盡,我們將如何面對(duì)接下來(lái)的人生,這真是一個(gè)很大的問(wèn)題。”今年春天,周嘉寧和一些挺久不聯(lián)系的朋友聊起來(lái),大家因?yàn)橐咔槎加幸环N絕望的情緒,“好多人不約而同地說(shuō),之前二十年,我們已經(jīng)把過(guò)去能感受到的好運(yùn)都用完了。”
曾經(jīng)的年輕人走在每一個(gè)十字路口,四下張望,焦慮而感傷。周嘉寧知道,她小說(shuō)里的這些人,活到后來(lái)很可能也是遍體鱗傷的。
回望中的時(shí)光印跡,觸發(fā)了一個(gè)個(gè)故事
每次出版新書,周嘉寧都會(huì)對(duì)“代表作”部分再做精簡(jiǎn)。在《浪的景觀》里,她的作者介紹只提到了三本舊作:《基本美》《密林中》和《荒蕪城》。
“我覺(jué)得以前寫得很爛。”周嘉寧直言,她不會(huì)再去看之前的作品,甚至包括《密林中》,盡管《密林中》至少還有一些“幼稚但認(rèn)真”的思考。“以前我太急于寫出某一個(gè)時(shí)段的感受,但這些感受并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思考,所以很多經(jīng)不起時(shí)間的考驗(yàn)。而且從根本上講,我以前也不懂得什么是小說(shuō)。”
“那現(xiàn)在呢?你覺(jué)得什么是小說(shuō)?”
“我怎么知道?”周嘉寧笑了,“我不知道多少寫小說(shuō)的人可以對(duì)此給出定義,難道不是應(yīng)該要寫一本書來(lái)討論嗎?”
“那你現(xiàn)在覺(jué)得小說(shuō)跟故事是什么關(guān)系?”在我的感受里,《浪的景觀》相比她之前的作品,有了更強(qiáng)的故事性。
“我覺(jué)得像《浪的景觀》和《明日派對(duì)》,它們一開(kāi)始觸動(dòng)我的起點(diǎn)都和故事有關(guān),但都不是完整的故事。比如《浪的景觀》的起點(diǎn)是外貿(mào)服裝市場(chǎng)的一段往事,《明日派對(duì)》最初驅(qū)動(dòng)我的是電臺(tái)的黃金時(shí)代,我就想當(dāng)時(shí)身處其中的人是一種怎樣的狀態(tài)?然后我的人物就產(chǎn)生了。”她回應(yīng)道,確實(shí)是回望中的一些東西,觸發(fā)了這一個(gè)個(gè)故事。
之前有讀者評(píng)價(jià)這本《浪的景觀》是用文學(xué)“做21世紀(jì)初的時(shí)間考古”。在她看來(lái),考古依靠的不是記憶,依靠的是時(shí)光留下來(lái)的證據(jù)。有時(shí)它甚至不是你自己的證據(jù),因?yàn)橐恍┦掳l(fā)生的時(shí)候,大家都會(huì)留下證據(jù)。
“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上也還可以搜到各種線索,這些線索可以幫助你重新拼貼出那個(gè)時(shí)候的一些場(chǎng)景。”在寫新書中的三篇小說(shuō)時(shí),她也通過(guò)各種方式去尋找當(dāng)時(shí)其他人留下的記憶,“有時(shí)看多了別人的記憶,會(huì)有一種好像它們也變成了我自己的記憶的感覺(jué)。”
她偶爾也會(huì)看同齡人的創(chuàng)作,并從中看到他們共同擁有的時(shí)代印跡,以及那些印跡對(duì)他們這些人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部分觀察還蠻有趣的。特別是有一些我關(guān)注時(shí)間比較長(zhǎng)的人,比如做音樂(lè)的人,我會(huì)想時(shí)代賦予他們身上的一些東西,我身上也有。有時(shí)是一些好的東西,有時(shí)是一些弱點(diǎn),你看自己時(shí)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晰,但通過(guò)別人反觀自己,會(huì)覺(jué)得一下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關(guān)系,和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
在放慢的節(jié)奏里,理解自己和外界的關(guān)系
從寫作時(shí)間來(lái)看,新書里只有《再見(jiàn)日食》完成于2019年。周嘉寧之后開(kāi)始寫《浪的景觀》,沒(méi)寫多久,2020年就來(lái)了。
“疫情發(fā)生前的兩三年,我不知道為什么,自己整個(gè)人和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處于一個(gè)比較停滯的狀態(tài)。我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隱隱感覺(jué)到什么地方不太對(duì),但直到疫情開(kāi)始,它讓我真正反觀自身,發(fā)現(xiàn)原來(lái)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著停滯的問(wèn)題。所以反倒是疫情這三年,當(dāng)人在物理形態(tài)上真的被限制在某一個(gè)地方,我卻重新獲得了某種行動(dòng)力,重新回到了和外界的互動(dòng),也更主動(dòng)地去面對(duì)問(wèn)題。”
她先讓她的主人公動(dòng)了起來(lái),他們遍歷上海、北京、南京、杭州、青島……一直“在路上”。等他們上路了,她意外發(fā)現(xiàn)自己又找到了和社會(huì)、世界的溝通方式。“《基本美》是短篇小說(shuō)集,里面的小說(shuō)往往都做一個(gè)較為切片式的處理,但到了這本《浪的景觀》,中篇的容量能夠容納我的主人公更多地行動(dòng)起來(lái),在虛構(gòu)世界里去到其他地方,探討一些別的問(wèn)題。”
對(duì)她而言,書寫2010年之后的事特別困難,她找不到一種特別準(zhǔn)確而合適的語(yǔ)言,比如應(yīng)該如何表述一個(gè)寫公眾號(hào)的職業(yè)。另外一點(diǎn)在于,她始終沒(méi)有想清楚這十年的變化對(duì)自己來(lái)說(shuō)意味著什么,又對(duì)他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十年的世界變化無(wú)比迅速,但所有的一切都還處于未知。她說(shuō)過(guò),她沒(méi)有能力去寫對(duì)自己來(lái)說(shuō)還是完全未知的東西。
不難發(fā)現(xiàn),近三年周嘉寧放慢了寫作速度。去年年底整理書稿時(shí),她幾乎又把完成于2019年的《再見(jiàn)日食》重寫了一遍。“我特別在乎準(zhǔn)確的程度,每寫完第一稿,我會(huì)一遍遍地修改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周嘉寧坦言道,一開(kāi)始她對(duì)“慢”也有點(diǎn)焦慮,但現(xiàn)在她想用一種極其緩慢的速度去塑造一個(gè)世界,然后也以這種極其緩慢的速度陪伴她的主人公,在那個(gè)虛構(gòu)的世界里成長(zhǎng)。
在采訪前一晚,她和朋友坐在延安綠地的草坪邊上吃東西,看著天慢慢暗下來(lái),然后竟有一群大雁飛了過(guò)去。這是周嘉寧第一次在上海看到大雁,它們還排成人字形,從北向南飛。當(dāng)它們的身影掠過(guò)K11大樓,大樓的燈光從下往上打到了它們身上,它們看起來(lái)都是白色的,讓周嘉寧感覺(jué)說(shuō)不出的魔幻。
這樣的時(shí)刻猶如她的每一個(gè)虛構(gòu)時(shí)刻,現(xiàn)實(shí)退得遠(yuǎn)遠(yuǎn)的,整個(gè)世界都安靜了。
【后記】
作為“90后”,我對(duì)新世紀(jì)初的印象其實(shí)很模糊,每每看到或者聽(tīng)說(shuō)那時(shí)候的故事不免感嘆“原來(lái)還能這樣”,但這一點(diǎn)也不妨礙我親近并喜歡這些故事。這本《浪的景觀》的神奇在于,我有時(shí)會(huì)覺(jué)得它也是我這代人的故事,那里有熱情,有迷茫,有一時(shí)沖動(dòng),有無(wú)疾而終,就好像是我自己對(duì)青年時(shí)代的念念不忘,在這本書里有了回響。
在相當(dāng)一段時(shí)間里,周嘉寧被認(rèn)為不是一個(gè)善于講“故事”的作家,她更善于捕捉一種情緒、氛圍,或者說(shuō)人的內(nèi)心。這種“善于”在新作里依然是成立的,有時(shí)合上書本,腦海中依然會(huì)有幾個(gè)場(chǎng)景和人物的心緒揮之不去。但還有一個(gè)明顯的感受是,從《密林中》到《基本美》再到《浪的景觀》,周嘉寧越來(lái)越打開(kāi)自己,去傾聽(tīng)外界的聲音,尋找外界的痕跡,也對(duì)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思考與回應(yīng)。
“經(jīng)過(guò)了一些時(shí)間轉(zhuǎn)折點(diǎn),我相信每個(gè)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會(huì)有自己的變化,這些變化或許還不顯現(xiàn)。但所有的變化到最后都會(huì)變成更大的力量,進(jìn)而影響社會(huì),影響世界,卷入充斥著作用和反作用力的更大的磁場(chǎng)中。”周嘉寧坦言,“做21世紀(jì)初的時(shí)間考古”并不是為了重建時(shí)代,而是想要為充滿不確定的當(dāng)下尋找一點(diǎn)線索,這些線索匯集到一起,或許可以指向一個(gè)更明確的所在。
- 《浪的景觀》:浪里個(gè)浪,浪奔,浪流,浪淘盡[2022-10-11]
- 周嘉寧《浪的景觀》:回到千禧年[2022-09-12]
- 上海作家周嘉寧對(duì)話《愛(ài)情神話》導(dǎo)演,打開(kāi)城市書寫新空間[2022-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