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穿越虛無時代 ——張檸小說中的形象與理想

比鄰讀書會成立于2020年5月,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四川大學文新學院師生共同發起,主要成員為兩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博士研究生,讀書會旨在通過對現當代名家作品的研讀與交流,深化大家對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認知,形成南北兩校學術脈絡的互聯。希望能夠引領大家以生命體驗進入文學世界,以開闊視野體察文學流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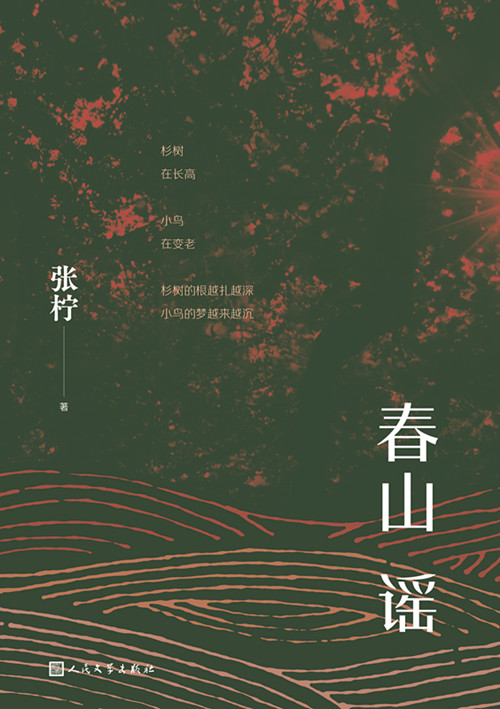
周維東:我很喜歡《玄鳥傳》,我覺得每個知識分子的心中都有一只玄鳥,差別只在于飛得遠近不同。通過《玄鳥傳》,我和作者的共鳴,在于對精神史的癡迷。寬泛來講,一切文學都包含了人的精神史,而張檸小說中的精神史,是現代人對于精神充實的焦灼感,是更現實的癥候。當然這種精神的焦灼感,帶有托爾斯泰的特點,同時也屬于都市漂泊者,包含了無助和傷感。
《玄鳥傳》主人公孫魯西的《玄鳥錄》是一部完整的“沉思錄”。這兩天我還專門把《玄鳥錄》全部摘出來,看它到底在講什么。這其中有道教的修身、佛教的拯救、基督教的愛等等,最后講到文學,既是孫魯西的精神成長史,又仿佛是關于文學意義的社會史。在人的精神追求中,直接遭遇的是哲學和宗教,最終卻在文學中獲得慰藉,找到寄托。為什么人首先不是通過文學解決自己的精神問題?這當中包含文學和哲學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有文學生活在當下發生變化的問題,很值得探討。也正因為此,這種文體跨界的現象值得關注,因為它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容量。作者在進行小說敘述的時候,把文化批評的睿智雜糅其中,比如《玄鳥傳》中關于古典寫作跟現代寫作的差別,經過小說敘事的鋪墊之后,更具有啟發性。
姜 肖:張檸有一種別林斯基式的勇氣,他在《三城記》中給顧明笛安排結尾時,是讓顧明笛走進了生活本身。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曾經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他說:“唯一能治愈當代疾病的途徑,就是歡欣鼓舞地接受生活。”這當然只是一句類似于調侃的話,但這句話立刻讓我想到了病中的魯迅,他在1936年的時候寫過一篇名為《這也是生活》的隨筆,在里邊他提到了一種戰士的生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戰士的生活一方面是金剛怒目式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生活之中的。所以我覺得《三城記》的結尾特別好,施越北在結尾處說:“每次奮斗都好像是為了離開而做準備。……今天就算我們為將要到來的新征程壯行吧,不管各位今后最后怎樣決定,不管我們還能有幾人相伴北上,不管大家以后又要各自去哪里,我們今天在這里每一個人永遠是最親的兄弟姐妹。”他們其實是再出發了,并不是沉湎于某一種庸常。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真正的戰士其實是一個平凡的英雄,這或許就是我們在面對青年性或是面對當下的困境時,可以提出的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張 敏:《玄鳥傳》用一種理想化的方式,為孫魯西打造了一個童話般的生活環境,探討了在對自由精神的極端追求之下,人究竟可以活成什么樣的問題。孫魯西并沒有像哥哥孫梁山一樣,成為成功人士,反而處處碰壁,處處失意。孫魯西對自由的追求,并不是虛空的想象,而是有其具體的時代語境:他生活在上世紀80年代,這是中國市場經濟起飛、城市社會迅速發展的年代,孫魯西所批判的電視節目、市場營銷等對人的束縛和欺騙,楊海經的“異化”,苗蔓的改變,都直指這個時代對人的“改造”。在這種情況下,人對自我的尋找和堅持就顯得彌足珍貴。
孫魯西對自由的追尋,指向的是人的身體和精神該如何自由舒展,是人要如何自處的問題。但他生活的失敗又說明,這種追尋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合適的。張檸曾撰文分析過作為審美理想的文學“新人”形象的特征,簡單來說就是要回應當下的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積極樂觀,追問世界,以行動改變世界。孫魯西顯然不太符合“新人”的條件,比如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簡單地用“勞動異化”一詞來對工作中的楊海經加以評判。他并不能體會楊海經所面臨的生活壓力,沒有對人情的共鳴。但不可否認,孫魯西又具備了“新人”非常重要的一點,即保持自己,不斷向自我、向世界和他人提問,所以《玄鳥傳》仍然可以看作是塑造“新人”形象的一部小說。
李曉博:回溯文學史,“漫游”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主題。最早的漫游強調身體的漫游,空間的密集轉變,這是其鮮明特征,如《奧德賽》《格列佛游記》《愛麗絲漫游仙境》《西游記》等等。當空間漫游的差異性減弱,精神漫游的部分也就凸顯出來了,重要的不再是人物去了哪里,而是他們在一路上想到了什么,極端情況就是空間變成一個點,身體不再行動,精神漫游開始無限延伸,代表就是《追憶逝水年華》。
張檸的《玄鳥傳》,采取了兩線并行的方式,一方面是孫魯西的旅行、游歷,另一方面是孫魯西對古往今來的宗教哲學的閱讀和思考。這是孫魯西“漫游”的部分;他“不漫游”的部分,就是他日常工作生活的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孫魯西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人,他幾乎沒有什么感情生活,跟自己父親的關系也很疏離,和妻子的關系也是名存實亡。他的日常生活是極度單調匱乏的,他的全部能量都消耗在了他的漫游上。但作者把日常生活的部分,或者說留有時代痕跡的部分,交給了孫魯西周圍的人;在孫魯西身上十分匱乏的日常生活,在他周圍人的身上有所體現,這就給了小說一個很真實、很踏實的時代環境。
我還想談談小說的結尾問題。“漫游”有兩種可能性的結局,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回到故鄉。《玄鳥傳》其實并沒有完全給主人公一個結局,作者讓他停了下來,停在海邊,他還繼續存在于這個世界上,還在繼續思考。這其實是一部未竟的小說。
陳田田:組詩《春山謠》作為長篇小說《春山謠》中重要的副文本,既是主人公顧秋林個人的青春情緒書寫,也是18位上海知青共享的回憶,與小說文本之間存在相互印證的關系,暗示著作品的敘事結構。
《杉樹林里的小鳥——春山謠1號》:“鳥”作為詩歌意象有著豐富的象征內涵,可以代表人生理想、象征自由,還常常和思鄉的愁緒掛鉤。小說的敘事結構可以用“嶺中之鳥”來概括,即講述小鳥和林子之間的關系:從貿然闖入,到努力適應,再到想要逃離。春山嶺始終對小鳥施加著某種力,小鳥呈現出一種受困的狀態。上海知青渴望在勞動中鍛煉和成長,實現革命理想,但鄉土社會對闖入者的排斥以及鄉鎮經驗與城市經驗之間的差異,決定了知青們的生存環境必然是一個充滿隔膜的復雜場域。
《土地的汗珠——春山謠6號》:“一只籠子在尋找一只鳥”是卡夫卡對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感到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像一只長著翅膀的“籠子”在不斷追逐著自己。對失去信念的知青來說,艱苦的勞動也無異于“一只籠子在尋找一只鳥”,他們逃無可逃,避無可避。為了實現新的夢,青年們開始模仿和實踐成人的生存法則,學會了拍馬屁、套近乎、鬧事和告密,可以出賣朋友也可以拋棄愛情。可是小鳥們永遠是被動的,一個隱形的籠子始終籠罩在小鳥的上空。
《春山謠0號》:主人公顧秋林直到最后仍然像以前一樣思考問題,固執地相信愛和希望,成為作品中特異性的存在。《春山謠0號:給LY》重新定義了整個敘事,在詛咒荒野和污泥的同時,他感謝草地和山花。春山嶺埋葬了一群人的青春,但也收留了一群人的心。這類在殘酷的世界里尚未放棄理想的人,使人重新相信清醒又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
張 高:長篇小說《春山謠》聚焦的是青春主題,作者試圖借助知青下鄉的特定歷史境遇,由個體來敞向對歷史整體生存的洞察。 張檸的敘述忠實于特定歷史階段的精神型構,使得鮮潤的生命故事不勝憂傷地呈現出歷史的癥候。不論是上海知青還是當地返鄉知青,在那特殊的歷史時期,每一個人都淪入自我拯救的泥淖之中,每個個體又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這讓我們感受到一種關于孤獨個體存在的體驗,其間的意味是豐盈而復雜的。張檸將青春故事置于歷史命運的維度之中,來喚醒隨時間磨蝕而被遺忘的歷史記憶,春山成為青春的故鄉與記憶之地,也是歷史命運的象征。
在《春山謠》中,愛與友善、溫情成為嚴酷命運的最大撫慰,它是青春持久不息的悠長回聲,更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維系的最為動人之處。小說敘事與抒情相交織,整體曲調回環曲折、紆徐綿延,如同一支歌謠,獻給了一代人的命運與青春,也獻給了關于歷史存在的述說。主人公顧秋林深情寫下的獻詩,是關于歷史記憶與精神命名的深情打開,作者以其文字的內力,尋求著讀者和他一同去竭力承擔那份生命的沉重。
《春山謠》將真誠的情感鋪展到人物的靈魂之中,體現出濃郁的生命關懷意識。青春的凋零,相聚與離散,生與死的明滅無形,理想的明亮與苦難的哀泣,城鄉視域下的不同命運……張檸敏銳地體察著青春的憂傷與荒涼,其中有熱淚、有激情、有無奈,有無盡的人生滄桑之感。《春山謠》如同緬懷青春流逝的一聲喟嘆,又在幽暗里時時透出光亮,那來自青春的躁動與追求、不幸與困厄、矛盾與沖突,留下一支關于生命的未曾停息的歌謠。
包辰澤:讀完張檸的短篇小說集《幻想故事集》,我特別注意到《羅鎮軼事》中凝結他鄉村經驗的六篇短篇小說。我在這里想提出“黃昏的繆斯”這一論題,并闡述有關這個論題的三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作為繆斯的鄉村經驗。《羅鎮軼事》是張檸對鄉村經驗的重構,“經驗”是他寫作中反復出現的一個關鍵詞,它深切地與肉身聯結,既是物質性的,又在記憶中深藏。在鄱陽湖邊農村成長的回憶,長久地在作者腦海里徘徊,成為他以自身經驗逼近農民生活、心理的絕佳武器。可以說,鄉村經驗是張檸寫作的觸發裝置,他曾在《土地的黃昏》一書中不無悵惘地提到這一悲劇性的事實:鄉村已在城市的沖擊下成為黃昏。對鄉村的經驗與記憶,隨著時間的拉遠,亦成為模糊的回憶,因此《羅鎮軼事》是對“黃昏之黃昏”的再書寫。
第二個維度,是作為繆斯的羅鎮女性。在黃昏的田壟中,除了調皮搗蛋的“我”之外,還站著羅鎮的繆斯們。在《農婦劉玉珍》一文中,張檸以綿密的對話交代劉玉珍的一生,劉玉珍綿長的啰嗦代表了所有在田間地頭勞作了一輩子的痛苦女人的縮影,張檸以這篇小說開篇,仿佛闡釋何謂小說敘事的舉重若輕。同時小說也昭示出,小說文學性的內核直到今日也沒有變,對人生命運的關注是文學永恒的話題。《呼哨和平珍》中的羅平珍,體現的則是女性身上某種模糊的悸動與不滿足,她經歷了三次出走,可以說是“小羅灣的娜拉”,是面對空洞生活的英雄。
第三個維度,我認為《羅鎮軼事》是在黃昏起飛的貓頭鷹。鄉村經驗會隨著時間的拉長而變得稀薄,同時也會被當代的文化生產所沖淡,那么我們為什么還需要這類鄉村小說?我給出的解答是,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羅鎮軼事》是對現下的反思。鄉村經驗與城市經驗存在著耦合關系,共同構成當下生活的表征;鄉村的精神與病癥,同樣反射于城市。《羅鎮軼事》不僅是對鄉村“奇葩”的展現,也是對總體性的人之經驗的把握。
楊 毅:一般人可能會把張檸批評家的身份作為一個背景,在此基礎上來理解他的小說,但如果我們粗略地把小說創作分成靠理念寫作和靠情感寫作這兩種,那么應該說,張檸并不是單純以他強大的理性作為一種寫作的支撐,而是呈現出一種精神史的寫作。這種精神史的寫作,主要是為了一種斷裂而不是連續,它是為了打破一種線性的時間敘述和總體性的幻覺。“青春”與“幻想”,這的確是張檸小說中的兩個重要主題,但它們的意義并不在于青春或幻想本身,而是通過重新講述青春和幻想的故事,來抵達一個總體性消失后的世界,重新塑造和建構一個精神性的存在。
這幾部作品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特點,就是它們都有一個“副文本”,比如說《春山謠》中題為《春山謠》的詩,《玄鳥傳》中的《玄鳥錄》等等。這些副文本更多地是在呈現作家本人的思考。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小說的結尾——我們發現作者在處理結尾時,實際上是傾向于一種沒有結局的結尾,因為作家很難給這些人物一個真正的結局,所以小說結尾呈現出的是沒有結局的狀態。
至于我所說的“波西米亞”,是本雅明在評論波德萊爾時使用的一個標題,他說波德萊爾一方面是玄妙的寓言家,一方面又是神神叨叨的密謀者,還有文人、“拾垃圾者”等等。這些形象的共同點在于,面對飄忽不定的未來,他們是在模模糊糊地反抗著社會,而不是直接反抗社會,這和張檸幾部長篇中的主人公其實非常相似。所以我認為,張檸的寫作是一種精神史的寫作。
張小宇:《幻想故事集》對女性形象的刻畫,體現了作者對當代女性境遇的觀照。沿著鄉村和城市這條脈絡,作者聚焦了女性的婚戀和事業問題,書寫了女性的命運。作者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性形象,有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比如劉玉珍、譚麗華;有進城打工的女性,比如黃菊花、藍眼睛、萬舒依;也有從城市逃離的女性,比如麥春娟、李雨陽。女性故事的敘述者也在不斷轉換,有他者的視角,也有女性自身的視角,即女性自己來充當故事的訴說者。
首先是他者視角。在《農婦劉玉珍》中,羅長生對劉玉珍的描述就是一種他者視角的敘述,比如“女人就是欠揍”“過著過著就變鬼”,讀者很容易想象到劉玉珍的悲苦生活。《流動馬戲團》的敘述人是一個少年,針對女孩程瑛的惡劣的歌謠,經由少年人之口說出,顯得更加令人心驚。這種他者視角并不關注女性的內心世界,將女性遭遇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暴力粗魯地揭示出來。
而《農婦劉玉珍》《黃菊花的米兔》《普仁農莊里的女人》等小說,巧妙運用女性的敘述視角,將敘述的權利賦予了女性。在正常語境下,病人要向醫生描述病情,劉玉珍看病時卻不講病情,而是“天上地下地胡說”。在劉玉珍絮絮叨叨的訴說中,一個農婦悲苦的境遇慢慢展現出來。《黃菊花的米兔》是對真實事件的轉述和藝術化,小說開篇就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敞嘴壇”的形象,此后的篇幅便圍繞著黃菊花的敘述展開,第一人稱的“我”貫穿全文。《普仁農莊里的女人》中的李雨陽最初以一個神秘鄰居的形象出現,她初到普仁農莊時“每天都在哭喊,不停地問:為什么”,作者借孔一梵之口點出李雨陽的困境:“她的‘為什么’不是疑問句,而是祈使句,是對世界的一種疑問、不滿、憤慨和宣泄,沒有對話的可能。”好在李雨陽的“生死故事”都在和孔一梵的對話中一點點揭開,李雨陽的傾吐和訴說可以說是一場救贖和復活。作者嘗試讓歷史和現實中長期被忽略的女性變被動為主動,突破男性話語的封鎖,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有女性能夠自我言說而不是被言說的時候,那些被男性話語遮蔽的女性遭遇,才能真正呈現出來。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7月16日第8版)
- 張檸:青春都一樣,命運各不相同[2021-06-01]
- 張檸《春山謠》:一段青春 三種視角[2021-05-17]
- 張檸長篇小說三部曲第二部出版,《春山謠》對準80后父輩的青春[202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