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批評印象:永遠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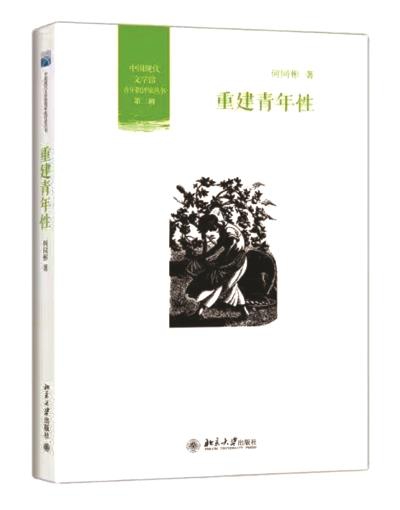


正巧是寫這篇文章的十年前,2012年的10月,我和何同彬,以及另外十位青年批評家同仁,被聘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二屆客座研究員。那一年來飽覽祖國大江南北,一起參加了多場文學活動,這是大家友誼的開端。在介紹我對同彬兄的批評印象之前,我尤為想說的,是對同彬兄多年來喝酒聚會時的印象——他只喝可樂,毫無局促地端著可樂碰杯,且得到了所有人的寬容。不需酒入豪腸,焦糖碳酸,同樣帶著七分月光三分劍氣。
多年來一貫如此,何同彬的批評文章永遠帶著“青年性”的鋒芒,有同仁稱其為“批評殺手”。“殺手”已經頗為傳神。我更想用另一個詞:刺客,從春秋戰國從《史記》中走出來的刺客。展開來說,何同彬的“殺氣”是一種“果斷”的精神氣質,尖銳、有決斷,令人想起加繆筆下的“卡利古拉”:“我要鏟除自相矛盾者和矛盾”,“使不可能變為可能”。這應合于何同彬在《重建青年性》一書中提出的批評觀念:“重新呼喚一種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沖動”,它“構筑在對現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壞之上”,即“檢查”“戳穿”“捍衛”“自信”。由此,何同彬借用克里斯蒂娃關于“遺產人”時代的說法,指出青年為了成為“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在父輩的訓導中變得老氣。這種批評是毫不注意“人情”的,對于我們這些同行來說也無疑顯得刺耳。但筆者選擇和何同彬站在一起,十年后來看,我們也即所謂“80后”這代作家和批評家出名太早,出成果太遲,蕭規曹隨,確實有些暮氣。這種批評同樣也指向筆者或何同彬本人,我們也有著類似的焦灼,比如對于參與、對于公共性、對于真實的意義的渴望,這種渴望有時非常強烈,超過沙漠中的旅人對于水的渴望。但茫茫沙浪,如何突圍呢?
何同彬選擇了正面強攻,在他對于文學批評之批評的基礎上,直接地向一個在他看來文學失重的年代發起了“挑釁”。他明確反對充斥著冗余知識、中庸觀點與惡俗歡顏的文學生活,進而呼喚一種更加嚴厲的批評倫理:“再不反對‘文學’,它就不值得反對了”。在教學生涯中,何同彬教導學生“珍愛生命、遠離文學劣作”;成為文學編輯以后,又成了“庸才殺手”,呼吁編輯群體任性、刻薄一點。此外,何同彬雖擔任了一些詩歌獎的評委,仍堅持認為詩歌榮譽造成了詩人與現實之間反諷的、矛盾的關系。從此前的《重建青年性》《浮游的守夜人》,到即將出版的《重新學習“火種”和“盜術”》,縱觀何同彬的批評實踐,他始終以充滿反思的眼光,打量自身所處的文學現場。無論處于高校或期刊等何種位置,他都是具有異時代性的同代人。
這種充滿“敵意”的考察,往往選擇了劍走偏鋒的方式。如同“卡利古拉”對既定秩序的反叛,何同彬的批評方式,是把問題推向一個極端,在追溯與提問中清理:“追問只是開端,我們應該回溯得更遠一些、更深一些、更極端一些。”為了讓人們充分“了解你的時代”,凸顯“真問題”、作“真反思”,何同彬常常在猛烈的追問中問倒他人,也問倒自己;戳穿了當下文學主體的“演員”性質的同時,也“無比厭惡”地發現了自身的“戲服”。
對何同彬來說,文學批評是對一種層層累積的生活的突圍,他大致有三條突圍的路徑:
其一是通過分析八十年代以來啟蒙話語的構造及其遮蔽,再次回到起點,重申“什么是啟蒙”。在對中國啟蒙話語的重審當中,他不止是在救亡和革命的理路中確認其意識形態旨歸,也指出九十年代以來大學制度下的知識化、理論化、學術化和歷史化,作為一種“語言的塵土”,如何蒙蔽了啟蒙的公共性,使之變為混雜幽秘的私人性的話語操練。何同彬以其強力意志,要求重設啟蒙的公共性標準:重建一個真實有效的公共空間。
其二,以重建公共領域為立足點,不斷拆解神圣儀式與集體默契的批評話語。對何同彬而言,虛假的文學實踐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自我戲劇化”。比如他認為詩歌藝術所主張的“內在的公共性”“詩性正義”,和知識者把原本明晰的啟蒙概念模糊化、晦澀化并無二致,都是封閉而抽象的私人表演,屬于“無限的少數人”。其自我陶醉的快樂是“無關緊要的”,構成了對啟蒙公共性的消解。因此,何同彬的詩評大多采取“題外話”的方式,從文本來到外圍,關注詩人的生活與詩歌之間的縫隙。他不斷拒絕有所粉飾的“逃逸”,將現實疼痛聚集起來,讓它從一種私人感受上升為公共議題。
更為重要的是,何同彬從當下詩人普遍的“中年寫作”,發現了這種私人話語的開裂處。在何同彬看來,文學書寫的中年性,不僅是青年與老年之間的一個雙重否定,其背后也標示了當代文化乃至文明進入了歷史的中年,而這一中年性本身是具有極強的消解性的。一旦遠離了公共空間,中年寫作的詩歌反抗姿態,很容易在逃逸中消解自身,或形成文學場一次“偽正義”的合謀或同盟。在同一層面上,何同彬的批評挑開了當前文學寫作的邏輯“破綻”:“朦朧詩”“第三代”所引發的“詩歌崇拜”,被揭示為毫無宗教獻身意味的“表演”,晦澀語言則是主體逃匿的“障眼法”;一貫被認為自由、反叛的“民間寫作”,在何同彬關于“邊界互滲”的描摹之下,也呈現出權力機制混雜、詩學偽裝與混亂的一面。
為了從根本上摧毀這種舒適安全的合謀、圈子或同盟,何同彬曾經提出“重建批評的尊嚴”,以期喚醒青年、喚醒“深夢”中的同路人:“仍然有必要,且不會因悖謬的丑陋而斷絕對后來的反抗者的召喚”。并且,他似乎試圖用這樣嚴肅的批評激起寫作者的羞恥心,讓他們的寫作變為“對羞恥感的回應”。
其三,做一個“有力”而未必“高明”的讀者,對于“力”的這種追求,導向了倫理的重建。與這一極端性追問的批評風格一致,他對作品好壞的評判標準也有鮮明態度與立場。但這一立場并不指向孤立的美學,作者在“極限性”的意義上,具有清晰的倫理認識。也許青年的極限性可以驅散中年的疲勞感,他所青睞的作者,往往選擇一種如同“極限運動”的寫作:不斷摩擦文學形式與內容的邊界。在此意義上,何同彬和這類作者的親和性是顯見的。而同樣地,無論批評家還是作家,如果漠視價值標準的建立,則很有可能會被他視為中庸和世故。
但這一姿態并不意味著何同彬的批評拒絕對話,反而是尋求更有價值的沖突與對話。這從他對黃孝陽小說《眾生·迷宮》、翟永明詩集《灰闌記》等作品的批評中也可以看出來。何同彬對黃孝陽沖擊小說語言書寫極限的激賞,根本上也是他對文學在內容上無意義重復的厭倦,對既定秩序的“災異”或破毀的渴求。這種對“災異”的練習展露的就是“卡利古拉”式的超出現實秩序的“最高法則或極限法則”,它引向“我們未被告知的命運”,將現實如同曠野一般真實的面貌鋪陳開來。顯然,這樣的分析已經超出了單個文學文本的范疇,而是要藉由一個節點控制住全面。用何同彬自己的話說:“必須越出‘極限’,站在‘天空’的基點之外,回到小說和寫作者的肉身,以架構一種追問和質辯的關系……一種有效的批評和對話,就是要呈現極端的‘個人性’中風暴一樣的‘事件性’。”
作為一種視野,“事件性”所呈現的結構,恰恰是對話得以發生的地點。也就是說,何同彬將這些有能力沖擊自身極限的文學文本,視作“事件性”生發的標志,而從中可能出現誕生一種真正的對話。何同彬對翟永明“新女性寫作”的批評更直接地呈現了這一事實關切,并且依然圍繞公共領域交流的限度來展開。他認為翟永明的“新女性寫作”所刻畫的,是差異性個體之間共通的感受。這種“共通性”具有毫不含糊、明確的極限。它昭示著個體之間命定性地隔絕,但交流也悖謬性地依賴于差異與分裂。就像何同彬在引文中常常改寫西方理論家的句子,不同的語境之間存在可分享的經驗,但必須穿越石塊般的不可消化的間隔。
這也正是何同彬“極端性”批評觀念的出口,即讓私人在一個有意義的空間當中發生聯系,不再停留于自我戲劇化的慰藉中,而是確立一種公共的對話和參與。唯有這樣,代表私人感受的文學藝術才具備真正的(而非所謂“內在的”)公共性。何同彬的批評,不管是倡導“直言”“字里行間的寫作”“不合時宜”,還是自嘲“粗魯卻誠實”“武斷”“題外話”,都同樣把真正有意義的文學藝術與批評,定義為對生活的參與和拓展。這種態度堅硬而不可商榷,沒有模棱兩可的余地,而且敢于面對既成的失敗。
何同彬所重塑的批判力和感受力,如同卡利古拉般迸發一種摧毀陳舊秩序的強力,以最嚴厲的倫理價值去質詢自我的矛盾,不斷回應著當下對公共性的渴求。在這個意義上,何同彬確實如同卡利古拉,如同這位古羅馬皇帝,是一位帶著激情與厭倦的“暴君”——就像對于卡里古拉的評價,既然“人不理解命運,那他就“裝扮成了命運”,讓人看清命運的面孔。
回到文章的開始,何同彬對于酒的“過敏”,也許更可能的原因,是沒有任何一款“酒”辛辣到足夠刺激。也許,在文壇盛宴上不合時宜地端起碳酸飲料的朋友,擁有著最為狂野的靈魂,一切都如此顛倒,這才像文學。但不得不說,刺激,如同酒精本身,也會上癮。何同彬的文學批評,給我們展現了永遠的“青年”,這在過于成熟的年代,無疑彌足珍貴。但永遠的“青年”,也意味著永遠地拒絕“中年”的入口,拒絕了“人到中年”的隱忍與沉默中,未必表露出的曲曲折折的堅持。我有時候覺得,何同彬改寫了——他難以改變改寫名人名言的“惡習”——他所激賞的魯迅先生,肩住閘門,放出了一群中年人,他和“青年”們選擇留在原地。這里無疑有何同彬的迂直,以及這份迂直所包含的殉道般的代價。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