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文學需要表現人性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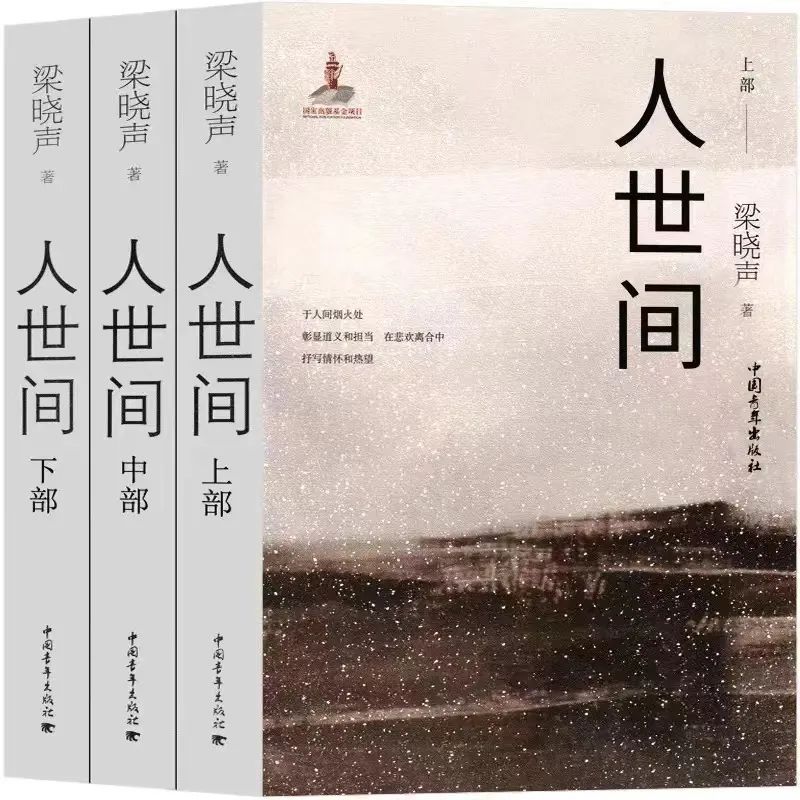
一、為眾生寫作,天然地帶有一種感情
陳智富:請您談談早期閱讀與文學觀形成的關系吧。
梁曉聲:寫作觀念跟閱讀的關系很密 切。一個作家最初接觸哪些種類文學作品與文學品相如何,以及接觸的時間有多長, 對寫作者以后形成的文學觀念是有影響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大約也就二三十部,如果一個人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讀,到初中畢業時就幾乎讀完了。再加上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作品, 以及以十八、九世紀啟蒙文學作品為主的世界文學名著譯本。于是構成了我這個文學愛好者涉獵古今中外文學精品的多元閱讀史,為以后創作與文學觀形成奠定了最先的基礎。
魯迅先生曾對年輕人說過,閱讀的范圍要廣一點,不要僅限于讀自己喜歡的哪一類及哪一個作家的作品。比如你是寫小說的, 不妨也讀散文與詩,也讀讀報告文學、聽聽歌曲、欣賞畫作,這些都有可能形成文學理念。我不認為,一個沒有欣賞繪畫等藝術眼光的人,一個不常讀書、不知道別人已經寫得很好的人,在創作上會走得多遠。之所以要持續閱讀、要關注文壇動態,不是要跟著別人走,而是為了解情況后寫出不同個性的作品。
陳智富:您覺得一個有抱負的作家應該保持怎樣的寫作態度?
梁曉聲:1949 年以前的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是著名的傳統文化學者,以五四新文化先驅自居。有一次講課,他的學生希望他講講文學創作理論。之后一次上課,他在黑板寫下了“觀世音菩薩”五個字予以闡述。觀,是指觀察。世,是指入世和出世兼備的 生活態度。大眾保持入世的態度生活,作家也應保持入世的態度看待生活,不能過于出世。音,是指語言修辭要有抑揚頓挫的美感。菩薩,是指作家要有一顆救苦救難的菩薩心腸,即悲憫情懷。
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留下好作品的作家都有一顆積極入世、關注眾生、溫暖人心的心靈。蒲松齡是這樣,雨果、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都是這樣,寫《苔絲》的哈代、寫《紅與黑》的司湯達也是這樣。
但是,有誰天生就有菩薩心腸呢?文學作品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心靈。當你讀了多部優秀且有人性有溫度的文學作品,你像是文學修道院里的一個修行者,你的心靈變得柔軟了,同情心更強了。你看到路邊流浪的小貓小狗冒失地過馬路,會生出慈悲心,心想可別被車壓到了。《人世間》中寫到一個叫光明的孩子,原型就是我上中學時路過太平胡同時經常看到的孩子。生命只有一次, 他自出生就是盲人啊,對色彩沒有感受,連爸爸媽媽長什么樣子都看不到,太不幸了。 我同情,卻幫不了他,不可能不產生悲憫, 他的樣子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我想擺脫這種困擾,心想有一天要將他寫到我的作品中。創作《人世間》時,我很自然地將這個人物寫入了。我下筆的時候,會覺得為眾生寫作,天然地帶有一種感情。寫完后,那個盲少年的形象就從我的腦海中移出了,成了文學人物,有了文學命運與心靈。我覺得, 如果作家缺乏對生活、對他者、廣而言之對命運、對社會的觀照,將文學創作理解為一 種可單憑技巧進行的事,無論技巧多么熟練,未見得能持續寫出好作品來。
二、電影似乎比文學更強調塑造人物
陳智富:您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之前,曾長期在北京電影制片廠、中國兒童電影制 片廠工作。這些電影制片工作對您的文學創作應該產生重要影響。請您談談電影與文學 的關系。
梁曉聲:我的文學創作跟我在電影界工作 20 多年有關;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 12 年,在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任藝術委員會副主任有 14 年,當時的主任是電影前輩、 演過江姐的于藍。她的先生是北京電影制片廠廠長田芳。我跟于藍、葛優的爸爸媽媽、 陳凱歌的父親都是同事。雖然我那時年輕,到他們家里談工作,葛優、凱歌就自動規避。我與水華、謝鐵驪、凌子風等中國電影界的 大師也產生過工作關系,他們也為中國兒童電影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和他們接觸主要是談論電影。這些工作經歷給我一個重要啟發,就是電影要塑造人物。
電影和文學是有共通之處的。我覺得,電影似乎把“文學即人學”的理念提得更高,比文學更強調塑造人物。我當時作為年輕的編劇參加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年會,每次年會一般要討論十三四部作品。根據什么來判斷一個劇本是否值得投拍呢?就是要看有沒有立得住的人物,是否塑造了一個或者幾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之所以說一位導演、演員的成就令人尊敬,是因為他為中國電影藝術畫廊增添了一個形象成功的人物;當年的電影理念如此。
就我的閱讀經驗來說,凡是好作品必 然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作品人物的名氣往往大于作者的名氣。如果我心里沒有最初的人物形象是很難動筆的。
我的全部小說都是為了塑造人物,一切情節和細節都是為塑造人物而服務的。早期 的電影相當注重細節,細節更是為塑造人物服務的。現在很多編劇想得更多的是故事,殊不知故事是需要人物來參與的,而不是相反,人物變成了棋盤上的車馬炮,被故事牽著走。許多電影在有限的時段,塞進更多情節,不斷地制造矛盾沖突,以滿足觀眾需要。一些年輕編劇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寫故事的執念。
我有一個時期對故事曾有極強的排斥心理,特別是接受采訪時常會被問到:講一兩個有意思的故事吧。我往往懷疑,這是否意味著大眾只要聽故事呢?是否小說和影視創作就是編故事呢?事實上,許多電影的故事性是三言兩語無法講清楚的,但是人物在那兒啊。某些經典電影和小說一聽名字就是講人物的。如果要求編劇用最簡潔的語言講一下它們的故事,恐怕有點強人所難。
《人世間》是虛構的,但是我希望讓讀者讀到 20 頁以后最多讀到 50 頁時,忘記是 在讀一本小說,而是進入了一片生活,這片生活和他似乎有著一種熟悉的關系。為此,我要克服“顯示”深刻的想法,我要打消暗示讀者這段文字很漂亮的念頭 :我沒有什么了不起,誰比誰更深刻呢?《人世間》寫了一個情節,金老太太坐輪椅到了大院外,在窄路上遇到素不相識的周秉昆,周 秉昆貼墻而立讓行。金老太太讓推 輪椅的阿姨停下,倒回去,跟周秉昆說謝謝。這就把這個人物的基調定了下來。這就是我們講的細節,它不是沖突,不是矛盾,它是生活。文學作品畢竟不是原本的生活,當然要突出矛盾沖突,矛盾是生活的一部分啊,生活中的矛盾沖突有時也會具有戲劇性啊,但是一定要用生活的氣息把矛盾沖突包裹起來,使它像是發生在生活的原態之中,讓讀者感覺到是生活在呈現,而不是赤裸裸的矛盾沖突的編織。現在的創作問題可能在于,過分強調矛盾沖突,把和生活有關的東西略去了。很多影視作品缺少生活的質感,故事像是光禿禿的樹干,為沖突而沖突。
三、破題:從小說到影視
陳智富:您剛才談到寫作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那么與作家自身的個性是否有密切關系?
梁曉聲:我覺得是有關系的。我少年時看過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木木》。小說寫到——莊園里有一個叫做蓋拉辛的又聾又啞的農奴。蓋拉辛經歷了戀愛的失敗,和其他人也無法交流,就養了一條叫木木的小狗,并視作“養女”,兩個生命個體建立了深厚感情。一次,木木沖著女地主叫,女地主要農奴蓋拉辛將小狗“處理掉”。蓋拉辛萬般無奈,不得不劃小船到湖中心,在船上慢慢地給小狗木木系繩套,木木充分信任主人,以為主人跟它做游戲。雖然小狗是蓋拉辛唯一心愛的生活之伴,但只要主人說“處理掉”,他就不得不順從。作為農奴,蓋拉辛已經喪失掉了維護個人權利的任何本能。第二天,農奴蓋拉辛從莊園消失了。因為這篇小說,俄國展開了若農奴離開莊園何以為生的大討論,推助了取消農奴制的呼聲。這篇小說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是短篇的經典 ;但其思想性是由人物體現的。
我讀后,還專門寫了散文記錄這段閱讀的回憶。為什么我的閱讀印象如此深刻?與我的個性有關,我很喜歡小狗,甚至在手機頁面存著小狗的照片。我讀小學的時候養著一只小狗,我和弟弟妹妹每天把自己的飯分出一點來養小狗。我喜歡小狗,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究竟幾何?我覺得經常把小狗帶入我的作品,起到了特別的文學效果。我即將出版的《父父子子》中,有小狗的形象出現。 我早期作品《今夜有暴風雪》中,也寫了一只叫黑豹的狗。《人世間》里也寫了一只小狗。老父親在去看望周蓉的路上,無奈地買了一只小狗。我在跟導演說劇本的時候說, 強調這個情節一定要保留,它很重要。如果 只是局限于寫故事的話,編劇會說這個情節游離于故事之外,游離于矛盾沖突之外,因此有什么意義呢?而我認為,小狗對于塑造人物很重要,并非閑筆。實際上,那集的觀看量挺高。后來小狗長大了,宋佳飾演的周 蓉因為害怕狼松開了繩,將小狗放進原始森林。據說,網絡播放平臺下面還有一堆批評宋佳的留言——我認為電視劇中那個情節簡單了,對塑造周蓉反而不利。
陳智富:您先后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茅盾文學獎, 在當代作家中并不多見。您對獲獎這件事怎么看?
梁曉聲:作家的創作心態至關重要。評獎自有一套模式。作家沒法預估。如果奔著得獎而寫作,一開始就錯了。得了一次獎, 還想再得獎呢。得過國內獎,還想得國外獎呢。雖然抱著得獎的心態去寫作不排除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不可能在文學道路上走得更遠。我大約三十四五歲的時候,《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父親》分別獲 1982 年及 1984 年全國中短篇小說獎。文學界曾有一個說法,1984 年是梁曉聲年。《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原刊于《北方文學》 雜志。這個雜志不是北京的重要刊物,而是 黑龍江省的偏遠刊物。我寫這篇作品,根本沒想獲獎的事,如果想了,可能會投給北京的刊物發表。恰恰是我沒想得獎,就會全部 心思地寫好人物。記得頒獎的時候,蔣子龍跟我說,對不起,你的作品應該排第一的, 但是考慮到你太年輕了,所以讓你屈居第二。這都是玩笑話。我并沒有把得獎看得那么重。
四、蒲松齡的一篇小說感動我
陳智富:您的不少作品都是橫跨幾代人、長達幾十年的鴻篇巨制,在謀篇布局、構造結構等方面獨具匠心且卓有成效。您覺得,作家在創作長篇小說如何選擇合適的視角?
梁曉聲:合適的視角當然很重要。每一 部作品都是不一樣的。比如我 11 月要推出的長篇小說《父父子子》,寫作時間跨度從 1937 年起到上世紀 80 年代初,寫了幾代人的故事。大家可能會很困惑這么長時段的故 事,怎么壓縮在一部小說中呢?就得有視角的變化。比如,上一章以作者的視角寫父母親的經歷,到了下一章以兒子的視角寫“我” 的經歷,這樣就可以最大程度選擇合適的素材,作品節奏就會推進快一些。
陳智富:您曾提出“好人文學”的概念, 寫作中也特別著意于人性美的挖掘與頌揚, 《人世間》中的周秉昆無疑是“好人文學” 的典范。請您談談文學與人及人性的關系。
梁曉聲:我在大學教書時向學生布置作業,總是強調先寫親人吧。有的同學交給我的作業,洋洋灑灑八九千字,大抵寫的是交待性的寫親人,自己怎么逛親戚,基本就是寫到這個層面,就沒了,人物形象立不起來。筆鋒一轉,便開始寫自己了,仿佛自己和親人之間,自己才更值得寫。我就問,親人怎么寫丟了?不管是魯迅的《阿 Q 正傳》《祝福》,還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塑造人物的。
我關于文學創作最基本的理念,跟現代派的主張不一樣。文學即人學,永不過時,這個“人”不是抽象的普羅大眾,不是抽象的所有人。作家寫自己關注到的一些人、事的感受,呈現一段人生給更廣大讀者看。人們為什么要讀小說呢?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自身所接觸的有限現實來了解更廣的現實生活。
我曾經和李敬澤有過一次對話,談到了苦難這個話題。我說,別人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可能會認為我經歷過某種苦難的歲月,但我并不感覺那是苦難,也不愿 用“苦 難”兩 個字,那只是經歷而已。窮愁經歷而已,與“苦難”并不統一。
讀文學作品是了解他人命運的一種方式。誰愛情受挫,職場失意,買彩票沒中獎,會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是當 你讀作品多了,會不再覺得自己的人 生是最失意的。一個作家也不會再為自己得獎而洋洋得意。以對社會的貢獻 論,科學家、醫 學工作者、社區管理者、片兒警、快遞小哥等在實際生活中默默無聞的實際貢獻,絕不亞于作家的貢獻。作家比其他行業的人又了不起到哪里呢?所以,我提出 “好人文學”的概念。
事實上,我筆下的青年都有好人的那一面,這跟我的閱讀史密切相關。我讀《聊齋志異》,其中《王六郎》這個故事讓我震撼。一個漁夫在河邊垂釣偶遇少年王六郎, 二人經常在河邊飲酒。一天,王六郎告訴漁夫,今天是最后一次共飲,明天他要去投生。 漁夫懷著很大的好奇心,隱在河邊觀察投生是怎么回事兒。有一位母親抱著一個孩子向河里走去,三次都被大浪打回岸上,最后沮喪地離開。隔日,王六郎又來到河邊與漁夫共飲。漁夫覺得奇怪,問怎么回事。王六郎 說投胎沒投成,說昨天是母子二人,我不能以自己一命來換對方兩命。下次投生的機會可能在幾年之后,可能在百年千年之后,也可能永無投生之日。漁夫大敬,引為知己。 蒲松齡寫出了人性無私的最高境界,全世界的作家恐怕無人能出其右。我極受震撼,心想 :蒲松齡能寫一篇小說感動我,我能不能也寫一篇小說感動別人?當這樣的作品多起 來,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會不會有一種很好的文化促進作用?
五、現實主義文學寫人,實際上有兩種
陳智富:您踏入文壇之初,寫出了《這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年 輪》等一系列知青小說代表作,直到今天仍然筆耕不輟,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自始至終都秉持著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請您談談現實主義文學創觀吧。
梁曉聲:我曾經看過一個民間故事。獵人海力布在深山打獵,救了一條小白蛇,小白蛇是龍王的女兒。龍王為了報答,決定賦予海力布能聽懂百鳥百獸語言的能力。龍王告誡海力布不可對任何人說出這個秘密,否則會變成石頭。一天,所有動物都在奔逃,海力布聽懂了動物們的語言,知道洪水要來了,也動員部落逃離。但人們都不相信,海 力布不得不實話實說,結果在說話的過程中,從腳底到頭慢慢變成了石頭。這個民間故事,也給少年的我一種震撼。我從小多次問自己,世界上有這樣的人嗎?我能做到嗎?我不能。但是,文學故事有時候就是要寫到 生活中的不可能。
還有高爾基的《丹柯》,寫到部落在冬夜遷徙,丹柯剖開自己的胸膛,捧出心臟當做火把,照亮了前行的路。隊伍前行了,丹柯倒下了,丹柯的心被無數腳步踏碎了,變成了小星星。這小說也感動了少年的我。人性在作家筆下,不應僅是丑惡、歹毒、極端 自私與邪獰的。又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 檻》,寫一個女青年打算推開某扇門,有一個聲音問著 :“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作什么? /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東西在等著你? /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 疾病,甚至于死亡。”女青年回答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如果她推開那扇門,將失去親人,失去愛,甚至失去生命,她一次次被叩問,仍回答要推開那扇門。屠格涅夫寫這首散文詩時正是俄羅斯處于大變革之年代,的確有一群女革命家投身于革命運動。我們中國大變革時期也有這樣的女青年。歷史并非虛無,也不是史家一廂情愿編出來的。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英雄,為了民族的明天義無反顧地坦然地犧牲了自己。比如,譚嗣同留下《獄中題壁》絕命詩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樣的英雄人物是存在著的。雖然不是我們,也不是我們認識熟悉的人,但不要以為沒人做得到。
現實主義文學寫人,實際上有兩種:不僅僅應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還要寫人在現實中為了責任和使命應該怎樣做、能夠做到什么程度。歷史乃從前之現實。“文學即人學”,實際上就是這兩種文學創作的結合。 如果文學寫人只寫在現實中大抵怎樣,是有局限的,等于只寫了一半的現實。現實主義文學寫人不僅僅有阿 Q、祥林嫂,還有王六郎、海力布、丹柯等,譚詞同等。
再舉個例子。我曾在《知青》小說中寫過一個細節——有一名男知青由于參加紀念周總理的活動,被有關方面逮捕了。他的知青朋友們在勞動的時候看到警車載走了他的排長,就將警車攔住。他們說,只想和排長見次面,告別一番。不少編劇認為不可能,現實不是這樣的。現實應該是,連長一聲令下,大家便都不敢那樣了。但是我告訴他們,你們所了解的現實是差不多的,你們認可了那樣的現實,而我不認可。難道在實際生活中,排長很好,我們不應該送送嗎。文學作品可以強調人在現實中大抵怎樣,但也應關注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能夠怎樣的寶貴少數。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曾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死在他的學生費孝通的懷里,費孝通就是不怕牽連,現實中就有這樣的人啊。現實中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你以為你知道的就是全部嗎?有些作家對現實的認識很局限,認識不到位,寫人物想當然地排除掉了另一些可能性,沒有對人性的全方位關注。
優秀文學作品其實都閃爍著人性的光 芒。托爾斯泰的《復活》,寫到男主人公的懺悔。那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多見,但是不能因為少,就自動認為那樣的人不必是文學關注的存在。恰恰相反,文學需要弘揚人性之善,揭示現實生活中有弘揚人性的善的文化影響。
《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被沙威追捕,沙威從屋頂滑下時,冉·阿讓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被追捕的人救了追捕自己的人,這個細節是偉大的細節。在現實中能夠像冉·阿讓那么做的人肯定很少。雨果寫出了人作為人的心靈的高貴的一面。所以,我們認為雨果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
人是什么樣的?是欲望的容器,一杯子欲望而已嗎?人不應也自己理性的教師嗎?人有家庭親情,還有家國情懷,多少仁人志士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肝腦涂地。這都是 由真實的事跡證明了的。我就不認為這是宣傳,我對那些英雄人物肅然起敬,這構成了 我對人之存在的思考的方位。
我有了這些思考,寫人時總是在想: 我做不到英雄那樣,做不到王六郎、丹柯、冉·阿讓那樣,我還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做到一個有溫度的好人嗎?我還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做到一個周秉昆嗎?這就是我的邏輯。
關于文化和人的關系,我說過四句話,第一是根植于內心的修養 ;第二是無需提 醒的自覺 ;第三是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 ; 最后一句是“為他人著想的善良”。起碼在 我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出版關系中,我做到了。我經常提醒他們,現在《人世間》銷售好,也不要沖動,不要多印,克制一點,不要積壓在那兒。
我講了這么多,似乎是說要通過文學作品影響教化別人。其實,寫作的過程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總是感激文學,因為在閱讀、創作的過程中,文學像是無數的智者、善者,耐心地教育著創作者。
- 動畫版《三體》能否滿足市場期待[2022-11-07]
- 梁曉聲 :用文學傳遞人間溫暖[2022-10-08]
- 拓寬文學價值 激發創造活力[2022-10-04]
- 梁曉聲在湖北談文學創作[2022-09-27]
- 梁曉聲:我的父親母親[2022-09-06]
- 湖北籍作家新作投拍成影視作品[2022-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