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琺:G6高速上的班馬與一個(gè)仰望的角度 ——讀《北緯四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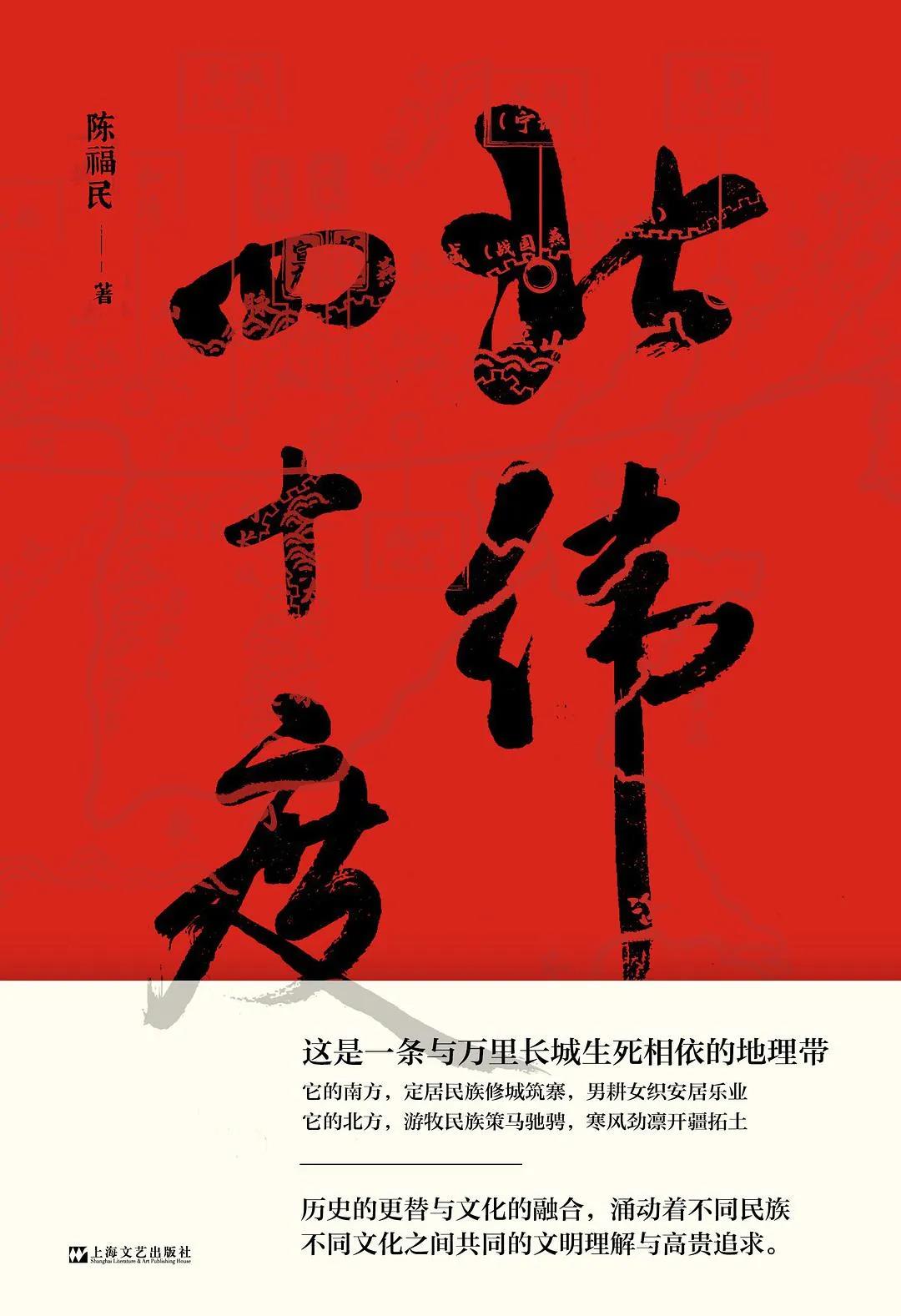
陳福民《北緯四十度》
北緯四十度線上,今河北唐山那里曾有一個(gè)孤竹國,存續(xù)到商周之際,因?yàn)橥瑫r(shí)出了兩個(gè)都不想做國君的王子而天下聞名。后來那兄弟倆一起隱居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采薇至死,遂被千年之后的司馬遷置于《史記》七十列傳之首,通史中人物群像的開篇者,亦可以算作漢語傳記人物的發(fā)端。他們的名字叫伯夷和叔齊,伯和叔是排行字,也就是當(dāng)今所謂老大和老三,他們常常被合稱為“夷齊”。有時(shí),伯夷也會(huì)被置于堯時(shí)代的著名隱士許由之后,把這兩個(gè)人當(dāng)作不世出的高人代表,并稱“由夷”。這樣做是合乎順敘慣例的,倒過來若是喚作“夷由”,那就奇怪了,要變形成鼯鼠即大飛鼠的別名了,參見中國最早的詞典《爾雅》。
時(shí)間上下游之間的關(guān)系殊難違抗,我們無法讓時(shí)光倒流,歷史表述也由不得顛來倒去。但我卻曾注意到有個(gè)例外:上古兩位最著名史家、《史記》和《漢書》兩本書的作者,在后來的歷史上少稱“馬班”,而多謂“班馬”。就譬如《晉書》:“丘明既沒,班馬迭興。”為何先舉東漢班孟堅(jiān)(公元32-92年在世),再提西漢司馬遷(公元前145-?年)?說法不一,有更合乎歷史邏輯的理由,傾向于是文史間的競標(biāo)所致: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往往揚(yáng)司馬遷而抑班固,更傾向《史》、《漢》并舉;但在史學(xué)領(lǐng)域,班蘭臺(tái)之謹(jǐn)嚴(yán),又常被認(rèn)為改良了太史公的疏狂與草創(chuàng),所以“班馬”正是后來居上的價(jià)值判斷。
當(dāng)然,如果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尺度,這實(shí)在是個(gè)太細(xì)小的問題,甚至可能會(huì)淪落到“兩小兒辯日”、“日近長安遠(yuǎn)”之類的辯術(shù)中去,司馬遷與班固或許都不會(huì)太在意于此。須知,他們二位都有通史的野心,司馬遷無須多言,《史記》已然實(shí)現(xiàn)通史的闊大;而班固吃虧就吃在生得晚,或許他已經(jīng)生有“既生班,何先生馬”之嘆亦未可知;班大體上繼承馬創(chuàng)下的紀(jì)傳體之后,零敲碎打地做了不少體例上的調(diào)整。少為人知的是,他把《史記》中的“書”改成“志”體之后,都大體實(shí)現(xiàn)了通史的規(guī)模;表中的“古今人表”也是一個(gè)絕唱的發(fā)明。只是后世讀者往往囫圇吞棗,徑將一部同樣胸懷大志的《漢書》簡單等同于它的諸多斷代史后裔了。按照宋代黃庭堅(jiān)的說法:“文章最忌隨人后。”但先生在起跑線上天然就領(lǐng)先于后生,后生太難以擺脫在資料、視野以及表達(dá)方式上對(duì)先生的踵武,這就是歷史本身,也就使得“通史”——把歷史從古而今地悉數(shù)勾聯(lián)起來敘說得首尾周全的做法,變成個(gè)越來越困難與繁重的任務(wù),多少有雄心的歷史學(xué)家都不再落實(shí)這一野望,而漸漸縮若秋毫,深入作業(yè),關(guān)心皮毛之下的微觀如毛血細(xì)管中的狀況,宏大敘事久不作矣。
我在陳福民《北緯四十度》一書中卻再一次隱約看見關(guān)涉通史的壯志。這真是一種久違的氣息。全書十一篇,除了《遙望右北平》圍繞著一個(gè)北緯四十度上的昔日舊地標(biāo)(北平-北京也正是作者的立足點(diǎn))重新展開歷史,像一枚鎮(zhèn)紙一般置于卷尾壓軸;前十篇,依次分別備說趙武靈王、漢高祖劉邦、飛將軍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王昭君、劉淵、安祿山、北魏孝文帝元宏、宋太宗趙光義、明英宗朱祁鎮(zhèn)及其所在時(shí)代的人事。這本近五百頁的書當(dāng)然稱不上也無意于成為一部真正的通史,但畢竟書中也提到了趙武靈王之前《詩經(jīng)》即吟誦過的“不遑啟居”、“靡室靡家”的“獫狁”——古匈奴——之故;并言及17世紀(jì)及之后的滿清事跡,有顯有隱,有張有弛,有繁有簡。而書中前十篇——十頗能與《史記》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及《漢書》百篇相呼應(yīng),是一個(gè)完整的數(shù)字——所及為世人耳熟能詳?shù)娜宋锘蚴菤v史轉(zhuǎn)折點(diǎn)上的關(guān)鍵,或是歷史延長線上的重心。敘事抒情須以人物為中心、而非事情,這樣的文學(xué)認(rèn)知,放到當(dāng)代依然常常有效;而這更是自司馬遷開始的古老傳記傳統(tǒng)。因此,它不僅是串珠,還仿佛是時(shí)間線上一場跳島戰(zhàn)術(shù)的演練,順流而下,關(guān)聯(lián)起從上古到近古漫長階段中的時(shí)代變遷與文明接續(xù)。
但倘若僅僅只是歷代人物的群像,歸為名人傳的序列或是更合適的,西洋有普魯塔克(Plutarchus)希羅相映的傳統(tǒng),漢代有文獻(xiàn)學(xué)宗師劉向《列仙傳》、《列士傳》、《列女傳》的先例;而本書的立足點(diǎn)與視線,顯然還不止于此。正如“跳島”這個(gè)比況的喻體所暗示的,逐章進(jìn)展,一系列位移行動(dòng)拖拽出真切的空間感,一條更為明晰的“線”躍然而出。這正是作者毫不隱諱,堂堂標(biāo)在書名上的:他進(jìn)行長時(shí)段的歷史關(guān)注、從漢文明的延續(xù)過程中拈出“北緯四十度”,一條劃然筆直的線。這條橫空落實(shí)在地形地貌上的概念之線區(qū)分出農(nóng)耕部族與草原部族的星野,而又在古典文獻(xiàn)中提舉牽引出一系列彼此攻防進(jìn)退的實(shí)據(jù)化為今用,我們關(guān)于中國史的漫漶注意力、無窮的線索、多樣的闡述由此薈聚在一起,確立為一種漢匈相競、南北拉鋸的秩序。而且這還包含了一個(gè)隱而不發(fā)的上層前提:北緯四十度從屬于地球的視野系統(tǒng),因此既是南北方向上的坐標(biāo),又暗示著東西尺度上跨經(jīng)度的橫絕。
北緯四十度不唯是單向度的標(biāo)準(zhǔn),這也跟作者陳福民的身份、用心、工作方式以及落實(shí)在文字中風(fēng)格上的經(jīng)緯關(guān)系頗能相映。在這部看似以歷史敘事與評(píng)議為主的厚重之作背后,首先必須點(diǎn)明,作者不是個(gè)浸淫于故紙的史部深耕者,而是一位長期游弋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批評(píng)家。慣熟上我們會(huì)重復(fù)“文史不分家”的陳說,這當(dāng)然也在文學(xué)歷史中反復(fù)得到回響與認(rèn)同:不論是論尋求敘事的方式,還是還記憶以真相、記經(jīng)驗(yàn)之形態(tài)的目的,文史之間的藩籬或許本該是臨時(shí)的便宜,以及后世管理學(xué)與分類學(xué)上人為造成的結(jié)果;但不可避免的是,隨著各自傳統(tǒng)的推進(jìn),彼此都添磚加瓦筑起高墻,甚至在墻的兩側(cè)亦多修垣堵,把空間切割得更加細(xì)密,不斷在種植收獲成果時(shí)壘土,使“隔行如隔山”。尤其是進(jìn)入學(xué)術(shù)體制的歷史研究,通人漸少而專家在各個(gè)精致的小房間里麕集。高墻的另一側(cè),創(chuàng)作及批評(píng)領(lǐng)域的情況并沒有好到哪里去,文學(xué)作品日漸一篇篇浸泡在瑣碎的私人領(lǐng)域,或者在心理學(xué)時(shí)尚的推波助瀾下進(jìn)入人心探幽燭微,對(duì)小宇宙的興致中是不是挾帶著我們?nèi)粘,嵥榈膶?duì)人陰私的窺視欲不好一概而論,但確實(shí)是棄守了對(duì)大宇宙的觀察慣例。就小說來說,使之側(cè)重于街談巷議的“稗官”一面,而疏略了其“野史”的那個(gè)張揚(yáng)肆意評(píng)點(diǎn)江山的向度。“日不顯目兮黑云多,月不見視兮風(fēng)非沙”(敦煌漢簡《風(fēng)雨詩》,英國探險(xiǎn)家斯坦因發(fā)掘哈喇淖爾南岸所得,今敦煌市經(jīng)緯度:東經(jīng)92°13′-95°30′,北緯39°53′-41°35′。)。個(gè)體經(jīng)驗(yàn)?zāi)J(rèn)成為作品的邊界,時(shí)代的溫室遠(yuǎn)離山河,在高樓與都市中,風(fēng)沙與日月都消隱了身形。
但也總會(huì)有“老翁逾墻走”,富有經(jīng)驗(yàn)的魔術(shù)師或謂老法師通曉穿墻術(shù),這既是一個(gè)悠久的志怪主題,還會(huì)屢屢在當(dāng)下眾目睽睽地付諸公共的文藝(譬如大衛(wèi)?科波菲爾在1986年時(shí)候表演過穿越長城)。《北緯四十度》中,作者不止一次直陳他對(duì)文學(xué)的批評(píng)意見。他指出,“公眾讀者的歷史觀并不是通過歷史學(xué)習(xí)去獲得,而是在文學(xué)虛構(gòu)與民間故事當(dāng)中完成的”(自序P5),頗能一語中的,這正是漫長文明傳統(tǒng)中的一個(gè)悖反命題,自史詩開始,到演義說部,文學(xué)似乎一直是歷史教育的更重要形式,史官的身影及其成果被藏之名山、束之高閣、收在秘府靈室,只在一個(gè)小眾的范圍之內(nèi)隱秘傳承。傳統(tǒng)社會(huì)囿于書籍傳播方式的不夠發(fā)達(dá),但到了現(xiàn)當(dāng)代,其理由當(dāng)然不能繼續(xù)成立,而現(xiàn)象依然,這正是出現(xiàn)如《北緯四十度》之類的歷史書寫的時(shí)代動(dòng)機(jī)。陳福民在自序中即提到本書是“個(gè)人的一次文學(xué)歷險(xiǎn),也是對(duì)歷史學(xué)的致敬”(自序P6,這句話可以被視為是在向“成一家之言”致敬)。他既有正本清源的敘述動(dòng)力,警惕“歷史的真實(shí)而沉重的分量,一般來說敵不過經(jīng)由修辭裝飾后的文學(xué)故事的非凡魅惑力”(P6),“呼吁人撥開修辭去努力看到歷史真相”(P327),也“始終是把歷史學(xué)家作為潛在讀者”(自序P4)。
我們可以再次提到前引“班馬”一例,這個(gè)詞的成因歧說,還可以折射出文學(xué)往往如何對(duì)史學(xué)構(gòu)成了歪曲,顛倒了時(shí)間秩序:有一種意見認(rèn)為,它是順服既有詞匯的結(jié)果,為招引更有名的聲響,即在詞法層面上屈從于固有范式,而吊詭的是,史學(xué)文獻(xiàn)在這里又成了文法的養(yǎng)料:是左丘明《左傳?襄公十八年》最早引有“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之句,班馬就此成為離群之馬的稱謂,與孤雁哀鴻相侔,成為值得一再抒情的美學(xué)意象。譬如李白,更有名句“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甚而到了近代,有可能是因由“班馬”而格義出了“斑馬”,而不把zebra譯作“條形馬”——這個(gè)假說當(dāng)然需要再考據(jù)。相較之下,更令人信服的一種說法來自音韻之美的考量:說漢語聲調(diào)平上去入的順序強(qiáng)勢(shì)甚于歷史邏輯,不論是文學(xué)史上的李(白,701-762年)、杜(甫,712-770年)、蘇(軾,1037-1101年)、黃(庭堅(jiān),1045-1105年),還是本書(P122)涉及的衛(wèi)(青,?-前106年)、霍(去病,前140-前117年),碰巧都是時(shí)間與聲音的合流;而偏偏“班馬”不是,平聲的班字遂能凌駕于上聲的馬字之上。
另一種也把歷史搭上的看法則認(rèn)為:先有班固與馬融(79-166年)因其時(shí)代相近,而又都有經(jīng)學(xué)史上的聲名成就,遂形成并舉,這個(gè)詞后來遭“敗壞”、被“篡位”或者活用,換成了司馬遷。甚至,太史公還不是終點(diǎn),到了唐宋一班文學(xué)家的筆下,把更早些時(shí)候?qū)憽蹲犹摗贰ⅰ渡狭帧分x的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年)拉來擱在寫《西都》、《東都》二賦的班固之后,譬如皎然論說辭賦稱:“屈宋接武,班馬繼作。”問題是,人家屈原與宋玉是師徒關(guān)系,而班固、張衡的西漢大賦無疑是接承司馬相如、揚(yáng)雄的前漢傳統(tǒng),由天子游獵題材轉(zhuǎn)而把目光移到京都繁盛的呀。可見文學(xué)確實(shí)因其虛幻的構(gòu)造而“劣跡斑斑”,多露馬腳。
我覺得,如果“班馬”是一個(gè)必答的二元選擇題,這本書的作者一定是更向班固、以及作為史官家族的東漢班氏譜系趨近靠攏的。書中李廣一文的結(jié)尾處,稍有遲疑之后,作者直言了司馬遷在世界觀及其他觀念上的史學(xué)短板和文學(xué)氣質(zhì)(P91-92)。西漢司馬遷因中年變故而從史學(xué)走向文學(xué),而史上班氏家族兩代人皆兼有史家與文學(xué)家的身份,卻堅(jiān)守著史學(xué)立場:且不說班固撰作大小賦卻有“質(zhì)木無文”的五言詩一面;班彪及其女班昭皆有述行賦作,《北征》、《東征》前后相繼,身體力行,旅途中一路激活歷史,把昔日往事與當(dāng)下見聞相疊合,延宕在時(shí)間里曾經(jīng)的悲歡之情,遂能淋漓為空間里的逶迤之態(tài)。比之兩千年前,今人著述與行走當(dāng)然便利得太多,《北緯四十度》也是壯游與讀史的合奏,依作者的夫子自道,“以歷史為經(jīng),以北緯四十度地理帶為緯”(自序P3),而那句著名的套語移用來此是真正恰切的,這正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實(shí)踐;甚至還有第三個(gè)句子,一個(gè)寫作者本分的達(dá)成:寫萬字文——是新的“東征賦西征賦”。
作者在書中提到,他出行的路線中有一段近乎直線,是沿著G6即京藏高速前一段北京到內(nèi)蒙古巴彥淖爾(臨河),他反復(fù)自駕,那即在北緯四十度,并且也與戰(zhàn)國趙北長城的位置相重。高速上的車輪聯(lián)通古今。“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北征賦》)。“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東征賦》)。北緯四十度因此就落實(shí)到長城這一舉世皆知的線條上。“望長城內(nèi)外,惟余莽莽。”書中一開始就把長城這個(gè)底翻出來了,《北緯四十度》整部書的基線與重點(diǎn)所在因此也得以豁然,在開闊的四十度線上,在長城與壩上的閎闊場景中史事明了細(xì)致。但我們不免也還是略有疑惑,因此“北緯四十度”會(huì)不會(huì)其實(shí)是一次老調(diào)重彈?無非“長城”換了套行頭,是不是以新的修辭來包裝起來的舊真相呢?以四十度線作比,是否過于順滑?以長城為喻,那么,長城上的雉堞呢?依山形來龍去脈隆起低落的那些迂回?cái)嗬m(xù)呢?
細(xì)讀下去,就知道不必?fù)?dān)心。書中掩藏著一些偶然的閑筆,還有一些巧妙的隱喻頗可一觸即發(fā)(散、引申),譬如談及明代那個(gè)歷史關(guān)節(jié)點(diǎn)的地名變遷: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鎮(zhèn)失手被擒之地,書中寫到,原本叫統(tǒng)漠,后來稱統(tǒng)幕,最后荒腔走板,訛作土木或土木堡(P418)。文學(xué)讀者很容易聯(lián)想到,這是先前某種主體意志一廂情愿的藍(lán)圖——正如“統(tǒng)”一大“漠”的雄心。其在《史記》中的表達(dá)方式是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見《匈奴列傳》;又譬如漢人冠名為“和親”的新舉措:和親的概念在先秦指和平相處、和睦相親的非戰(zhàn)爭狀態(tài)或戰(zhàn)后格局,在白登之圍后,才演變成以美女換和平——終如漢高祖白登之圍那樣,“統(tǒng)”帥的種種心思在遭受重?fù)糁拢煅跊]于重重之“幕”后,不可索解;但究其“土木”形骸,無非還是南方不斷感受到的“北風(fēng)那個(gè)吹”來的壓力,筑起長城,而后長城又不斷被突破的單線敘事。
因此我們不會(huì)把《北緯四十度》看作是重述與印證的簡單文字,書中提到:“我們用了前半生的時(shí)間通過文學(xué)故事去積累歷史知識(shí),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個(gè)個(gè)甄別推翻……”(P157)。作者在述說國史時(shí),自有一層對(duì)個(gè)人史的反思,絞結(jié)著求學(xué)與成長經(jīng)驗(yàn)的當(dāng)代史與從上古而降的漢匈史,在具體地理關(guān)系上兩相對(duì)峙、彼此審視,作者過往的文學(xué)認(rèn)知與批評(píng)的履歷,在這一次成規(guī)模的散文書寫中惕然成為反復(fù)自我敲打的對(duì)象。這促使作者抱著重估的眼光來給那些歷史人物點(diǎn)名:對(duì)李廣的改判,對(duì)衛(wèi)霍的辯護(hù),對(duì)昭君的論述,對(duì)《蘭亭》的調(diào)侃,與其說這偏離了成見的舊道,不如講是在一條新的路線(譬如北緯四十度,譬如G6)上重新相見。此外,在書中堪稱新能源的,還有當(dāng)下歷史題材的雄文難得一見的諸多新詞潮語與網(wǎng)絡(luò)式表達(dá),它們未必是在輕率追風(fēng),而拉開了自身與古典判斷之間、與古籍原文之間的距離,構(gòu)成了雙重的在場性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作者通過在北緯四十度上的漫游抵達(dá)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原發(fā)地;又編織以如許當(dāng)下的腔調(diào),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此時(shí)此地,去回顧并言說彼時(shí)此地。
讀者會(huì)在一章章承前啟后中領(lǐng)會(huì)到作者對(duì)文學(xué)態(tài)度的潛臺(tái)詞,這同樣也是一次篤定的重估,而不是出走和反叛。譬如關(guān)于民間故事,作者的言語策略并非一成不變,從開頭站在傳說中被孟姜女哭倒的長城立場上,“訝異于一些國人這種情感立場的錯(cuò)位”(自序P2),到書的結(jié)尾處涉及到楊家將時(shí)由衷的同情之語,作者未必是長途旅行之首施兩端;而是意識(shí)到民間傳說雖然不公平于歷史之真,卻善于當(dāng)下,他起初擔(dān)心“干擾了歷史事實(shí)”,“這會(huì)讓國民沉溺于想象而自欺自慰”,但最后“忽然有了某種理解與不忍”(P457)。不確定的表達(dá)只是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過程中姿勢(shì)的調(diào)整,而作者關(guān)于文學(xué)的用心與定位一直都守著那根線:“我不是在做歷史研究,我的寫作始終屬于文學(xué),對(duì)此我很清醒自知”(自序P5)。這既是對(duì)當(dāng)下自我的認(rèn)知,也是對(duì)當(dāng)下時(shí)代的關(guān)切。我們注意到,在本書編輯出版的時(shí)候,《北緯四十度》中那一段重要伏線的G6高速,已于2021年春夏之際從北京一直通車到青海格爾木,換言之,北(京-)臨河一線的北緯四十度已經(jīng)南下貫通到了世界屋脊。
因而,把《北緯四十度》定位為一部歷時(shí)非虛構(gòu)寫作作品,可能是最合適的。近來,“非虛構(gòu)”的概念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完全歸為話語體系的迭代與話術(shù)的更新,那是文學(xué)內(nèi)外的一種合力,含有對(duì)古典式高亢的文學(xué)抒情的省思,也針對(duì)敘事成本漲跌起伏的推敲,還有文學(xué)手法潤物無聲地在新聞、史學(xué)研究諸領(lǐng)域中蔓延的托辭。因此它并不是擠壓了文學(xué)的傳統(tǒng)領(lǐng)地,而是現(xiàn)實(shí)見證下寫作股權(quán)的重組。看上去,非虛構(gòu)在共時(shí)性即社會(huì)學(xué)場域中拔營奪寨、廣泛收編,聲勢(shì)已成,與虛構(gòu)作品分庭抗禮。而歷時(shí)性場域,卻會(huì)涉及到方法的更新與范式的轉(zhuǎn)移,尤其是材料的不可控與不可交談性,因此相關(guān)的術(shù)語還需千呼萬喚,從人類學(xué)工作規(guī)則到傳統(tǒng)漫游的趣味也有待繼續(xù)借鑒。
我們當(dāng)然樂見“歷時(shí)非虛構(gòu)”興起,與隔壁的公眾史學(xué),以及野史傳統(tǒng)長期澆灌的歷史小說、隨筆領(lǐng)域言語膨化的歷史散文等等構(gòu)成犬牙交互的景觀。但也要保持一份警惕,那大批的新文化史讀物,往往在一本書中宣稱找到一個(gè)重大的切口,在另一本書中又找到了另一個(gè)關(guān)鍵物,實(shí)則卻成為源源不斷的意象生產(chǎn),變形之鏡會(huì)消祛歷史的正典性而帶來滑稽感。另一方面,隱藏著的現(xiàn)實(shí)感會(huì)不會(huì)使得“北緯四十度”面臨新的后設(shè)性尷尬?這是回不到班固和司馬遷那里的現(xiàn)代知識(shí)(漢代只有經(jīng)書與緯書),它在地貌上可能可以像國界線那樣樹下界碑,像回歸線那樣鑿出供人旅游的標(biāo)志,但畢竟看上去是構(gòu)造的座標(biāo),經(jīng)緯線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生長出來的直線,所以會(huì)不會(huì)有“虛構(gòu)”之譏,而影響到“非虛構(gòu)”的品質(zhì)呢?如我們反復(fù)提起的G6高速,在實(shí)際地面工程中,只能保持大致而不是完美的直線,甚至,所有高速道路都為了避免司機(jī)在行車時(shí)前路過于坦蕩產(chǎn)生幻覺,為了減少事故率,而須人為設(shè)計(jì)出種種S形彎道來。北緯四十度會(huì)不會(huì)對(duì)于江山圖而言也是一條向現(xiàn)實(shí)有所妥協(xié)的幻線——就如同在180度子午線那里略有鋸齒的國際日期變更線(又稱換日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呢?
若越俎代庖替《北緯四十度》反詰這些問題,須先請(qǐng)出太史公。司馬遷除了說到“通古今之變”,還有先前一句:“究天人之際”。地上沒有直線,不等于說天上沒有規(guī)則。蘇軾那句“西北望,射天狼”的壯言名句,可一直周而復(fù)始地反復(fù)實(shí)現(xiàn);因?yàn)榘ㄌ炖切窃趦?nèi),繁星流轉(zhuǎn)而有序,四季星空更迭,雖有歲差,但在肉眼的視域中,在三五千年的尺度里,“秦時(shí)明月漢時(shí)關(guān)”可以看作一種有常。而另一種恒定在于,星空變化中,須知有北極星始終在正北所在。更重要的是,它在北半球,使不同緯度意味著不同的角度:所以,北緯四十度也可以說真的是一條非虛構(gòu)的線:人們正北望,以黑色的天地背景下,會(huì)在與地平線成四十度夾角的地方找到那顆不變的恒星。在北緯三十度,北極星位于正北三十度角的高度。不同緯度的見聞是不同角度的見聞,而這個(gè)四十度夾角,相比于更低緯度地區(qū),使永恒之星不易受草木、建筑與山石的遮蔽,更加閃亮;相比于更高緯度地區(qū),人亦無須鼻孔朝天,強(qiáng)直脖項(xiàng)來觀察;總之,北緯四十度,是保持著尊嚴(yán)的仰望與致敬的立場。也正是要同樣保持著這個(gè)角度與姿勢(shì),才便于從此穿過重重幽暗,重新望進(jìn)歷史,去看見從班固到司馬遷的古史記錄與史家精神。而“班馬”,因此也成為并非虛構(gòu)的一條觀看與言說的倒敘線索,與《史》、《漢》中的逝者如斯之流相互動(dòng)。
- 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2022-01-24]
- 陳福民:有我之史乘,無韻之長歌[2021-11-10]
- 對(duì)談|《北緯四十度》:面對(duì)歷史,文學(xué)能做什么?[202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