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翻譯的詩體莎士比亞戲劇有何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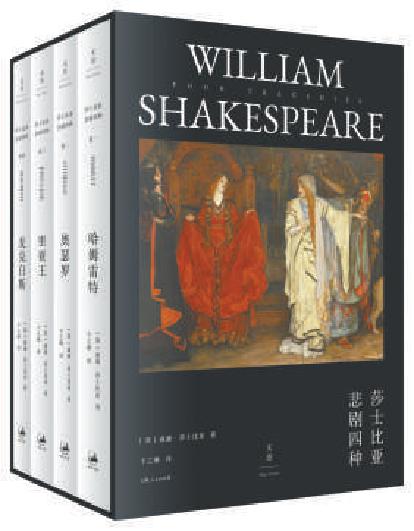
卞之琳先生(1910-2000)是我國著名的詩人、外國文學翻譯家和研究家。在從事著譯活動的六十年里,他在詩歌創作、外國文學譯介和評論等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期出版的新版卞譯《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更是被王佐良先生譽為其翻譯事業的巔峰之作,也有不少前輩將卞譯《哈姆雷特》列為各中譯本之冠。卞先生融歐化古,以一代新詩弄潮兒的匠心加之學者的嚴謹,為廣大文學愛好者奉獻了獨具格調的莎劇譯本以及對文學感受性的多重體驗。
?與莎劇結緣
早在上世紀20年代,還在江蘇海門鄉下念初中的卞先生就與莎士比亞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卞之琳自小就被母親鼓勵多學英文,以期未來能到洋人掌管的郵務、海關等機構獲取豐厚的酬報。當時初中學校所用的英文教本,正是由英國蘭姆姐弟編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高中畢業后卞之琳前往新學盛行的上海,在頗有名氣的浦東中學選修過莎劇課程,讀過原版劇作,還在課余悄悄試筆,翻譯過英國大詩人柯勒律治的名篇《古舟子詠》。
此后,卞先生在北大英文系學習及在川大、西南聯大和南開大學任教期間,他始終無法割舍年少時的那一段初識,在翻譯英國詩歌和《仲夏夜之夢》等原劇本的過程中不斷打磨自己的文學鑒賞力和翻譯功力,為1949年從牛津大學訪研歸國后開啟的莎劇譯介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卞先生原計劃在上世紀50年代末完成四大悲劇的翻譯工作,但直到1988年譯稿才得以付梓出版。好在翻譯似酒,需時間的醞釀和技藝的雕琢,而莎翁四大悲劇之沉郁雋永,更不會辜負譯者在這三十個春秋之間的堅守與耕耘。
?“亦步亦趨”中的別出心裁
卞先生對翻譯的基本主張可追溯至上世紀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歲月。在翻譯課上,他自述首先要破的就是“信達雅”、“神似/形似”和“直譯/意譯”這三種舊說,而毋寧要將他所堅持的翻譯標準總結為一個大寫的“信”字:“從內容到形式(廣義的形式,包括語言、風格等等)全面而充分的忠實。”到上世紀80年代,他又將其提煉為“亦步亦趨”這一四字原則:“我們譯西方詩,要亦步亦趨,但是也可以做一些與原詩同樣有規律的相應伸縮。”可以說,他將這一理念如實而又不失靈活地體現在了莎翁四大悲劇的翻譯中。
翻譯要做到卞先生所謂之大“信”,其障礙之一便是來自母語表現力的誘惑。在20世紀那樣一個新舊更替的時代,新觀念與舊學問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當時就有譯者強調“舍形求神”——洗凈“歐腔美調”,統統吞入譯者“胃”中,化為地道純正的中文,這便有了譯學中的“打破原文結構,發揮中文優勢”一說。對于母語,中文讀者不僅有著認知定勢,還有著審美定勢,譬如對于成語或四字短語的偏好使用便是其中一例。然而卞先生的譯作卻能大膽地突破這一藩籬,在語言文化之定勢與誘導讀者接受新鮮異質的文學感受性之間找到了某種微妙的平衡。
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場中,哈姆雷特王子對母后不顧亡夫尸骨未寒便匆匆改嫁一事有一句評價:“The funeral baked meats/Did coldly furnish forth the marriage tables。”朱生豪先生的散文體譯本是:“葬禮中剩下的殘羹冷炙,正好宴請婚筵上的賓客。”“殘羹冷炙”在此處是很貼切的成語,但原文“baked meats”(烤肉餅)這一具體意象消失了,文學的感官性在這里讓位于中文表意所呈現出的慣性,轉化為朱譯本中空泛的“殘羹冷炙”,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文學具體性以迎合表意通俗性,實際上是一筆由譯者主導、而讀者并不知情的交易——盡管讀者滿足了自己的理解預期,但同時也喪失了對異域/異民族某一具體感性之物的直觀體驗。而卞譯本則將“亦步亦趨”的優勢展現得淋漓盡致:“喪禮上吃不完、涼了的烤肉餅就搬上了結婚的喜筵。”不僅將“烤肉餅”之語保留了下來,且將“furnish forth”譯為“就搬上了”,較之朱譯本中為了附和情景而憑空構想的“宴請賓客”,也更能生動地捕捉到丹麥奸王迎娶寡嫂這件事在王子心中所散發的粗鄙不堪的氣息。
對雙關語的處理亦是不可不提的妙證。英國18世紀的大文豪約翰遜博士嘗言:“雙關語是莎劇中傾國傾城的‘埃及艷后’;為了她,丟了江山也在所不惜。”就此而言,譯者倘若避重就輕,丟掉莎翁孜孜以求的“埃及艷后”,未嘗不是一件憾事。
此處僅舉《哈姆雷特》中最著名的一例:在弒兄娶嫂后,奸王嘗試用言語來招撫哈姆雷特,試探性地將其從“侄子”拉近到“兒子”的位置:“my cousin Hamlet,and my son。”剛經喪父之痛的王子不僅不受其惑,反而巧妙地答道:“I am too much in the sun。”莎士比亞這里讓哈姆雷特借用son/sun的諧音雙關語,暗戳了叔父的偽善。對此句,朱生豪譯作“我已經在太陽里曬得太久了”,梁實秋譯作“我受的陽光太多”,似乎都選擇了避而不譯,后者最多只是在尾注中補充了“sun”的諧音義。而卞譯則別出心裁,譯作“陛下,太陽大,我受不了這個熱勁‘兒’”,將前文的“son”(“我的兒”)和后文的“sun”(“熱勁‘兒’”,指奸王異乎尋常的突獻殷勤),通過兼顧音和義的方式勾連了起來,可謂一筆曲盡其妙。凡此種種,在卞譯四大悲劇中不勝枚舉,盡顯譯者的巧智和用心。
?在不同文體間穿梭
盡管后世盛贊莎翁之詩才有如“第二自然”,但主題上的包羅萬象和對駁雜人性的明察秋毫,并不能遮蔽劇作家創作時所植根的文學傳統。正如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所探討的,西方自古典時代以來的文體分用原則在莎翁筆下得到了十分自覺的調用,而卞先生兼及學者之嚴謹的一面更在于,他有著十分敏銳的文體意識,不僅對莎劇中的不同文體有著精深的研究,還能從漢語的雅與俗之間信手征用恰切的文類及風格,來使譯文在表意和氣韻上做到對原作的“亦步亦趨”。
《哈姆雷特》中的兩處“戲中戲”是絕佳的例子。第二幕第二場中,巡游劇團到訪丹麥宮廷,王子邀請伶人表演他最受觸動的一段古典戲文。這段60多行的臺本故事取自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再現的是特洛伊城陷落后老王普利阿摩斯受難及王后為之哀嚎的場景,氣勢磅礴,悲愴肅穆,是典型的史詩風格。卞先生對這一段的譯文風格如下:
天上是一片寂靜,云也靜止了,
風也不言語,大地是全然沉默,
簡直象死了,忽然間一聲霹靂
震裂了天空;披勒斯一停頓以后,
殺心也就激起他重新動作;
塞克羅披斯錘打戰神的鎧甲
管保它萬世都結實,落手無情
也不及此刻披勒斯掄起血花劍
狠命的直劈了普賴姆!
滾出去,滾出去,命運女神是娼婦!
愿天神全體一致剝奪她權力;
打碎她那個轉輪的輪輻和輪盤,
把那個圓軸心滾滾的直推下天山去,
直落到地獄的底里!
在腳注中,卞先生闡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如此處理的理由:該段臺詞“史詩氣重,戲劇性少”,只有與本劇正文風格形成鮮明對照,才能符合“戲中戲”的要求。
無獨有偶,在第三幕第二場上演的“戲中戲”《捕鼠器》中,莎翁用70多行詩戲仿了丹麥老王與王后之間“感情甚篤”的舊日時光,對當前真實的父死母嫁情景形成了奚落與反諷之勢,且使用了略顯 陳腐的“ 偶韻 體”(rhymed couplet)。卞先生對此處譯文也進行了精妙的處理,正如他所給出的說明——“在戲中戲里為了顯出與本戲截然區別,就故意用陳腔濫調……我在譯文里索性更把它庸俗化一點,中國舊曲化一點”,他在遣詞造句上對其時流行于蘇南浙北一帶、近似于“打油詩”的民間舊曲進行巧妙地吸收和化用,達到了融歐化舊、神形兼備的妙境。試摘一段:
伶王
愛妻須知,我誠恐即將辭世,
我的精力愈來愈不濟事。
你該在花花世界里安享天年,
受人敬愛;倘一朝有緣得見
伶后
哎呀,帶住!
誰這樣戀愛該就是負心的娼婦!
要再嫁丈夫,活該我受盡詛咒!
再嫁的就是謀殺親夫的兇手!
哈 〔旁白〕
苦黃連,苦黃連!
可見,卞先生不僅追求意義傳達上的忠實,還在刻意挖掘并還原戲劇內部不同文類和語體帶給讀者的錯落有致的審美體驗,這不僅是對原作者的忠誠,更是對中文世界廣大莎劇愛好者的一份虔敬。16世紀末期的英國舞臺上,充斥著各類取自古典及基督教中世紀的戲劇程式和套路,劇作家對不同文體風格的選擇有著超越形式本身的意義。可以說,形式是內容的外化,二者血肉相連相互滲透。在很多時候,藝術審美的第一步恰恰是要去把握這些“有意味的形式”,若像某些譯者那樣,為求表意的通達曉暢而犧牲掉大部分形式上的“意味”,只能說是囿于所處時代及一時之需求。而卞譯緊緊依托原作,融通了中西文學傳統中的高低文體,做到了雅俗并置,在不同的文體和詩體之間穿梭自如、獨運匠心,是為譯事中之大“信”也!這也正是梁實秋先生呼吁譯界“應當馨香以求”的一項成就。
?還原莎劇詩體風貌
自出版以來,卞之琳的詩體譯本《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以其全面而獨到的價值,代表了我國莎劇翻譯的重要成就。他用漢語白話律詩摹擬莎劇的素體詩,以頓代步,強調原作詩行的音律美和形式美,被方平先生譽為“可以站出來”與傅雷先生“作分庭抗禮”的代表性人物。
普及莎劇這一篳路藍縷的工作已由先賢完成,以詩譯詩來還原莎劇的理想風貌必然是未來莎譯領域新的突破點。因而,巫寧坤先生的評價一語中的:“正如朱生豪先生的翻譯為今天的莎劇翻譯工作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基礎,卞之琳先生的這個譯本為明天的莎劇翻譯工作者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終其一生,莎劇始終是卞先生臨窗探望的風景,而他的譯本也將裝飾無數后來者的夢。
- 孫琴安:憶徐志摩研究會的幾位顧問[2021-12-09]
- 1964,我們知道的比莎士比亞少?[2021-11-16]
- 莎士比亞和他的愛情詩[2021-10-24]
- 早期現代的修辭話語與性別重構——以莎士比亞《愛的徒勞》為例[2021-10-19]
- 莎士比亞與威尼斯幻夢[2021-10-13]
- 我國現代著名詩人、翻譯家、學者卞之琳藝術館在海門開館[2021-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