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在場、好看、“片面深刻”的文學史 ——訪《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主編唐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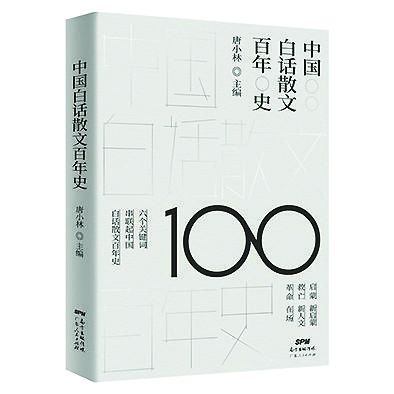
第一部呈現中國白話散文百年狀態的文學史——《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于近日面世。該書以文學與時代的關聯為主線、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為核心、以“介入,然后在場”為價值尺度,采取“片面的深刻”方式,對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百年白話散文進行了客觀理性的遴選、審視與評判,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百年白話散文浩繁豐富復雜,雖不能說因此蓋棺定論,卻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認識參考。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這部書和中國百年白話散文,本報記者專訪了該書主編、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唐小林。
——編者
記者:當我拿到廣東人民出版社剛出版的《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的時候,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已經有了那么多的中國現當代散文史,為什么你要來主編這樣一部散文史,而且還稱為“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有些文學史名稱變了,但內容沒有變。比如有些所謂的“20世紀文學史”,不過是把“現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簡單地拼湊在一起,在史觀和史料甚至寫法上沒有太大變化。
唐小林: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啊!的確,我們已經有了大量的中國現當代散文史,盡管這與同一時期的文學史、小說史、詩歌史比起來還是要遜色得多,但總體上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而且還出了一批像林非、俞元桂、劉錫慶、朱金順、吳周文、范培松、陳劍暉、王兆勝、王堯等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名家。由郭預衡、郭英德任總主編的《中國散文通史》的“現代卷”和“當代卷”,厚厚四冊,規模相當可觀,內容扎實豐富,可以說是現當代散文史集大成者。
但文學史常寫常新,我認為這段時期的散文史還沒有寫夠。我之所以要來主編這本《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是與我對“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這三個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有關,更與我對白話散文誕生以來這百年中國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考相關,這個變局遠未停止,尚在迷局般演化,不得不整體觀之。如果將其拆散和拼裝為現當代散文史,也許更符合現行的學科規范,卻可能看不清白話散文這百年來的真正命運與特殊貢獻。
當然,回到白話散文自發的現場,并不存在一個整齊劃一的一百年。“百年史”作為一個文學史范疇,只能是一個大致的時間段。說它是一個“多元”的也可以。它可以是1915—2015,也可以是1917—2017,還可以是1919—2019。之所以是“多元”不是“多樣”,是因為每一個時間段后面,都隱藏著不同的“元語言”,而不同的元語言,會裝置出不同的文學史風景。我更傾向于把上限上延,越過1915。歷史或許有多個“引爆點”,“引線”卻可能是長長短短的。這樣,我所說的“百年史”,上下牽出的遠不止百年的文學史想象。
記者:你特別強調“百年”或“百年史”這樣的概念,這一百年對于中國“白話散文”真的很重要嗎?可否詳細說說?
唐小林:是的,這一百年對重構中國白話散文史尤為重要。
這一百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在這個轉型途中,發生了一場相當于西方人所說的“軸心革命”,即意義的“大脫嵌”。簡單地講,在古代中國,我們的意義來源于“以自我為中心的家國天下連續體”,那時的人,正如郁達夫所說,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大脫嵌”發生以后,轉換了意義的源頭,也扭轉了歷史的方向,個人掙脫了家國天下連續體構筑的鐵柵,努力奔赴自由,獲得了新的感受、新的經驗、新的認知和新的表達,從而引發了中國散文的“白話轉向”。就像“大脫嵌”的軸心革命拉開了人類現代性的序幕,也撞開了中國走向現代性的艱難之門。
“大脫嵌”在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幾個世紀,在中國卻幾乎濃縮為白話散文的這一百年。可以說,沒有白話文,在中國就不會有“大脫嵌”這件事,更不會有隨后現代性的蓬勃滋長與快速曼衍。也可以說,文言文總體上終結于家國天下連續體的崩塌,而白話文則創開了中國現代性的新紀元。與此深刻關聯的,是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中國開始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所以這一百年又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百年。
這兩件大事,構成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核心內容,也從根本上推動了“白話”取代“文言”成為“國語”,從而徹底改變了散文的整體風貌。
記者:作為“散文史”,你是怎樣處理“散文”這個概念的?“散文”與其他文學體裁比較起來有什么特點?
唐小林:關于“散文”這個概念的確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就認為散文要具有“散文性”,更加強調“文學性”的一面。他們更愿意談論“藝術散文”,而不太關注雜文和通訊、特寫、報告文學這類文體。有不同的看法才是正常的,有不同的看法才能將散文的不同側面多樣化地呈現出來。正如你所知道的,作為現代文體的散文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泊來品,在西方文體四分中,散文與小說、詩歌、戲劇并肩而立。我認為,散文之“散”,并非寫法上的“形散而神不散”,而是作為體裁的散亂無邊,作為范疇的難以歸類。
在我看來,散文是除小說、詩歌、戲劇以外的所有文體,是文學領域的“不管部”:不是小說,不是詩歌,又不是戲劇的文學作品都是散文。可以說,散文是散落在小說詩歌戲劇邊緣的文學體裁的總稱。散文之散亂,看似它的局限,實際是它的優勢:它似無小說詩歌戲劇的一定之規,可以任意而談,無所顧忌,仿佛自由的精靈;它似無小說詩歌戲劇的虛構之苦、敘述之難、隱喻之累、象征之艱,可以直面現實與內心,仿佛自由言說的媒介;它似無小說詩歌戲劇的高貴與高級,乃如白話一般,天然具有煙火氣、草根性。
我記得在三十多年前,文史學家黃修己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寫小說的可以不做詩,做詩的可以不寫戲,但搞文學的幾乎沒有不寫散文的。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凡能識文斷字、舞文弄墨的,都寫散文。散文比其他三類文體,顯然更具自由性、民主性和平等性,因此才在這一百年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發揮著其它文體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在主編這部散文史的時候,盡管我們的敘述有所側重,但依然重視雜文和通訊、特寫和報告文學這類文體,特別指出,它們從兩個相反相成的方向,致力于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政治認同:一個方向主要是通過雜文抨擊舊物,揭露時弊,從歷史和現實掃除現代民族國族政治認同的各種障礙;另一個方向則是通過通訊、特寫、報告文學追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步伐,以奏響時代最強音的方式正面強化這種政治認同。
記者:有一種說法是,文學史就是遴選經典的歷史。的確,書寫文學史有一項重要職能或者說重要任務就是遴選經典。而如何遴選經典,或者說有什么樣的“經典觀”,有什么樣的經典遴選標準,就有什么樣的文學史。你認同這樣的觀點嗎?還有,你主編的這部《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又持怎樣的經典遴選標準?
唐小林:你的這些問題都擊中要害。我當然贊同持什么樣的經典觀就有什么樣的文學史的說法。主編這部《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散文作品時,到底以什么的標準遴選經典,也是我們長時間思考的問題。我們的主要想法是,放在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或者說散文與時代的關聯的框架下遴選白話散文經典,它應該具備幾個基本要素。這里例舉兩點。
首先它是白話語言的經典。也就是說,純熟的白話、好的語言,是經典白話散文的第一要素。胡適說,只有純熟的白話,才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狀態。只有好的語言,才能夠得上文學經典的門檻。
其次它是藝術文本的經典。這是指散文文本內部要存在“審美距離”,使文本建構的“可能世界”內在地具有對“實在世界”的“概括力”。我認為,在“可能世界”與“實在世界”有所關聯的前提下,藝術文本內部存在的審美距離越大,也就是它建構的“可能世界”與“實在世界”之間的距離越大,它的“藝術概括力”也就越大,它的精神深度和思想深度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在這個意義上,藝術文本的審美距離,就是它的藝術概括力,也即是它的意義深度。意義深度越大的藝術文本,就越具有生命力,就越具有超越時空的可能,就越具有經典品質。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要素并無固定的標準,總是相對而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史是經典遴選史的重點是“遴選”,遴選意味著比較,意味著淘汰。即是說,白話語言的經典、藝術文本的經典等要素,只是在這一百年眾多散文作品的比較中作出的判斷,而不是來自某個“文學性”或“散文性”的恒常不變的法則。而且,對于相同或不同的作品來說,這些要素的表現也并不總是均衡的,可能某些作品某一方面或某兩個方面更加突出一些。但由各方面作用的因素卻是缺一不可的。
記者:我注意到《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用六個關鍵詞,即啟蒙、救亡、革命、新啟蒙、新人文和在場六個關鍵,就串連起了這一百年的散文史。前五個關鍵詞好理解,而把“在場”與前面五個關鍵詞并列,有點超出常識,能不能談談這樣做的理由和想法是什么?
唐小林:把“在場”與啟蒙、救亡、革命、新啟蒙、新人文并列,應該是這部文學史的一大特點。這一方面把散文史的書寫緊扣時代,且推進到了當下,使散文史“在場”了。另一方面,在場主義散文運動也是近十年值得重視的文學現象,它的發生看似偶然卻蘊含著某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與當時文學、文化和思想界的狀況有關。
一是時代呼喚文學在場。受新文化運動中郁達夫、周作人小(小品文)、美(美文)觀影響,百年白話散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出現了過度關心個人內心世界,與時代缺席,以至抒情而濫情、寫文而濫文、審智而濫智的現象,中國傳統文學的擔當精神嚴重丟失了。消費主義文化的興起,使各種事物包括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等等都有“為消費”“被消費”的傾向。因此時代呼喚文學在場。
二是文學與時代疏離的情況日益嚴重。虛擬世界的出現,使人們不斷往還于線上、線下,或同時處在線上與線下之間,與實在世界的關系,尤其是與周遭世界的關系日漸疏遠和大幅弱化,這種疏離在散文上同樣明顯。
三是語言的遮蔽導致意義離場。在西方沸沸揚揚大半個世紀的語言學轉向到此一時期才真正落地中國,寫作的語言自指化傾向與消費主義緊密呼應,導致意義的離場,寫作的及物性問題越來越尖銳,符號泡沫、符號異化表現突出。
四是形形色色的復古思潮導致散文的現實性削弱。古典主義或擬古主義思想盛行,國學熱、西方古典熱、漢服熱、古鎮熱等等,把人們的目光從現實帶向以往,思想界文化界文學界出現現實空場的現象。而與之相應的則是散文的復興,“散文熱”和“大散文”時代的到來。但在“散文全面繁榮”的同時,有人則在大聲疾呼“救救散文”,認為這個所謂的“大散文”時代,實際陷入了“虛假、虛假、虛假”的泥淖。陳劍暉以學者特有的敏銳,把這一現象歸結為“現實性”不足。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在場主義散文”運動,大聲疾呼散文對現實、對當下、對精神的介入和對意義的發現。另外,在場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部散文史所持的立場之一,只不過在場的意義在這里更寬泛了:一是“歷史”的在場。這一百年最重要的歷史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史。二是“現實”的在場,必須立足今天思想史的高度和現實處境回望和審視這一百年的白話散文史。三是“敘史者”的在場。我們每個歷史的書寫者,都帶著對歷史的同情性理解,在所敘述的對象中帶入自己的生命體驗、審美經驗和理性判斷,精神性地介入到白話散文百年史之中,尤其是對百年散文經典的解讀之中。
記者:我還有一點感到奇怪,在第二章“救亡與民族的獨立”中所涉及的經典散文,有的似乎與當時的抗戰無關,這又如何理解?
唐小林:我這樣來回答吧。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戰勝利,是發生在現代中國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救亡運動。現代民族國家依賴于兩個認同,即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救亡也因此表現為政治認同上的救亡和文化認同上的救亡。對于白話散文而言,如前所述,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等紀實類報道性作品,更偏向于政治認同上的救亡。而另一類作品看似“與抗戰無關”,或者說與抗戰現實沒有直接關聯,但依然從民族文化的認同上起到了救亡的作用,就像都德的《最后一課》給我們的啟示那樣。
現代民族國家,不僅僅靠政治,更靠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把人心凝聚一起,把統一維系起來,筑起一道精神世界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救亡雖具有間接性,但依然是中華民族救亡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從長遠看,或許是更為深層的一部分,因為它會對未來更加持續地發生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何其芳的《畫夢錄》、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等白話散文,從頑強的民族文化認同的角度,仍然在民族救亡這個巨大的時代主題之中,而且今天越來越散發出獨特的審美光芒。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你在緒論中聲稱,這是一部“片面的深刻”的散文史,“片面的深刻”指的是什么?
唐小林:用六個關鍵詞串連起一部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顯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部“片面”散文史,而且是一部“宏大敘事”的文學史。“宏大敘事”在今天談得不夠,如今學術內部更關注“復雜”“含混”“差異”“地方”等。但在學術上我是一個喜歡“背道而馳”的人,我覺得這個時候正是應該“回到宏大敘事”的時候。我們的“宏大敘事”還沒有做好、做夠,有些連“規范性基礎”都還沒有找到,更談不上對“現實”和“事實”的觀察。
“片面的深刻”是這部散文史編寫的初衷。“片面”是肯定的。“深刻”卻只能是一種追求。這種追求不僅表現在這部散文史的立意、構架上,也表現在對具體作品的解讀上。也許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部白話散文史在經典作品的細讀上下如此大的功夫,且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力求“不虛美,不隱惡”,有體驗、有溫度、有滋有味,語言既有美感,又有質感,可以說這是一部好讀的文學史。
記者:你能否有一句話概括《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的特色。
唐小林:硬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可以說:這是一部在場、好看、片面深刻的文學史。
- “九十年代文學”:需要重視的一個“年代”研究[2022-02-15]
- 中國網絡文學,有資格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2022-01-19]
- 中華詩詞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撰工作會議召開[2022-01-12]
- 科幻研究和重寫文學史[2022-01-11]
- 90歲謝冕先生與當代詩歌[2022-01-06]
- 錢理群:關于“20 世紀中國文學經驗”的思考[2021-12-21]
- 陳曉明:建構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2021-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