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寫作即是活著,活著即是寫作
2002年,不到30歲的李修文在《收獲》雜志連發兩部長篇小說——《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兩部作品還被改編成影視劇。但在這之后,李修文陷入了長達十年的沉寂。他開始了走南闖北的編劇生涯,一路上也遇到了無數人和事。
2017年,李修文以散文集《山河袈裟》回歸文壇,并以此拿下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2019年,又一本散文集《致江東父老》來到人世,他憑借它摘得“2020南方文學盛典”的“年度散文家”。今年3月,李修文的最新散文集《詩來見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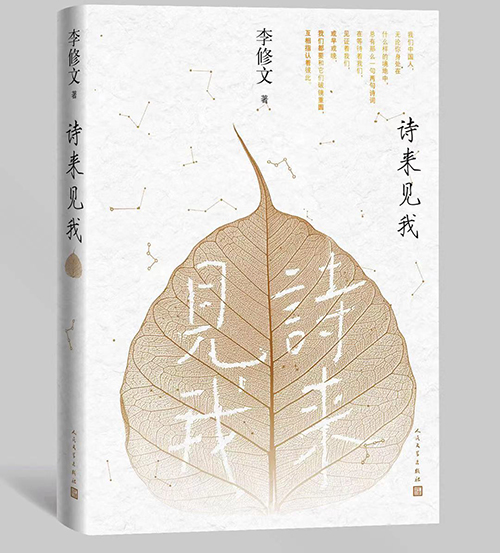
今年3月,《詩來見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詩來見我》共二十篇,每一篇的內容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這些主題往往可以用一個字或一個詞概括,比如酒、花、雪、秋天、驛站、友情、故鄉、母親、自我、貶謫、悼亡、追悔、別離,等等。大部分作品完成于2020年春天,最早以專欄“詩來見我”刊載于《當代》雜志。那陣子,因為武漢疫情,李修文下沉社區,對口支援。他說:“在那樣一個人之為人的根本處境上,許多詩都會不請自到,而且常常安慰我。”
其實在《山河袈裟》和《致江東父老》,甚至于李修文更早的小說中,古詩詞也時常出現。他相信,對中國人而言,詩詞首先不是學問,而是生命本身。無論走到哪里,無論什么時候,總有那么一句詩忽而浮上心頭,見證著我們的喜怒哀樂。比起其他講解詩詞的書,《詩來見我》無關字詞、寫法、主旨,它有關人與詩歌的相遇,是一本面向生命敞開的書。
在連出三本散文集后,今年李修文也重新開始小說創作了。“而今,我倍加珍惜自己還能夠寫作。寫作于我來說,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寫,它關乎生命沖動,而不是為了‘散文’、‘小說’和‘非虛構’的沖動。我是要寫作,而不僅僅是為了哪一種文體去寫作。”近日,李修文就《詩來見我》以及自己的寫作狀態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他說:“目前,我可以確信,我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熱愛過寫作,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覺得寫作即是活著,活著即是寫作。”

5月25日,李修文參加由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當代文學批評工作坊主辦的“‘詩來見我’與中國故事的講法”研討會。 受訪者供圖
在人之為人的根本處境上,詩不請自到
澎湃新聞:“想寫一本關于中國古典詩詞的書”,這個念頭攢了多久?現在《詩來見我》出來了,它是你之前想象中的樣子嗎?
李修文:有這個念頭太久了,但是一直并不明確,而且自打有這個念頭我就知道,我其實做不了古詩詞的鑒賞家和學問家,所以也常常望而生畏,但念頭卻一直沒有斷,讀了很多詩,也讀了很多詩論,王夫之沈德潛王國維陳寅恪,都讀了,大概在兩年前,我就開始寫了一些零碎篇章,有研究小說里的“有詩為證”的,有研究禪詩僧詩的,寫完了也沒拿出去發表,下意識里,我覺得寫出來的這些并不能印證我的舉意和動念——我想寫它們,是因為我從來就沒逃出過那些詞句的指認,機場和高鐵站趕路的時候想起過它們,荒郊野外里想起過它們,怎么一寫下來就沒了荒郊野外和機場高鐵站的影子?
還是因為武漢疫情,我得出門去下沉社區,得去對口支援,在那樣一個人之為人的根本處境上,許多詩都會不請自到,而且常常安慰我:我們今天經歷的一切都不新鮮,杜甫經歷過,羅隱經歷過,李商隱、蘇東坡、唐伯虎全都經歷過,而我,甚至我們每一個人,終須像他們一樣度過這些困厄的時刻。
很奇怪,那些安慰我的詩,常常不是詩歌史上公認的名篇,反倒是些緊貼著日常生活的短詩小令,像飯,餓了就吃,也像藥,不舒服了就吞一顆,尤其是杜甫的詩,它們在四面八方等著我回憶起來背誦起來,對,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想我大概知道自己怎么寫這本書了,無非是,以身作器,再讓詩來見我——我甚至都說不清它們好在哪里,但是它們都是好的,那么,我就不管不顧地去靠近這些好吧。
澎湃新聞:身處武漢,你從去年開始經常被問到有關“疫情書寫”的問題。《詩來見我》寫于去年疫情期間,但其實它的開端是在疫情到來之前?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關注處于困頓中的人,在《詩來見我》中,有關疫情的書寫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全書共二十篇,每一篇的內容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這些主題往往可以用一個字或一個詞概括,比如酒、花、雪、秋天、驛站、友情、故鄉、母親、自我、貶謫、悼亡、追悔、別離,等等。它們時而串起了你在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時而滑向更久遠的記憶。為什么選擇以這些字或詞作為書寫的主題?有用它們來抵御災難帶來的痛苦并重建信心的動因嗎?
李修文:你所說的這些字詞,大部分來自于我在疫情期間的真實體驗——寫酒,是因為實在想和朋友們一起喝酒;寫花,是因為封閉在家的時候,我看見樓下草地上開了一片小花,因為消毒頻繁,它們很快就死了;寫秋天,是因為我跟葉舟通電話,兩個人一起說起了敦煌,二十幾歲時,我和他曾經一起驅車,穿過河西走廊拜謁過敦煌和它的秋天;寫母親,是因為疫情期間我在武漢,而父母兩個人在荊門相依為命,人子之心,萬古皆同,唯有寫下,方可勉強消愁;寫著寫著,更多的詞匯出現了,我想,那不過是我清晰地看見了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別人,只要你在這世上流連奔走,你就逃不過那些詞——驛站,不過是我們討生活時住過的一座座小旅館;悼亡,中年已至,我們終于得以看清楚,人生不過是一次漫長的告別,我們先是和別人告別,最后,這世界與我們告別;貶謫,只要你經歷過被炒魷魚四處找活路,只要你拎著幾件行李從這個地方奔忙到過那個地方,你也總歸會心有戚戚,對吧?
說到底,之所以要寫這些詞,是因為身在災情中,它們就像那些基本生活用具出現在了我的眼前周邊,又變成一種提示:此刻的這條道路,你非得踏上去不可。由此,我甚至看輕了災難,至少能夠與之平起平坐——你也無非就是我必須要踏上去的一條路而已。
澎湃新聞:在形式上,《詩來見我》中不少文章比較特別,比如《墓中回憶錄》以擬唐伯虎的口吻向后人“李修文”講述自己詩文的形式展開,《自與我周旋》依托的是“我”給某兄的書信,《追悔傳略》和《陶淵明六則》則采用了第三人稱。聯想之前的《山河袈裟》和《致江東父老》,你也有散文形式上的探索。為什么想做這樣的嘗試?你希望實現什么?
李修文:這個問題,其實關乎最多的還是寫作者的聲音和調門,事實上,我對“風格”這個詞一直都很警惕,以我過往的寫作經驗看來,“風格”即囚籠,“風格”初顯之時,可能恰恰就是寫作者變為囚徒的開始,而對抗“風格”的武器之一,恐怕就是盡可能使每一個文本都有著自己的獨特聲音和調門,你看,蒲松齡寫了那么多狐妖,幾乎沒有一個是相同的,無非是,有多么復雜的人,就有多么復雜的妖。一座廟,千萬人來拜,它都當得起,是因為它容得下好人也容得下壞人,可是,好人有好人的聲音,壞人有壞人的調門,所以,如果說我有什么希望,我就希望“風格”到來得越晚越好,讓不同的聲音和調門在文本里出現得越多越好,因此,至少目前,我希望我的寫作是含混的和互相沖撞的,是興沖沖而又不確定的。
這是一本通向“原諒”的書,接受自己的書
澎湃新聞:書中有四位詩人分別獨占一篇“特寫”,他們是杜甫、羅隱、韋應物和唐伯虎。為什么給了他們特別的篇幅和筆墨?
李修文:我們的肉身在這世上要經歷什么,杜甫就是什么,幾乎在一切奔走、眼淚和渴望的深處,我們都能看見杜甫的身影,他就是一座普通人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上站著我們自己,我們的父兄,我們的姊妹和兒女,我們得到了又喪失了的,還有我們注定得不到的,都在這座碑上,它們全都是偉大杜甫的示現與化身,也因此,我甚至覺得,杜甫才是從我們自己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神。
武漢封城之后,我一直沒什么吃的,剛能出門的時候,就去找朋友想辦法,朋友找了一張漁網,我們兩個一起下湖打魚,天氣太冷,水溫太低,一條魚都沒打著,所以我離開的時候,朋友要兒子從陽臺上給我扔下了兩捆青菜帶走,回去的路上,確實是百感交集,不斷想起杜甫的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當晚,我就寫了《枕杜記》,事實上,我對杜甫又有一種畏懼,我怕我根本說不清楚他的好,所以,我希望通過我的遭際,告訴可能的讀者們: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把他的詩,還有他這個人帶給我們的撫慰,將它們當作枕頭一樣枕在自己的頭下。
一生中,我們有太多的時刻需要與自己的生活、與世界和解,那些偉大的詩人們也同樣如此,所以,韋應物于我而言,就顯得特別重要。在我看來,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求得和自己、和世界的和解,既不形骸兩忘,也沒躺在地上耍賴,盡管他不是李白、杜甫、蘇東坡這個級別的詩人,但他格外認真,認真地做一個鰥夫,認真地寫詩和養育孩子,并且在其中修成正果,這正果也不是什么靈丹妙藥,不過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本分中完成自我精進,時間到了,塵歸塵,土歸土,那他就歸塵歸土,仍然活在自己的本分中,這就是一個人可能完成的正信。詩人里,有情之人多,多愁多恨之人也多,唯獨拿一輩子去實踐、去兌現的言而有信者少。老實說,早年寫詩,他其實天資一般,但越寫越好,我想,這個好,其實是他從與世界的真正搏斗、周旋和共處中拽出來的。只是,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韋應物,迎來某種和解并不是我們該得的,相反,它其實是僥幸。
你看羅隱就是如此,前半生寫詩就像討價還價和指桑罵槐,而后,他寫出了許多好詩,“隔林啼鳥似相應,當路好花疑有情”,“云外鴛鴦非故舊,眼前膠漆似煙嵐”,這樣的句子,真好,對不對?真是和解之人寫出的和解之詩。可惜的是,于羅隱而言,這種和解很快就半途而廢了,再往后,越寫,他就越是尋章摘句和有氣無力。但是,這不僅不叫人可惜和嗤笑,反倒叫人心疼:這種反反復復和半途而廢,豈不無數次地重蹈在我們自己身上?
喜歡唐伯虎,是因為他例外,與上面說到的詩人相比,單從詩境詩藝上說,他寫的簡直就是大白話,可我偏偏很喜歡這些大白話,因為它們與遭際不悖,與心志不悖——為什么總要從正經和譜系中去認識詩歌呢?為什么不能有一個人從日子和不正經里站出來讓我們靠近詩歌呢?要知道,和眾多軼事里的唐伯虎不同的是,真實的唐伯虎從來就沒逃脫過厄運乃至死亡的威嚇:二十四歲這一年,父母死,妻死,兒子死,妹妹死。在這個背景下再去看唐伯虎,其乖張瘋癲,其白話入詩,豈非正是用冒犯抵抗死亡,用一種瘋狂逃避著更大的瘋狂?
澎湃新聞:你剛才的講述里,有幾次說到了“和解”。我還發現,“原諒”一詞在《詩來見我》中經常出現,有時是原諒他人,有時是原諒際遇,有時是原諒自己。你寫羅隱“在科舉幻夢與杭州刺史這兩座囚籠之間,竟然迎來了一生中少見的清醒和原諒,既原諒了自己,也原諒了旁人和一整座塵世”;你寫韋應物“一座風塵世界被搬進了黑夜和身心,再寫下的,唯有理解和原諒之詩”;你寫世間多少人“先在詩里看見了自己,繼而也替自己找到了寬諒和解脫:人生一世,豈是成敗二字便可以輕巧道盡?”。
所以在我看來,《詩來見我》也可謂一本“原諒之書”。在這本書里,你看見自己,找到自己,再與自己和解。
李修文:你說得非常對,寫這本書,就是為了接受和和解:與自己的,與他人的,與世間各種糾纏的。所謂“詩來見我”,顯然有在詩歌里讓自己示現之意,這個自己,哪怕在寫這本書時,也是困頓、狼藉和拼命自圓其說的——疫情中,一心希望還能做得更多,但是個人的力量又過于微薄,就算去了社區,諸多愛莫能助乃至心如刀絞之感仍比比皆是,我如何說服自己立足于能做之事,又如何接受自己遠遠未能做到更好的事實呢?這種情緒其實是我寫這本書的背景,我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中開始寫作這本書的。
毫不夸張地說,在他人受苦之時,我也為我自己還在寫作這樣一本書而感到不安,對于身處在災情中的人,多一本書,多一個寫作的人,對他們來說有什么意義?然而另外一邊,我終究選擇了原諒自己,所謂“文章千古事”,反而越是在那時候越真切地顯露了其筋骨和要義:說到底,我們經歷的災難,李白、杜甫、白居易、韋應物全都經歷過,我們今日之經歷,不過是災難變幻了面目重新來到了我們身邊,而我們究竟該如何在災難中與他人、與世界相處,又該如何自處?也許,那些偉大詩人們走過的道路,那些偉大詩篇所誕生的關口和契機,恰恰提示給了我們哪怕遠隔千年的可能,如果將這些可能性與今日處境相連接,那么,我也就說服和原諒了自己。
所以,我傾向于認為,《詩來見我》是一本通向“原諒”的書,這條路上,不僅走著我們,也走著元稹、李商隱、羅隱、蘇東坡,這既是一條道路,更是一場戰役,我們當然要期待與萬事萬物最后的原諒與相親,但是,首先,我們還需各自為戰,各自去經受“生也生它不得、死也死它不得”的個人命運。
澎湃新聞:盡管《詩來見我》以詩為題,但它在某種意義上也延續了《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的某種“內核”:你在不斷的行走中遇見了無數的人,也一次次看見了自己。
不少文字寫到了你這些年對自己創作的評價,比如,“我年復一年地寫寫畫畫,最終,灰心作祟,我還是將它們全都付之一炬,再忍看著自己一日比一日變得更加形跡可疑。”“那幾年,我浪跡于涇河渭河,鬼混在河南河北,終究未能寫出一個字,一個過去的青年作家,已然變成了一樁笑話。”
這些年的行走在你的寫作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在你的文字里,常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身處困頓破敗中的人,在雷霆暴雨中忽然有如神啟一般心靈進入高貴光明,這樣的感受和你這些年的行走以及“行走”中的遭遇有關嗎?你在行走中如何給自己的心靈尋找“落腳之地”?
李修文:幸虧那些行走,我的骨頭才越變越硬,而不是越來越軟,因為它們不是我在體驗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它們也不是審美,而是貨真價實的謀生本身,所以,它們會讓你忘掉自己曾經是一個作家,你必須跟那些修傘的補鍋的一樣,睜大眼睛找出生計,找出安身立命之所;其次,它們又經常從迥異于往常的體驗中提醒你,你仍舊是一個作家,甚至,你還有可能寫得更好:那么多你從沒見過的人,現在你就跟他們睡在同一個旅館里,趴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只要這種生涯繼續,也許,你的寫作就能繼續。
但其實,行走也好,不走也罷,一個人終生的功課,可能還是如何獨處——畫地為牢,抑或踏遍河山,不過都是為了說服自己、接受自己和安頓自己。從前,我聽說過芙蓉花的顏色一日三變,也從未在意或細究,有一年,我在四川的一個小鎮子上,有個瘋癲的老太太非得拽著我去看她種的芙蓉花,我沒看見“三變”,但是花色急速變化的時刻還是被我親眼看見了,我當然非常震驚,繼而,看著花,看著老太太,我覺得特別滿足,我確信,我就置身在我即將寫下的作品中,哪怕我當時還在嚴重地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繼續成為一個作家。
對了,還有一回,在甘肅的戈壁灘上,幾個萍水相逢的修路工請我去看樹,我們走了很遠的路,最后才在一條很深的、被風吹不到的壕溝里看到了他們種下的幾棵小樹——就像步行去看電影一樣,這些修路工隔三岔五就要去那條深溝里看自己給自己種的樹,當我跟他們一起置身在那幾棵小樹邊,說實話,我多少有些淚目,甚至覺得慚愧:我怎么就沒能夠在種種匱乏之處給自己種上幾棵樹呢?
這些體驗,看起來是所謂的“落腳之地”,但又不全然是,一個人哪怕擁有無限廣闊的生活,如果他未能獨斷,未能成為一個問題的處理者,寫作對他來說只怕還是問題。是的,再多的行走,再多的“落腳之地”,不過是使自己從體驗里出發,并且去面對體驗的豐富和疑難,它們只是開始,而遠非結束。
寫作不為了哪一種文體,它關乎生命沖動
澎湃新聞:2002年,你不到30歲,在《收獲》連發兩部長篇小說——《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它們被歸為“愛與死”三部曲中的前兩部,開頭部分都是古詩詞,一部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一部是“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行文中亦有許多古典的痕跡。但是后來你放棄了第三部的創作,并說:“我覺得不好寫,很困難,很惶惑,我無法歸納我今天置身的這個時代圖景。這就回到一個問題,即我們到底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現實當中。”
而在十年沒有文學作品發表后,你以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和《詩來見我》歸來,狀態越來越好。且不說《詩來見我》,就是《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亦有許多古典的影子。我可否將此理解為,當時的你感覺到用古典來應對現實的方式出了問題,多年以后,你重新在古典中找到了面對世界和自己內心的方式?
李修文:自我開始寫作,對古典資源的處理就是一個問題,它們一直在深重地影響和折磨著我。一方面,我的語感和修辭、我認識世界的方式均是受到古典傳統的塑造而得以進行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今日生活細碎、復雜而浩蕩,古典倫理逐漸分崩離析,個人處境的疑難越來越具體和莫可名狀,所以,在此情形下,說書人的傳統,傳奇話本的傳統、唐詩宋詞的傳統,便越來越失效,如果我非要將這些疑難視而不見,非要將今日生活放置在這樣一個傳統的慣性之下展開敘事,那么,我要寫的和我看見的顯然就是兩張皮,而我自己又極其依賴生活本身對我造成的沖擊,換言之,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成為那種生活與寫作互相袒露又互相激發的作家,時間長了,我就不信我寫的了,這種不信一度對我形成了閹割,幾乎無法寫作——我還以為我已經失去了一個作家對時代、對周邊生活的基本感受力。
最終,還是要自己來救自己,也就是你之前所說到的那些“行走”,年復一年之后,我突然覺得,我們并沒有活成別的什么人,李白、杜甫走過的路,我們還在走,劉禹錫的朗笑,柳宗元的哽咽,照舊在我們耳邊不斷回響,古典也好,傳統也罷,它們不在我們的身后,也不在我們的對立面,它們才是穩定而飽含秩序的,因為我們的加入,它們才得以向前延伸,到了這時候,再去看那些古典傳統,它們其實也就變成了我們的生活本身。老實說,認識到這個地步,我的內心里甚至是酸楚和欣慰的。實際上,《武家坡》沒有走遠,《游園驚夢》也沒有消失,《紅樓夢》式的故事更是在日日上演,我突然有了一種很大的放心:那個樂府詩的中國,那個幾乎所有的故事里都包藏著一聲嘆息的中國,仍然活在我們身上,甚至,別有一些人,是要注定成為它的承載者的,就好像歷史上的諸多王朝鼎革之際,前朝舊事仍然頑固地存留在那些注定之人身上,當然,這種存留與承載,首先需要的還是個人的精進。
澎湃新聞:你把《三過榆林》視為你創作歷程中一篇非常重要的作品,正是這部作品啟發了你對散文“虛構與真實”的認知。散文在今天的文學評價機制里往往被歸于“非虛構”一類,近年的“非虛構熱”引發了許多爭議,比如,“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是否已難以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因而轉向非虛構尋求幫助?”“什么是文學的真實?”“什么是文學寫作的意義?”……你怎么看待這些問題?
李修文:是的,《三過榆林》對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我也愿意不斷說起我受到的啟發來自何處——我所遇見的這個盲人,為了這輩子能夠好過一點,他在他的頭腦里給自己虛擬了一座世界,所以,他既與我們同在一世,又活在他所虛擬的世界上,那么,對他而言,究竟哪一座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只知道,這兩座世界都讓它容身,那么,我們是要站在“事實”立場上去指出虛擬世界的不存在,還是反倒像他一樣指鹿為馬,先置身于虛擬世界之中再展開敘述?
另外,如你所知,我有許多年其實都沒有能夠持續地寫作,所以,而今,我倍加珍惜自己還能夠寫作。寫作于我來說,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寫,它關乎生命沖動,而不是為了“散文”、“小說”和“非虛構”的沖動。我是要寫作,而不僅僅是為了哪一種文體去寫作。那么,這個問題,我就用陳寅恪先生的一段話來回答你吧:“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
澎湃新聞:可否也談談這些年的編劇經歷?文學圈對“作家寫劇本”一直是有看法的,通常認為這兩個領域天然“有壁”。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作家如何處理自己的內心和大眾之間的關系?
李修文:我的編劇經歷實際上是很失敗的,寫了不少劇本,能拍出來的其實屈指可數,有我自身的能力問題,也有一些項目本身存在的問題,你知道,影視工作實際上是一個眾多人眾多資源協作的產物,投資、陣容、過審,上映,這些都不是一個編劇能說了算的,在中國,除了極少數編劇之外,大部分編劇仍然處于鏈條的末端,沒有什么發言權,一個片子拍好了拍壞了,實際上編劇自己都可能是不知情的。細想起來,我也并不覺得做編劇對我的寫作形成了多大的啟發,相反,我一直非常篤定地覺得,文學,或者說出自文學的見識,對劇本寫作有百利而無一害。只是,實現起來太困難了。對于我的編劇經歷來說,文學背景反倒使我痛苦——你總是忍不住要使一個故事增添意義,但許多故事又根本不需要這些意義,所以,我在編劇經歷里的許多落荒而逃,實際上是那些我看過的書帶來的。當然也會有少見的幸運,比如你也許會碰見幾個對文學有見識乃至有執念的導演制片人,他們也深信文學的力量對于寫好一個劇本是有用的、且敢于突破各種限制去執行的,但依我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可能其實少之又少。
我個人其實沒有太多面臨“個人內心與大眾”之間的關系,我的內心就是我的寫作,但是,當我去從事影視工作,我非常明確我的工作就是諸多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是在共同完成一個同向大眾的文化產品。至于前者,我其實根本不在乎我的內心是否能夠被大眾所接受——你接受我也要寫,你不接受我照樣還是要寫,對不對?現在,我已經很少從事編劇工作,轉而從事一些監制和策劃工作,在這些工作中,我仍然沒有放棄在劇本里傾注文學之力的訴求,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都應當且也承擔得起給影視輸送必要的養分。
澎湃新聞:你也重新開始小說寫作了,會怎么看待這一次的開始?你認為一個作家的最大的體面是什么?
李修文:如我之前所說,寫作,首先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寫,其次,是傾注全力,在虛空里投以實在,這實在,于我而言,最要緊的就是不要使生活和寫作發生分裂,即是說,也許,只要我有捍衛真切生活的能力,我就將持續擁有寫作的能力。目前,我可以確信,我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熱愛過寫作,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覺得寫作即是活著,活著即是寫作,我甚至覺得,只要我還在寫作,那些死去的故人,那些我耳聞目睹過卻又不為人知的事物,就還能挪動腳踝,發出聲響,所以,不管小說、散文、劇本,還是當策劃做監制,我顯然都還會繼續下去,因為對我來說,它們就是我的生活,我得把我的生活度過去。
至于一個作家的體面,許多人都有無數的答案,有的人是為了寫出傳世之作,有的人僅僅安頓自身已是最大體面,而我心中的體面,不過是繼續像一枚釘子牢牢釘死在寫作這條路上。是的,這么多年,來來去去,去而復返,我不過是希望自己還能寫作,只要還在寫,體面就已經有了,此中情境,就像《韃靼荒漠》里的那個主人公,這個等待了一輩子敵人的人,在他死后,真正的敵人才肯現身,面對他的尸體,他的戰友們說:“他從來就沒有去往真正的戰場,但是,他和我們一樣,都死在戰場上。”
- 李修文:作家應成為寫作的主人[2021-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