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巴黎的日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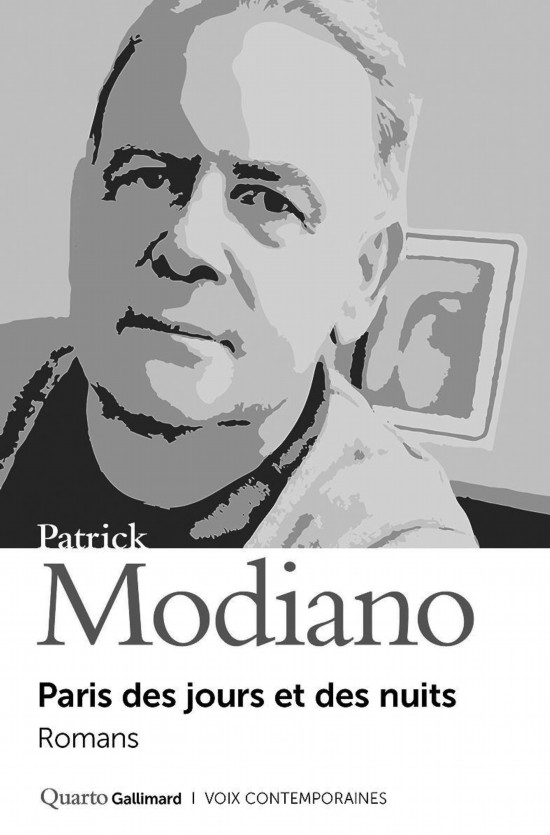
攝影師布拉塞和莫迪亞諾并非同時代人,但是布拉塞鏡頭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巴黎,讓莫迪亞諾重新發現了一個逝去的時代,一個他正在尋找的時代,也是他希望讓讀者認識的時代。
法國作家、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曾說過:“我生活過的巴黎以及我在作品中描述的巴黎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寫作,只是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巴黎。這不是懷舊,我對過去不曾感到遺憾。我只是想把巴黎變成我心中的城市,我夢中的永恒之城。在這里,不同的年代相互重疊,恰如尼采所說的‘永恒輪回’。”對莫迪亞諾來說,巴黎的幾個地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首先是6區的孔蒂碼頭15號(15 quai de Conti)。莫迪亞諾在《戶口簿》(1977)中寫道:“1942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一個和今天一樣溫和的黃昏,一輛三輪車停在了孔蒂碼頭的岸邊,這里將貨幣博物館和法蘭西學院分隔開來。一位年輕的女士從車上下來。她是我的母親。她剛從比利時乘火車抵達巴黎。”當時,莫迪亞諾的母親路易莎·科爾貝剛到巴黎,落腳在孔蒂碼頭15號,幾個月后,她遇到了阿爾貝·莫迪亞諾,生下了莫迪亞諾。兩年后,弟弟魯迪·莫迪亞諾出生。1949年至1953年,兄弟倆被父母送到法國南部城市比亞里茨,再是巴黎近郊茹伊昂若薩斯。1953年兄弟倆重新回到孔蒂碼頭15號。隨著年紀增長,他們開始拓展外出探索的范圍,他們過橋,從左岸來到右岸,在盧浮宮前的卡魯塞爾廣場玩游戲。然而,1957年冬天,一切變了樣。1月27日星期天,莫迪亞諾從寄宿學校回到家后獲知了弟弟去世的消息,而上一周兄弟倆還在孔蒂碼頭的臥室里一起整理郵票冊。從這一天起,他在巴黎變得形只影單。
莫迪亞諾和孔蒂碼頭15號的關聯遠未結束。2002年出版的弗朗索瓦·維爾內《非典型短篇小說》的序言由莫迪亞諾撰寫,標題就叫作《孔蒂河岸15號》。維爾內是一名抵抗運動成員,1945年3月死于達豪集中營,年僅27歲,直到60年后,這部作品方才問世。生前他曾暫住在孔蒂碼頭15號,莫迪亞諾在《馬戲團經過》(1992)中寫道:“早在我父親住在公寓之前,這些書就已經存放在那里。之前的房客,也就是《圍獵》的作者,把它們忘記了。其中有幾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個神秘的弗朗索瓦·韋爾內的名字。”當莫迪亞諾住在孔蒂碼頭15號的時候,弗朗索瓦·韋爾內如同一個看不見卻揮之不去的幽靈伴其左右,以至于莫迪亞諾在序言中寫道:“我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才找到這個人的蹤跡和他的真實身份……”
16區的洛里斯通街93號(93 rue Lauriston)曾是二戰期間法國蓋世太保的所在地,為首的有亨利·拉豐和皮埃爾·邦尼等人,他們從事著鮮為人知的神秘勾當。《夜巡》(1969)里有:“一輛淺藍色的塔爾博特從洛里斯通街開了過來”,《緩刑》(1988)里寫道:“安德烈經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幫人來往。”之所以“洛里斯通街的那幫人”始終縈繞在作家的心頭,那是因為他的父親在德占期間和那幫人有著微妙的聯系,為了在戰爭中生存,他的父親混跡于黑市之中,干著投機倒把的事情。莫迪亞諾和父親的關系一直很緊張,1966年徹底決裂,之后再無聯系。1977年,莫迪亞諾的父親在瑞士去世,很久以后他才得知這一消息,于是關于父親的諸多謎團變成了無解之謎。
18區的庫斯圖街(rue Coustou)在榮獲龔古爾文學獎的《暗店街》(1978)里就已經出現了,它連接著克利希林蔭大道和萊皮克街,附近是布朗什廣場。十年后,在《緩刑》里,莫迪亞諾又寫道:“在后來的年月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見到了讓·D,我那時二十歲。我住在布朗什廣場附近庫斯圖街的一間房間里。我在嘗試寫第一本書。”《小珍寶》(2001)中的地址由于多了門牌號而變得更加具體:“第一天晚上,我猜想我母親可能就住在我現在這個房間。就在我打算租房的那天晚上,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地址——庫斯圖街11號。”在《這樣你就不會迷路》里,主人公在庫斯圖街11號寫了20多頁《布朗什廣場》,與此前的《緩刑》形成了呼應。
14區的奧德街28號(28 rue de l’Aude)也多次出現在他的作品里。在《夜的草》(2012)中,“我”曾生活在這條小巷,“我在奧德街28號收到阿加穆里寄來的一封信時很吃驚,我在那里租了一個房間,但他怎么會知道我的地址?從丹妮那里要到的嗎?我帶她去過幾次奧德街,但好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我的記憶都扭結到了一塊。”又或者,在《地平線》(2010)中,“博斯曼斯一時無法作假,就說出自己真實的出生日期,并說他住在奧德街28號。”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的名字都是“讓”,而“讓”正是作家最開始的名字。莫迪亞諾還經常在書里提到63路公交,這條線路今天依然存在,往返于東邊的里昂火車站和西邊的米埃特門,途徑巴黎植物園、拉丁區、圣日耳曼德佩街區、亞歷山大三世橋、特羅卡德羅、布洛涅森林。莫迪亞諾回憶說,每到周日,父親會帶著他們兄弟倆來森林散步,一直走到湖邊,直到傍晚6點,他們再搭乘公交返回。
莫迪亞諾認為自己“是唯一一個將當時的巴黎與今天的巴黎聯系起來的人,唯一一個記得所有這些細節的人”。如果說莫迪亞諾筆下的人物大多是虛構的,那么代表作《多拉·布呂代》中這位和標題同名的小女孩則確有其人。
1988年,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1941年新年前夕的《巴黎晚報》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尋失蹤少女多拉·布呂代,十五歲,一米五五,鵝蛋臉,灰栗色眼睛,身著紅色外套,酒紅色套頭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運動鞋。有任何消息請聯系布呂代先生和夫人,奧爾納諾大街41號,巴黎。”登報尋找多拉的是她的父母。這個猶太少女在那個冬天離開天主教寄宿學校后,就再也沒有回來。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莫迪亞諾鍥而不舍地搜尋著關于多拉的資料,展開了一系列調查。作家像偵探一樣,回到奧爾納諾大街41號,詢問了多拉的鄰居,查閱了很多官方文件資料。他還在塞爾日·克拉斯菲爾德的《關押在集中營的法國猶太人回憶錄》(1978)里找到了“多拉·布呂代”這個名字。克拉斯菲爾德還向莫迪亞諾提供了其他珍貴的資料,包括幾張多拉及其親人的照片。
莫迪亞諾竭盡全力將多拉從虛無的遺忘海中打撈出來,試圖還原多拉的真實面貌及其心路歷程。當然,《多拉·布呂代》絕非單純意義上對多拉這一人物的傳記寫作,而是雜糅了紀實與虛構的文學形式,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作家對多拉的生活圖景進行了大量的想象,甚至試圖在文學空間內讓多拉和自己的父親建立某種聯系。2015年,也就是莫迪亞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次年,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決定在18區設立一條名叫“多拉·布呂代”的長廊,莫迪亞諾自然受邀出席落成典禮。他在致辭中說道:“這是第一次將一位無名少女永遠銘刻在巴黎的地理中。多拉·布呂代已經成為一個象征。在這座城市的記憶中,她代表著成千上萬名離開法國后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慘遭殺害的兒童和青少年。”
2024年9月,法國伽利瑪出版社推出莫迪亞諾的合集《日與夜的巴黎》,收錄了作家于1982年至2019年間出版的九部精選作品和一篇文章《夜晚的布拉塞》。布拉塞,本名久洛·豪拉斯,生于1899年,是一位知名的攝影師,他和莫迪亞諾曾于1990年合作出版了《巴黎的溫柔》,這部作品集結了布拉塞20世紀30至40年代在巴黎拍攝的照片,并附有莫迪亞諾撰寫的文字。2022年,莫迪亞諾對文字進行了修改和壓縮,作為《布拉塞:100張新聞自由照片》序言。莫迪亞諾回憶說,他曾經在朋友羅杰·格勒尼耶的家里見過布拉塞,在他看來,“布拉塞的設備很簡單,他屬于不會被技術所淹沒的真正的藝術家。只需要靈機一動就能創造出神奇的效果。布拉塞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巴黎的夜色之中。”布拉塞和莫迪亞諾并非同時代人,但是布拉塞鏡頭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巴黎,讓莫迪亞諾重新發現了一個逝去的時代,一個他正在尋找的時代,也是他希望讓讀者認識的時代。
攝影寫作風格是莫迪亞諾作品中不容忽視的特征之一。在《多拉·布呂代》中,照片作為一種物證,起到了推動情節的作用。莫迪亞諾不惜用了兩部分篇幅描寫得到的照片,從而形成一種“散文式圖片”寫作手法。第一部分描繪了戰前拍攝的八張照片,作家選用一般現在時客觀地介紹了多拉及其父母的服飾、姿態及周圍裝飾,而且每張照片的文字描述之間沒有連接詞或過渡詞。這段時期于多拉而言,是一段難能可貴、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第二部分重點聚焦一張多拉以及她的母親和外婆的三人合照。作家著重刻畫了她們的面部表情,其中多拉“昂著頭,目光冷峻,但唇邊有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這讓她臉上有了一抹溫柔的悲傷和桀驁”。作家猜測照片應拍攝于1941年或者1942年初春,彼時危機四伏,人心惶惶。作家使用“三個女人”的稱呼,暗示了多拉已不再是個小孩,童年的幸福生活不再,“三個女人”也代表了三代人,甚至是千千萬萬那個時期的猶太人。莫迪亞諾筆下的照片被賦予了深刻的意義,通過照片,作家真正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多拉一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狗樣的春天》(1993)的兩位主角分別是年輕作家“我”和攝影師冉森。冉森擁有一間房間,充作攝影室或者辦公室,而“我”幫他整理照片目錄,眷寫副本。在冉森決定離開巴黎之前的一個下午,他帶“我”走在巴黎的街道上,給我指了他曾經住過的旅館和工作過的地方。坐在長凳上時,“我”問冉森在拍什么,他答道:“我的鞋。”在咖啡館,他突然讓“我”別動,快門落在“我”手中的牛奶杯。冉森離開時,帶走了三個行李箱,只留下來了一卷膠卷,都是那天下午他所拍的照片。在冉森眼中,“攝影師什么也不是,應該融入背景之中,隱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說,截取自然光線。”所謂“截取自然光線”,其具體做法是使用從美國引進的泛光燈,通過人工方法產生自然印象。
莫迪亞諾將主人公的職業設置為攝影師絕非偶然,作家曾在訪談中提到,他經常思考光線的問題,對倫勃朗的《夜巡》充滿興趣。莫迪亞諾的作品總是營造出一種半明半暗的環境和氛圍,于是我們讀到了沒有開燈的臥室,讀到了咖啡館最里端的座位,讀到了人人提心吊膽的德占時期。莫迪亞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中說道:“占領時期的巴黎對我而言永遠都是最初的夜。沒有它,我就不會出生。這個占領時期的巴黎一直糾纏著我,我的書都沉浸在它那被遮蔽的光中。”如果說布拉塞通過照片為我們呈現了過去的巴黎圖景,那么莫迪亞諾則借助寫作把我們帶回到往昔歲月。在他的筆下,光與影相互交錯,勾勒出巴黎的日與夜,這座人人深愛的永恒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