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是否有“定則”? 《晨報副鐫》“愛情大討論”始末
百年前的現代中國,曾有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大討論”。那是在1923年初,北京《晨報》連續刊登了《譚仲逵喪妻得妻,沈厚培有婦無婦》《譚仲逵與陳淑君結婚之經過》兩封讀者來信,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張競生讀后有感而發,撰寫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經《晨報副鐫》主編孫伏園在該報發表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討論由此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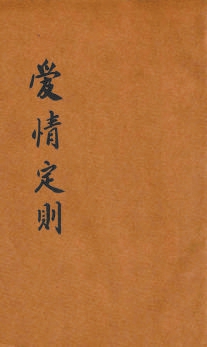
張競生《愛情定則》1928年4月出版
兩封讀者來信 引起教授關注
1923年1月16日,《晨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為沈厚培的“讀者來信”。投書者反映,陳淑君是自己在廣東時的未婚妻,與他早有婚約,然而,北大教授譚熙鴻(字仲逵)喪妻后,強迫妻妹陳淑君與之結婚。沈因此譴責譚道德淪喪,奪其所愛,吁請報社主持公道。不意第二天,陳淑君也致函《晨報》,指出沈所述與事實不符,自己與譚結婚系雙方自愿,完全是個人自由。
兩封來信,各陳其詞,針尖麥芒,各不相讓。由于當事人為社會名流,譚熙鴻是北大教授,陳淑君是陳璧君(汪精衛之妻)的三妹,所以格外引人矚目,一時輿論嘩然,社會熱議,更引起了對愛情、婚姻素有研究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競生的高度關注。
張競生與譚熙鴻同為留法同學,又是執教北大的同事,所以二人非常熟悉。1922年3月,譚熙鴻之妻陳緯君因產后感染猩紅熱癥,3月18日在醫院病逝,時年26歲,留下一雙年幼的兒女。同年秋,因陳炯明叛亂,廣東局勢混亂,在廣州就讀的陳淑君輾轉北上,寄居亡姐的家中,在北大當旁聽生之余,幫助姐夫照顧兩個痛失母愛的孩子,兩人日久生情、相戀并結婚,陳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獲悉后從廣州趕到北京興師問罪。
4月29日,張競生在《晨報副鐫》發表《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以“譚陳事件”為例,闡述愛情是一種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諸種因素的極繁雜的現象,提出“愛情有四項定則”:一是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是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是愛情是可變遷的,四是夫妻為朋友的一種。他在文中為陳淑君辯護:“她的愛情所以變遷,全受條件的支配。據她所說,見了譚宅亡姊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撫養”,“譚的學問、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所能及。這些條件均足左右陳女士對于沈譚的愛情。”張競生高度評價陳淑君的心靈解放和精神覺醒:“陳女士是一個新式的、喜歡自由的女子”,“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種朋友,可離可合,可親可疏,不是一人可專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愛或被愛的人,時時把造成愛情的條件力求改善,力求進化。”還突出強調:“主婚既憑自己,解約安待他人!憑一己的自由,要訂婚即訂婚,要解約即解約。”這些觀點,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一時滿城風雨。
圍繞“愛情四定則” 社會各界展爭鳴
五四時期,在覺醒的知識分子的引領下,科學與民主思想在中華大地狂飆突進,人們也熱切呼喚自由的、幸福的戀愛婚姻生活。張競生的“愛情四定則”振聾發聵,一場由一則“社會新聞”引發的“愛情大討論”呼之欲出。
《晨報副鐫》主編孫伏園敏銳地感知這是一個重大社會話題,于是策劃了一場系列討論。5月18日至6月25日,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在《晨報副鐫》連續刊發討論文章24篇、信函11件。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少數作(讀)者支持張競生的主張,絕大多數作(讀)者站在維護舊禮教的立場,且多是青年學生。
其中,北大教授梁鏡堯的反對聲音最為響亮,提出了與張競生截然相左的“愛情定則”:愛情是無條件、非比較的、不變遷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種。
更多的則是各有選擇、各有取舍。譬如,北大教員馮士造認為戀愛與婚姻,本是由友誼進步來的,因此,贊成“愛情四定則”的第四項,但對于愛情可以隨條件、經比較、可變遷的主張,他則極力反對。北大學生章駿锜也持相同意見:“除第四項我完全贊同外,其他三項與我的意見不合。”讀者丁勒生表示:“愛情可以比較,可以變遷,我全承認”,但“根本就懷疑有條件的愛情”,指出“我的意見是:愛情就是愛情,戀愛就是戀愛,絕不應摻入旁的一絲條件,不然,便不能算真正愛情、純正戀愛”。
一些反對者承認愛情有條件、可選擇、可變遷,這在婚前是正當合理的,但是一旦已有婚約或已結婚,就不應該再進行選擇,反映了在愛情、婚姻觀念轉型期的一種雙重標準的愛情選擇。例如,讀者世良指出:“我對于競生君的‘愛情的定則’的適用,要加一點限制,就是:‘愛情的定則,多半適用于未定婚約之前。’”
此外,一些反對者不僅對“愛情四定則”作了學理分析,還對譚仲逵的“不道德”、張競生的“偏袒”,提出了尖銳的嘲諷。讀者張畏民認為:“譚陳的知識、年齡、情形……不相當,他們絕對談不到愛情——狹義的——這是不用說的;就是以譚君處大學教授的地位,喪妻未久,同一個與他人已有婚約的女子去結婚,不能不受言論的制裁,張君偏要為一二人之私,破壞質樸的風俗,還要說什么‘愛情定則’,真正可嘆。”
孫伏園對于參與大討論的青年學生成為舊禮教的代言人,頗感失望。5月18日,他在《晨報副鐫》編前“按語”中表示:“可見現在青年并不用功讀書,也不用心思想,所憑借的只是從街頭巷尾聽來的一般人的傳統見解。”流露出滿懷的無奈和深深的失落。
周作人三撰文 一人演“雙簧”
6月20日,《晨報副鐫》在“雜感”欄目刊登署名荊生的短文《無條件的愛情》。“荊生”者,乃北大教授、著名文學家周作人的筆名。周作人不無調侃地寫道:
在我們這個禮儀之邦里,近來很流行什么無條件的愛情,即使只在口頭紙上,也總是至可慶賀的事。
于是我不禁記起什么筆記上的一條故事來。有一個強悍放縱的無賴獨宿在一間空屋里,夜半見有一個女子出現,他就一把拉住,她變了臉,乃是吊死鬼!他卻毫不驚慌,說他仍是愛她(原本的一句話從略)。
這似乎可以算是無條件的愛情的實例了,但總還有一個條件,便是異性。——倘若連這個條件也不要,那不免真是笑話了。
或者中國人大抵和我一樣喜歡說說笑話,所以那樣的主張也未可知。
作者以幽默的筆觸,諷刺了“愛情是完全沒有條件的”論調,贊同張競生“愛情四定則”中愛情是有條件的觀點,支持陳淑君的選擇。周作人的短文,作為討論的接續和延伸,不失為激烈論戰中一個巨大的正面回聲。
事實上,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就旗幟鮮明地抨擊舊禮教對愛情、婚姻的束縛,維護婦女權益。他在6月6日、6月15日,曾先后化名“鐘孟公”和“曹叔芬”,致書《晨報副鐫》,參與“愛情四定則”討論。其中,“鐘孟公”向“副刊記者先生”指出:
我現在以讀者的資格,對于愛情定則的討論這一件事,想進一句忠告的話。那些文章初發表的時候,我很有興趣的期待著,但到了現在讀過二十篇,覺得除了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佐證之外,毫無別的價值。先生還想繼續登載下去么?我想至少您也應定一個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是這樣的胡亂盡登下去了。
而“曹叔芬”則向“記者先生足下”主張表示:“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發表,不但可供小說家、醫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淺鮮。”
“兩人”觀點一紅一白,截然相反。一人分飾三角,更是催化了一波繼續討論“愛情四定則”的爭鳴。
許廣平與魯迅 前后參加討論
在“愛情四定則”討論中,許廣平和魯迅也不約而同地關注并參與其中,而那時他們還素昧平生。
魯迅和許廣平都飽受封建包辦婚姻之苦。1906年,魯迅迫于母命,與無愛的朱安女士結婚后,長期身受舊式婚姻的煎熬。許廣平出生僅三天,就被父親許配給香港一馬姓人家,20歲那年為抗婚,她北上天津入讀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
5月25日,許廣平以“維心女士”為筆名,投稿《晨報副鐫》,提出了不認同譚、陳結合,不認可張競生“愛情四定則”的看法,表現出一種與實際情形頗為迥異的角色沖突和觀念矛盾。
6月12日,《晨報副鐫》刊登陳錫疇等人的三封來信,他們一致要求停止“愛情四定則”討論。當天晚上,魯迅寫信給孫伏園,表明自己的立場:建議繼續討論下去。6月16日,《晨報副鐫》登載了魯迅的來信:
……鐘先生也還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為丑,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然還是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
雖然魯迅沒有直接回應“愛情四定則”的討論,但可以看出他對張競生的主張持贊同態度。兩年后,他在小說《傷逝》中,提出“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的命題,與張競生的愛情定則,異曲同工。
張競生“答復” “大討論”收官
這場大討論中,最直接的受害者無疑是譚熙鴻、陳淑君夫婦。然而,譚熙鴻并沒有因為所謂“緋聞”的影響而懈怠自己的工作,他繼續擔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履行教授治校職責,負責籌建北大生物系,并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經過前后一個多月時間的論戰,最后,張競生撰寫了近2萬字長文,發表在《晨報副鐫》,予以回應。
這篇《答復“愛情定則的討論”》上篇的開頭,張競生重申:“我在數年前已經留心研究愛情的問題了,但所擬就的愛情上幾個定則,終未拿出來向人討論。及到近來感觸了陳淑君女士的事情,使我覺得有宣布的必要。可是,處在這個不懂愛情的社會,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見的先生們,討論一個真正的改善和進化的愛情,使他們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屬為難。又要將一個被嫌疑的女子作為舉例,使他們不生誤會曲解,當然是更難之又難了。”同時,鄭重聲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許多無道理的攻擊,我對于陳女士和譚君唯有誠懇的道歉。”隨后,圍繞與他討論的文章、向他提出的問題,從四個方面一一分析闡述:“一、愛情是無條件的;二、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為愛情的條件,但名譽、狀貌、財產,不能算入;三、愛情條件比較上的標準;四、愛情定則,適用于未訂未定婚約之前,但不能適用于已訂已定婚約,或成夫妻之后。”最后,張競生向青年朋友們提出了中肯的建議:“你們如不講求愛情那就罷了,如果實在去享用真切的完滿的愛情,不可不研究愛情的定則,不可不以愛情的定則為標準,不可不看這個定則為主義起而去實行!”
持續一月有余的“愛情四定則”討論,至此偃旗息鼓。盡管張競生的理論有流于簡單化、絕對化和教條化傾向,然而,由此引發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于愛情的大討論,卻是一場對婦女解放與戀愛自由的全面啟蒙,昭示著時代的巨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