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長書 | 《花燈調》:讓鄉村巨變成為文學視野中的可見之物
2024年,中國作家網特別開設“短長書”專欄,邀請讀者以書信體的方式對話文學新作。“短長書”愿從作品本身出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也愿從對話中觸及當下的文學癥候,既可尋美、也可求疵。紙短情長,我們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學現場做出細讀,以具體可感的真誠探討文學的真問題。
“人只重視流血,而不重視流淚,是不對的。”《花燈調》原名《淚為誰流》,劉慶邦說,這是他準備了大半輩子的一部書。這種準備不是文學的修辭或技藝上的,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可以說,這部情感真摯飽滿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了觀察當下社會實踐的一個入口。“短長書”第6期,學者張元珂、趙牧以《花燈調》為中心,探討了關于時代的形象、思想與表情,可供有識者細讀。
——欄目主持人:陳澤宇
本期討論

《花燈調》,劉慶邦 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入選作品。
《花燈調》是作家劉慶邦的長篇新作,反映了脫貧攻堅歷史偉業下的時代生活。高遠村,一個“高原孤島”般的存在,這里停留在“刀耕火種”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這個地理條件與人文環境都極為惡劣的村莊如何脫貧致富?就在此時,向家明來到高遠村。向家明已經擁有了令人艷羨的工作、美滿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在檢察院跟高遠村之間,她選擇了后者,她走在田間地頭,攀在懸崖峭壁,宿在簡陋屋舍,在泥濘跟嚴峻中拓荒,在溝壑跟淤堵中楫水。從“走新路”到“闖新路”再到“致富路”,她將真心、良心、責任心付諸實際行動,展現出令人眼前一新的女性形象。
作者簡介

劉慶邦,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京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屆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斷層》《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黑白男女》《家長》《女工繪》等,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到處有道》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孫犁文學獎、南丁文學獎等。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國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短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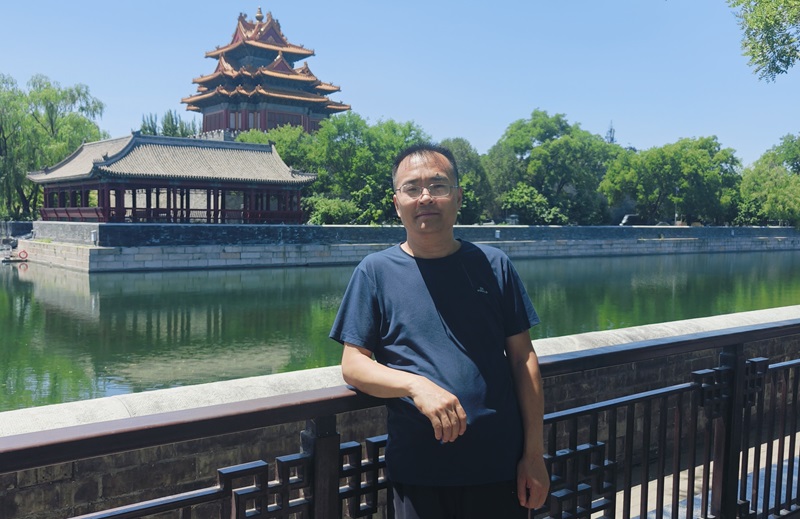
張元珂,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小說學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小說、傳記文學、新文學版本等。著有《中國當代小說專題研究》《中國新文學版本研究》《韓東論》《史與思——中國新文學史論與批評論集》。主編《現代作家研究》(八卷)等。
趙牧兄:
你好!你對劉慶邦有所關注或研究嗎?在我印象中,他向以短篇小說創作而蜚聲文壇,實際上,長篇小說也寫得不賴,比如,《平原上的歌謠》《遍地月光》《女工繪》。對之,我都曾多有關注、閱讀,并寫過兩篇評論文章。2024年1月,他的《花燈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反映新時代重大題材、帶有鮮明主題創作色彩的長篇新作。我之所以對他的這部長篇甚為關注并作了細致閱讀,主要因為近期我正在參與做一個由中國小說學會申報并立項的國家社科項目(《脫貧攻堅文學書寫與脫貧攻堅文學活動調研報告》),而《花燈調》恰好可作為一個典型文本予以重點考察。因之,就有若干問題提出來,想與牧兄交流交流。
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是發生于新時代中國最宏偉、最壯闊、影響最深遠的國家戰略和實踐活動之一。在此亙古未有之宏大歷史運動或時代背景下,對作家而言,以文學方式直接參與、思考和書寫這一進程,自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于是,我們看到,從2015年開始,尤其近3年以來,一大批脫貧攻堅題材文學作品——以報告文學和小說為最多——集中涌現。與創作此類題材作品的眾多作家相比,劉慶邦的創作動機更為特別:仔細閱讀《花燈調》后記《所為難得是情愿》,不難體悟到他對脫貧攻堅歷史實踐的無限感慨,以及他用長篇小說對之予以集中表達的主體愿景或精神動機——更多是出于一種源自生命本體的自我需要。他說:“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為這部書做準備。當初的準備不是文字、語言、藝術、和技巧上的準備,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我準備了半輩子,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由此推導,是不是他曾經親歷并深置于記憶中關于河南農村的貧困、饑餓,讓其靈感、情感又一次投射于貴州遵義這個偏遠山區的深度貧困村?劉慶邦是河南周口項城人,你也曾長期在河南求學、工作,你怎么看待如他這類“農裔作家”紛紛創作脫貧攻堅題材文學作品的動機及意義?
無論舊時代的鄉村或鄉土世界,還是新時代的“新鄉土”、“新農村”,都是一個各種觀念、關系和矛盾的紐結地。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以往“鄉土小說”或農村題材小說中會屢屢呈現出這樣一種主導性的修辭景觀,即從鄉村倫理(道德)、宗族紛爭或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入題出發,建構種種復雜關系,繼而達成對于農村世界乃至“鄉土中國”的勘驗、認知和表現。但在《花燈調》中,劉慶邦好像有意繞開這一傳統,而主動采用一種純化策略——即有意避開或弱化鄉村內部世界里的種種尖銳矛盾與沖突,而更多以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的主動作為、各級政府在政策、財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等各種外部視角、關系及力量為核心依托或動力機制——從而一步步達成對于扶貧干部形象的塑造、對于種種新關系的建構,以及對預定脫貧主題的集中表達。這種側重以高遠村外部力量及關系為著力點推進敘事、建構關系、生成主題的修辭實踐,恰好與國家層面上自上而下發起的脫貧攻堅運動,形成了一種互為參照、彼此闡釋的頗有意味的“間性關系”。因此,在我看來,與以往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相比,這部小說在敘事視角、策略和結構方面均展現出了某種新質、新貌。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進一步升華,你如何理解“新時代小說”的發展趨向和特有內涵?
實際上,無論政治層面上的脫貧攻堅運動,還是文學領域內的脫貧攻堅書寫,深扎農村的扶貧干部和作為被扶貧對象的農民,都始終是其中最具主體性和目的性的第一存在。然而不同于前者對于人的關注更多落實于物質技術層面,后者則尤重于對典型形象及其內在精神譜系的建構與揭示。或者說,“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或“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在脫貧攻堅題材小說創作中,依然是小說家們所要遵循并踐行的“金科玉律”。《花燈調》的審美價值和思想意義之所以引人關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塑造的核心人物向家明是“獨特的這一個”。在小說中,作為檢察院檢察官的她,無論職業、事業,還是家庭生活,原本都一帆風順、一派光明,但她還是毅然選擇到深度貧困的高遠村,作為駐村第一書記進駐脫貧攻堅第一線。在她帶領下,高遠村在物質上從極度貧困到徹底脫貧,在精神風貌上從舊顏到新貌,都獲得了質的突變與發展。那么,你如何理解她的生活世界、情感活動、理想抉擇?你怎么看待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除了主人公向家明外,哪一個或哪幾個人物讓你有所感觸?另外,關于如何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有何建議?
因為做課題項目,脫貧攻堅題材小說我倒讀了不少。在我看來,對于新時代新農村圖景的文學描繪、對于思想性的深入表達,以及對于新時代典型人物(扶貧干部、新農村新青年)的集中塑造,都取得了一定成績。若說不足或缺陷,我同樣覺得,人物形象及關系建構的模式化、雷同化,以及由直接圖解路線或政策所導致的文學性欠佳,倒是其中普遍存在的癥結。不知你是否有同感?具體到《花燈調》,我非常欣賞《花燈調》中的景物描寫(比如第一章第一段、第十一章第一段)、精準描摹細節或細部的筆法,但文學性上仍有深化空間。由是觀之,你對劉慶邦在《花燈調》中的“文學性”建構有何體驗或評價?在新時代,能否出現比肩柳青《創業史》或路遙《人生》那樣的杰作?你有何感想或建議?
牧兄,以上啰啰嗦嗦談了我的一點膚淺的閱讀感受,也順帶提出了若干問題。你若與我有同感,可作必要的答復;若無感,直接忽略即可;若覺得我對《花燈調》理解不到位,或者你有自己的新發現,也請多多指教!
恭祝夏安!期待牧兄來京一聚!
張元珂
2024年5月19日 于康泉小區家中

趙牧,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塔夫茨大學訪問學者,廣西壯族自治區電影局評審專家小組成員。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思潮研究、臺港及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以及文化人類學視野中的中外電影史研究。曾在《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文藝爭鳴》等刊物發表論文130多篇。
元珂兄:
您好!因為大家習慣于網絡上你一言我一語的即時交流,連郵件也很少使用,而久沒有收到這么長的信了。在信中談文學、談小說,在這個視聽化、消費性占據主導的時代里,也變得越來越稀缺了。所以,收到您的來信,非常開心而又忐忑,生怕對不住您的熱忱和信任,但也不敢怠慢,以您的來信做指引,認真拜讀了劉慶邦先生的《花燈調》,不揣冒昧,趕緊向您做個答復。
劉慶邦的作品,我相對來說,還算是比較熟悉的。這可能跟我曾經在礦業院校就讀,而后又在煤礦工作了4年有關,在我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已經是全國知名的短篇小說大家了。我到現在還記得,大約是在1995年暑假結束返校的火車上,我曾在一本雜志上讀到一篇報道,說是當時京城文壇有“三劉”——劉恒、劉震云、劉慶邦,是三個最有才華和風格的小說家。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劉慶邦的名字,而后又在大學宿舍樓下的報欄里讀到了他在《中國煤炭報》的一篇紀實,那是關于當年平頂山某煤礦的一次瓦斯爆炸事故的文章,其用平實的語言對那次慘烈事故的記述,更是給我留下了難以抹掉的記憶。一個鄉野出身而又在礦業學院讀書的大學生的文學愛好,就是從這里得到啟蒙和激發的。
據我對于劉慶邦創作的了解,他的小說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鄉村生活的記憶,另一部分是煤礦生活的記錄,而這兩個部分,其實又可以合二為一的。因為煤礦這一能源產業的特殊性,依附于煤礦而討生活的一群人,無論是礦工,還是家屬,絕大多數都有一個農村的背景,而礦區本身,雖然在二元制的城鄉戶籍體制下,被納入了城鎮的范疇,但其實卻被廣大農村所包圍的。有人曾經概括路遙的創作,說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內容不外乎“城鄉結合部”的生活,而這一結合,則恰就是煤礦的最大特色。所以,劉慶邦的作品雖然有大約一半的篇目是關于煤礦的,但是這些煤礦題材的小說,其實都跟鄉村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當然,這并非您所關心的重點。如您所言,《花燈調》這部小說“帶有鮮明的主題創作傾向”,而所涉主題,則正跟你們正在開展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脫貧攻堅文學書寫與脫貧攻堅文學活動調研報告”高度相關的。首先,我對選題獲得立項表示祝賀,而這一選題,不僅顯示了你們的學術眼光,而且包含了對社會的關懷。文章合而時作,課題更是如此,而且非如此不可。其次,這一項目的選題,也并非來自沒有根據的想象,而是基于當前創作的實踐: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作家進入到“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創作主潮了。我們知道,20世紀中國文學從傳統而走入現代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失去了傳統士大夫地位的作家從鄉村而進入城市,并因此而被賦予了一種現代性的視野,所以當他們從城市“卻顧所來徑”的時候,就讓城鄉對峙和沖突,變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在啟蒙、革命及其現代性的歷史發展脈絡中,隨時變換著它們的具體表現形式。但竊以為值得提出并加以討論的是,從“新世紀”到“新時代”,以城鄉互動為題材的創作,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先就我的了解聊聊這一變化。“新世紀”之初,中國加入WTO,在社會經濟領域加速卷入了全球化的進程,而與之相伴的是,大量的農民開始流轉遷徙于城市周邊的工礦企業,成為了沒有城鎮戶籍及相應社會保障的“農民工”。他們一方面流血流汗,為城市也為國家總體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另一方面,則又為之付出了巨大而又慘痛的犧牲。不僅在工礦企業里蒙受經濟壓榨,而且身心遭遇重創,以至于掙扎于城鄉之間,無論“留守”鄉土還是遷徙城市,都無所適從。這樣的社會現實,在學術界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不同的理論視野,不同的倫理視角,甚至不同的出身背景,提出了不同的解答。而作家們原本就擁有社會中最為敏感的神經,他們也就理所當然地對此做出了審美的回應。這中間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當中的左翼敘事傳統,就為此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文學經驗和觀察視角。
所以,在當時表現城鄉關系的作品中,農民工和下崗工人無疑充當了主角,關懷他們的處境和命運,呈現他們的悲哀與犧牲,不僅是一個審美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所謂的“底層文學”,雖回避了階級話語,但正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對這些融不進城市也回不去故鄉的龐大群體的代言。“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成為那時城鄉敘事中最為沉痛的一個提問:出身并成長的鄉村已“空心化”了,但在城市里,這一群體卻又因戶籍、教育、居住、社保等方面的因素而感受到巨大的排斥,所以鄉愁不再是一個知識分子化的審美,而是對于諸多社會不公的嚴肅提問:在這樣的審美視野中,我們很難指望“回鄉”會成為一個解頤的答案,原本已經破敗的鄉村,只能在這樣的現代性視野中繼續破敗下去,而一切的憤懣與不滿,都是指向“向城求生”的艱難,并強烈地呼吁獲得同等承認的可能。
然而新時代提供了另外一個可能。這就是隨著“鄉村振興”計劃的提出,“新的山鄉巨變”成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標。當然,這并非是對于發展路徑的放棄,而是在問題與反思中給出了“共同富裕”的抉擇:我們的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誰也不應成為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棄物。既然億萬農民為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理應共享發展的紅利。這與“向城求生”的“底層敘事”,有著相通的倫理前提,但所尋求的解答卻是南轅北轍的。但問題是,現代性所形塑的空間美學是以都市和消費為表征的,而為此所確立的修辭慣例,往往是城市代表了富裕、先進、時尚和新奇,而鄉村則是貧窮、落后、蒙昧和守舊的象征,難道說為著城鄉等值,就要蚍蜉撼樹,要徹底扭轉長久以來形成的城市與鄉村的審美形象嗎?
實際上,在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實踐中,像這樣的扭轉的企圖,已經出現過,那就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審美現代性訴求。在這個訴求中,城市的現代化變成了墮落和敗壞的代名詞,而鄉村呢,則無疑代表了一切淳樸和美好的事物。但這顯然并不是“共同富裕”“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等政策性訴求的方向,“新山鄉巨變”仍以發展為旨歸,除了強調“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觀念外,“巨變”與“改造”仍是共通的前提,只是“改造”的對象、“巨變”的目標,以及其中的受益者發生了變化,也就是億萬農民不再僅僅是實現發展目標的工具了。
所以說到底,“新時代山鄉巨變”是突出了現代化發展的溢出效應。在改革開放40余年后,中國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發展的成果,不能為城市及其相關群體所獨享。鄉村在這時候被納入“巨變”的視野,就是要強調城市的“反哺”,并且這一“反哺”的行為,是由黨和國家統一領導的。就此而言,您已經開宗明義地指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是發生于新時代中國最宏偉、最壯闊、影響最深遠的國家戰略和實踐活動之一”,而在這強調“共富”的新時代,作為作家,當然也應“以文學方式直接參與、思考和書寫這一進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新時代山鄉巨變”這一題材創作,常見由城市黨政機關中的國家干部為主人公,他們離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在黨的號召和組織的安排下,到貧窮落后的邊遠鄉村擔任“駐村書記”,帶領廣大村民實現發家致富的目標,實現鄉村世界的“舊貌換新顏”,就成為最主要的敘述模式。當然,這并非向壁虛構的結果,而是變化著的社會現實,而“駐村第一書記”本就是這一社會現實的參與者和政策的實踐者。
那么回到劉慶邦的《花燈調》,小說中的向家明作為高遠村的“駐村第一書記”,無疑內在于這一高度符碼化的人物系列。實在說,在這個人物譜系中,向家明不算一個血肉豐滿的形象,她幾乎所有的個人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的點綴和補充,但作為一個敘事技巧高度成熟的作家,劉慶邦成功地將這些點綴和補充,轉換在細節的烘托、情感的渲染和心理沖突的詩意描摹之中了。他既有的鄉土敘事經驗這時也被不動聲色地調動起來,“脫貧攻堅”這一艱巨的任務,似乎在瑣碎和家常的詩意中就可以輕易實現了。
相較“十七年”時期的農村題材創作中致力于“山村巨變”的英雄形象,向家明已經不再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而是工農結合的后代、具有了國家干部身份,“根正苗紅”的家庭出身是她不合常規卻又欣然接受兩次委派的前提。向家明實際上是有些不情愿的,后來還在駐村期間被迫離開檢察官隊伍,這明顯是柿子專拿軟的捏,有些欺負人的味道了。劉慶邦作為一個對人性有著充分了解的作家,必須將這一不情愿委婉地表達出來,所以特別設計了讓檢察院的領導安排她先去高遠村“看一看”這一情節,使得一切都是向家明自己選擇的結果。而被概念化的高遠村的“深度貧困”,也具體化為村上小女孩一家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處境,正是這一處境喚起了向家明的“慈母心”,意識形態需要也由此轉換為情感話語,她于是在對自家女兒優渥生活和學習條件的聯想中下定了決心。
當然,僅僅依靠這樣的情感話語,是沒有辦法實現新的“山鄉巨變”的。這一點,劉慶邦無疑也是清醒的,所以從一開始,他就指出之所以向家明在第一次的駐村工作中“沒有辜負領導和大家的期望”,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是因為她擁有“在市里工作的資源優勢”;而這一次,相關的資源優勢則是更進一步具體化為強大的家庭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復雜的關系網絡。當然,向家明的駐村,原本就是一種組織行為,她并非以純粹的個人身份駐扎在高遠村,而幫助村民們脫貧致富,理所當然也不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所以在高遠村有老支書和村主任協助,背后則是單位和家庭作后援團。這其中,她父母的作用是喚起社會主義前三十年的歷史記憶,為當下的“脫貧功堅”提供合法性的證明;而她的丈夫和妹妹們,則是提供現實的支持,這支持不僅是情感上的,而且是工作上的,即便工作上的,也不僅僅出謀劃策那么簡單,而是他們各自背后都有著強大的政商資源。劉慶邦將此敘述為脫貧攻堅的助力,這并非是他的文過飾非,而是借助于這一書寫,讓寫作者對于現實的觀察成為一種“可見之物”。
事實上,新時代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敘事,一方面當然是對于時代重大事件的回應;但另一方面,卻也讓被忽略和遺忘的廣大鄉村的貧困和苦難,變成了文學視野中看得見的事物。如果沒有國家層面的倡導,那些徜徉于都市的街頭流連于消費景觀的作家,怎么可能去關注鄉野事物,怎么會有興趣讓土的掉渣的內容“污染”他們審美的眼光呢?這可見不僅是倫理上的,也是審美上的,并由此而獲得書寫的合法性。劉慶邦說“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為這部書做準備”了,如果不明白這種鄉村情感的辯證法,我們是沒辦法理解他這樣的表達的。劉慶邦出生于河南的鄉間,經歷和感受過鄉村苦難,但這些苦難長久以來,在現代化敘事中,被審美上驅逐到了不見光的邊緣地帶,失去了審美的合法性,即便有個別作家堅持將它們作為表現對象,但卻無法獲得時代的聚焦效果。“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主題,讓這一書寫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被放在了聚光燈下。所以,作為一名出身于鄉村而又因為偶然因素脫離鄉村的作家,劉慶邦說他從剛記事就為這小說做準備了,就不是“矯情”,而是一種由衷的興奮。這樣的興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這樣的脫離了農村卻無法擺脫農村之根的讀書人感同身受的。您在信中提及一個概念,“農裔知識分子”,我雖然不敢托大,自視其中一員,但我確實為這樣的創作而高興,因為鄉野之地,在原來的現代化敘事中,已經被忽略了太長一段時間了,即便是有所關注,賦予它們鄉愁的意味,也從骨子里將它們視為應該逃離的地方。
從另外一個層面,劉慶邦所說的“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為這部書做準備了”,也可以理解為,這部小說中所涉及的鄉村事物都是他曾經見過的,也大多在他以往的小說中表現過的。這些熟悉的事物,在這次新題材的創作中,變換了方式重新出現了。所以這部小說雖在劉慶邦的創作歷史中顯現了新鮮的面容,但它卻調動了他此前大部分的生活和創作經驗。許多修辭的手段,敘事的方式,詩意的追求,都在他既有的小說中屢見不鮮。當然,如您所說,這部小說大多數地方采用了外部的視角和純化的策略,讓向家明這個“駐村第一書記”充當了外部的觀察者,這適應了主題要求:因為其一,既然向家明是一個外來者,她就不可能深入到高遠村的內部,弄清楚其中存在的宗族紛爭、倫理秩序;而其二,作為鄉村的幫扶者,她所代表的是一種由上到下的力量,她所有的行動都是“改造”,而沒辦法像人類學家那樣進行田野調查。當然了,這外部視角的選擇,可能也與劉慶邦的經驗有關。他出身在河南沈丘,黃泛區的平原生態,畢竟與小說中貴州遵義的山野之地有著很大差別,如果不從外部觀察,而硬性進入高遠村的內部,恐怕會自曝其短。
這大致上是我對于《花燈調》的理解。這些理解未必都能一一回應元珂兄在信里所提出的問題,但我想,鄉村振興題材創作,劉慶邦樂意參與并投入其間,強調其在自己生命和創作中的意義,這是很值得肯定的。而且如元珂兄所言,作為“農裔”讀書人中的一員,我也很樂見這樣的主題,讓廣大的農村和農民再一次成為合法的表現對象。要知道,如果沒有黨和國家層面的關注,農村和農民作為現代性視野中的弱者,大概率是被忽略和犧牲的。甚而至于,在發展的快車道上,他們更因為落后、貧弱、無能而被碾壓。在以發展為指路明燈的現代世界上,最擅長的工作,可能就是制造爭先恐后和追新逐奇的氛圍,而在這個過程中,抹除那些掉隊者、失敗者,是沒有倫理的負擔的,但黨和國家卻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執政理念,讓億萬農民分享發展的成果,而力推“鄉村振興”的戰略,這是何等的氣魄。作家參與其中,因為表達的急切,不免概念化、圖解化的“缺陷”,而失去了一部分所謂的“文學性”,但“文學性”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長久以來,就是因為對于“文學性”的強調,社會主義前三十年的工農兵文學傳統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遺棄了。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卻試圖扭轉這一“文學性”的壟斷,再次讓億萬農民成為現代建設中的“可見之物”,所以,我慶幸而又樂見這一新的時代主題的涌現,希望有更多作家參與到相關創作中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并不因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山鄉巨變”字眼而失去其價值的。
最后再次感謝元珂兄的信任和期待。將劉慶邦的《花燈調》以及與之相關的這么多宏大的問題拋給我,而我作為您所說的“農裔”出身的讀書人,又曾經在煤礦工作多年,自持對于劉慶邦以往的作品多少有些關注和了解,就不揣冒昧地將之承接過來,既認真拜讀了《花燈調》,并將之放置在現代中國的城鄉書寫傳統中加以觀照和思考。雖然我這樣的思考不免讓元珂兄發笑了,但我仍非常開心地認為,這樣的討論是一個非常有意義,因為這主題以及與之有關的創作,正是我們當下生活的根源,我們既從中而來,也不忘其根本。言多了,當與不當,都望多多包涵,而我也相信,元珂兄既然對于相關問題的關注,也應早已在胸中有了自己的答案,所以期待有機會北京拜訪,做進一步的討教。夏天來了,祝愿我們共同開心快樂,也一起參與新時代創作主題的討論。
此致
敬禮!
愚弟趙牧敬上
2024年6月1日,于南寧
“短長書”專欄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舊交替中踏浪而行,與時代交匯的心靈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