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吶喊》:經(jīng)典的誕生及輻射
原標(biāo)題:《經(jīng)典的誕生及輻射——<吶喊>初版百年紀(jì)念本導(dǎo)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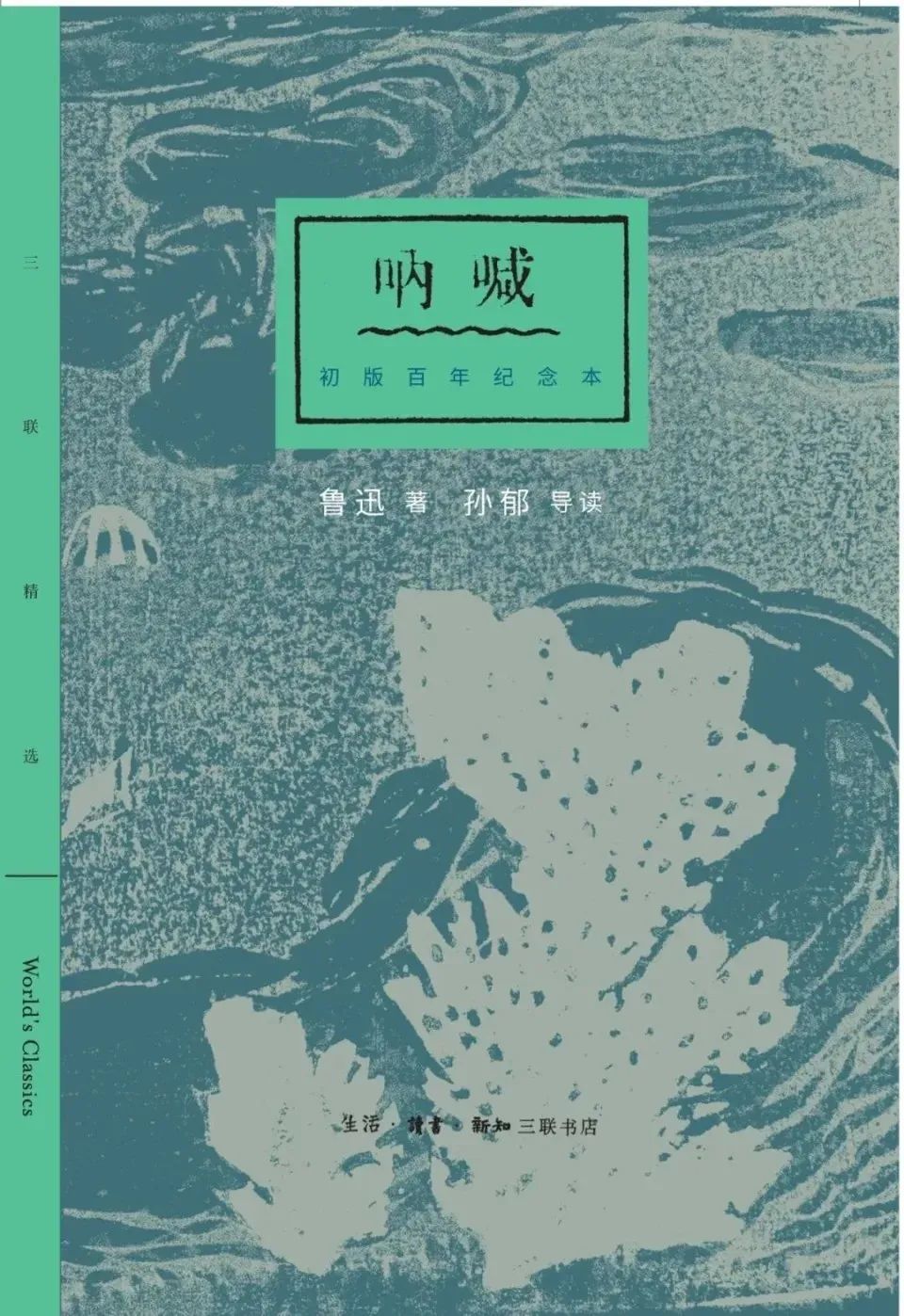
《〈吶喊〉初版百年紀(jì)念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23年版
一本書(shū)如果到了百年還被人不斷閱讀,那就有經(jīng)典的地位了。《吶喊》之于文學(xué)史,就是一個(gè)例證。自從新文學(xué)誕生以來(lái),翻譯、改編和研究它的文本,已經(jīng)汗牛充棟。而每個(gè)時(shí)期人們對(duì)于它的解析,似乎都并不是簡(jiǎn)單地重復(fù),還引申出新的題旨。百年間,面對(duì)這奇異的文本,夾雜了無(wú)數(shù)不同的讀者體驗(yàn),各式理論也滲透其間。這在新文學(xué)史中,可說(shuō)是十分少見(jiàn)的。
魯迅最初的小說(shuō),發(fā)表于《新青年》,剛一問(wèn)世,便被讀者稱(chēng)贊,喜愛(ài)者甚多。那時(shí)候《新潮》《晨報(bào)副鐫》《時(shí)事新報(bào)·學(xué)燈》《小說(shuō)月報(bào)》《東方雜志》《婦女雜志》都登載過(guò)他的作品,在文壇上是四面開(kāi)花的。凡是接觸這些作品的,都驚嘆于那體例的別致和思想的異樣,有一種意外之喜。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初期,《新青年》的同人寫(xiě)作,都是觀念性的演繹,主要是確切性的思想的表達(dá)。而魯迅的文字則沉潛在歲月深處,孤寂與熱望的氣流都有,流動(dòng)著理性所難以描述的體驗(yàn),舊中帶新,暗中含明。那些不便說(shuō)、難以說(shuō)的隱秘,在他的文本里卻一一出現(xiàn)了。
最早想出版魯迅小說(shuō)集的,是陳獨(dú)秀。他在1920年9月2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就以贊佩的口吻說(shuō)了許多自己少說(shuō)過(guò)的話,并有意促成作品集的出版,那信說(shuō):
豫才兄做的小說(shuō)實(shí)在有集攏來(lái)重印的價(jià)值,請(qǐng)你問(wèn)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lái)付印。
對(duì)于陳獨(dú)秀而言,魯迅的文本,拓展了漢語(yǔ)書(shū)寫(xiě)的空間,那畫(huà)面?zhèn)鬟f的信息和背后的隱含,超出了他對(duì)于新文學(xué)的想象。這說(shuō)明,魯迅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初期的成績(jī),已經(jīng)成為《新青年》同人值得夸贊的資本。無(wú)論陳獨(dú)秀還是胡適,內(nèi)心的喜悅都可以從他們的文字中看到一二。
1923年8月,魯迅的第一本小說(shuō)集《吶喊》在北大新潮出版社出版,書(shū)的封面是紅色的,毛邊本,19.5厘米×13.3厘米。《吶喊》最初收小說(shuō)15篇。它們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頭發(fā)的故事》《風(fēng)波》《故鄉(xiāng)》《阿Q 正傳》《端午節(jié)》《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不周山》。1930年第13版時(shí),作者抽去《不周山》,后改此小說(shuō)為《補(bǔ)天》編入《故事新編》中。至今的篇目,一直保留著13版的樣式,存小說(shuō)14篇。到1936年,共印刷23次。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說(shuō)自己是被拉到新文學(xué)陣營(yíng)的,寫(xiě)小說(shuō),也是別人催促的結(jié)果。在教育部時(shí)期,他絕望于故國(guó)的環(huán)境,對(duì)于以往的歷史亦多有灰色的感覺(jué),覺(jué)得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是沒(méi)有光明的地方。所以便一日日沉到時(shí)光深處,遠(yuǎn)去的歷史也毒液般刺激著自己,精神是苦痛的。加入《新青年》隊(duì)伍,他發(fā)現(xiàn)僅僅是悲楚地看人看事,與刊物氛圍是不一的,便也將一種啟蒙理念,偶帶入文本之中。于是那文字就非筆直的延伸,而是彎曲的迂回。在遲疑中尋找著什么,荒誕里裸露著什么。那些無(wú)望的、冷意的原野的邊上,也有花的抖動(dòng),預(yù)示著春的氣息的存在。眾小說(shuō)幽深而撲朔迷離,解釋起來(lái)并不容易。在凌亂的時(shí)空里,看得出,吶喊之聲還是微小的。
這十幾篇作品并非有意設(shè)計(jì)出來(lái),而是隨著自己的思緒慢慢流淌出的。彼此并無(wú)深的關(guān)聯(lián),題材也多樣的,可以說(shuō)是幾十年經(jīng)驗(yàn)的一種折射,還有研習(xí)國(guó)外藝術(shù)的偶得。只是它們都暗含在文本的后面,不易被察覺(jué)罷了。每一篇作品的審美背景,都含著不同內(nèi)蘊(yùn),知識(shí)色調(diào)與詩(shī)意的符號(hào)是不同于舊派小說(shuō)的。這里我們感受到了象征主義的晦澀,還有無(wú)數(shù)的寫(xiě)意之趣,內(nèi)中有著無(wú)所不在的荒誕感,許多作品仿佛層層隱喻的疊加,在調(diào)子里多了變聲。有的是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聚焦,有的是知識(shí)人命運(yùn)的揭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guó)社會(huì)片影都有所呈現(xiàn)。作品集中還有些靈動(dòng)超俗的主題,像兒時(shí)記憶的描述就讓人想起童話的世界,清秀與微明間,閃動(dòng)著夜間水鄉(xiāng)美色。最為奇異的是還有著神話《不周山》這樣的文本,茫茫洪荒里,流出燦爛的霞影,冰冷的世界誕生了未曾有過(guò)的靈光。天地萬(wàn)物,斑斕多姿地與讀者見(jiàn)面了。
在從事小說(shuō)寫(xiě)作之前,他已經(jīng)有了相當(dāng)多的精神準(zhǔn)備。幼時(shí)讀過(guò)不少古小說(shuō),后來(lái)還在大量的類(lèi)書(shū)里鉤沉舊小說(shuō)片段,用力甚勤。留日期間,開(kāi)始翻譯域外小說(shuō),對(duì)于英法、北歐、俄國(guó)、美國(guó)、日本的文學(xué)都有所涉獵。不僅感動(dòng)于域外藝術(shù)的特別,重要的是,攝取了近代哲學(xué)的許多營(yíng)養(yǎng)。比如尼采思想,克爾凱廓爾生命意識(shí),和托爾斯泰精神。以為惟有人的獨(dú)立,和個(gè)性的解放,才會(huì)有新的文明的出現(xiàn)。回國(guó)后,又多年沉浸在周秦漢唐遺物的趣味里,于出土文獻(xiàn)和地方志中,體味到別樣的審美傳統(tǒng)。在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思想發(fā)生著巨大的震動(dòng)。挫折與自信,絕望和渴念,復(fù)雜地交織在一起。他既不像陳獨(dú)秀、胡適那么慷慨激昂,也非章太炎、劉師培那么確然,而是在精神的荒原里流亡著。在小說(shuō)的世界里,那些飄散于野地的氣息,都聚于背景之中,而人物的氣質(zhì)里,多了士大夫們看不見(jiàn)的東西。
每讀《吶喊》,都覺(jué)得魯迅不僅僅是中國(guó)社會(huì)風(fēng)俗的畫(huà)家,描出了道道人間圖景,也仿佛擁有上帝之眼的智者,透出世間的陰晴冷暖,晨風(fēng)暮雨里,百物昭顯。總體來(lái)說(shuō),這部小說(shuō)集是魯迅內(nèi)心黑暗世界的一種釋放,他早年對(duì)社會(huì)的絕望在此得以直觀地呈現(xiàn)出來(lái)。還沒(méi)有一個(gè)作家能夠如此入木三分的寫(xiě)各種各樣的小人物。在這些人物群像里,一切都是昏暗和無(wú)望的,人不像人,而仿佛是被馴僵的病者。作品背后,有一雙通天之眼,看著凡俗間的不幸。比如《狂人日記》,就以瘋子的口,說(shuō)出仁義道德的背后是吃人。在《孔乙己》里面,寫(xiě)出一個(gè)被舊的教育制度所戕害的一個(gè)可憐的人,一些有趣的場(chǎng)景,里面是深層的悲哀,我們?cè)谶@種簡(jiǎn)約的筆法背后可以感受到作者復(fù)雜的情感。《白光》延續(xù)了《孔乙己》的意象,但驚恐的氣氛更濃了,那文字指示著舊式的文人之路無(wú)法走通。《故鄉(xiāng)》寫(xiě)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也流露出作者在沒(méi)有路的地方走路的渴望。《藥》感慨于革命者與大眾間的隔膜,解救百姓的人并不被百姓所理解。《明天》哀嘆了小民夢(mèng)境的無(wú)助,《風(fēng)波》的風(fēng)俗畫(huà)面,愜意之筆下,有對(duì)于鄉(xiāng)野之風(fēng)的無(wú)奈。《一件小事》寫(xiě)出人力車(chē)夫心性的美,也襯托出知識(shí)人的“小”來(lái)。只有《社戲》輻射了一幅美麗的鄉(xiāng)間圖畫(huà),那里是有作家對(duì)古風(fēng)的依戀和對(duì)童趣的依戀吧。
那些鄉(xiāng)下人,無(wú)論是農(nóng)民還是破落的讀書(shū)人,心態(tài)都被奴隸式的病灶所染。魯迅以醫(yī)生的眼睛看他們,內(nèi)心流溢著諸多悲哀。鄉(xiāng)下人善良和麻木的表情,我們見(jiàn)了要倒吸一口冷氣,美的隕落是人間大的不幸。魯迅留日時(shí)代憧憬的個(gè)人主義的文化情調(diào),在此完全沒(méi)有表達(dá)的空間,一切都還在古老的渾沌里。精神的痼疾乃人間大的不幸,在魯迅看來(lái),當(dāng)這些痼疾盤(pán)踞在我們周?chē)臅r(shí)候,人是感受不到陽(yáng)光的。
對(duì)于病態(tài)社會(huì)的描繪,在許多作品中是一個(gè)主調(diào)。小說(shuō)集中表現(xiàn)了病、藥、死的意象。在《藥》中,華小栓已經(jīng)病入膏肓,尋來(lái)的藥竟是革命者的血染的饅頭,但還是死掉了。這里,身體疾病和社會(huì)病,被魯迅巧妙地置于一個(gè)故事里,作品就從舊文學(xué)里的一般性故事進(jìn)入社會(huì)話題的隱喻性描述里。這個(gè)置放,是鴛鴦蝴蝶派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小說(shuō)家所沒(méi)有的,它不是一般性的技巧的問(wèn)題,而是生命哲學(xué)的自如的流露,甚至多了迦爾洵、安特萊夫所沒(méi)有的妙意。魯迅把不相干的元素有趣地嫁接于一體,這是其審美思維的一種跨越。社會(huì)批判意識(shí)與審美意識(shí)的交接處,恰是其精神有機(jī)整體的一次詩(shī)意的綻放。
新知識(shí)人與老中國(guó)兒女的關(guān)系,在小說(shuō)中也時(shí)可見(jiàn)到。與《藥》比起來(lái),《故鄉(xiāng)》彌漫著最為動(dòng)人的情愫。作者借著自己的經(jīng)驗(yàn),描述了回到故鄉(xiāng)搬家的故事,少時(shí)的玩伴閏土已不復(fù)當(dāng)年的英俊之氣,而是被生活重壓而變得呆滯,鄰居楊二嫂的世故之影,襯托出故土本有的遺風(fēng)。幾個(gè)孩子的天然的樣子,在此形成一種反差。以往美好的記憶被一種無(wú)可述說(shuō)的悲哀代替了。每一個(gè)人物都很鮮活,而背后的沉重的憂思,則給我們無(wú)限的悵惘。這無(wú)疑是一首詩(shī),離開(kāi)故土的人,在少時(shí)的地方?jīng)]有獲得慰藉,反而生出悲哀之感。但那悲哀后的思考,對(duì)于人間希望的冥思,仿佛尼采的《蘇魯支語(yǔ)錄》,帶出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感悟。存在先于本質(zhì),在沒(méi)有路的地方行走,大約才是無(wú)意義的意義。
《吶喊》的諷刺筆墨,給人留下的印象很深,這也吸收了《儒林外史》的敘述筆法,對(duì)于人的存在的不確定性刻畫(huà)得十分形象。有的作品也糅合進(jìn)了作者自己的影子,比如《端午節(jié)》,就讓人想起作者與胡適、錢(qián)玄同的關(guān)系,但主旨卻是在寫(xiě)知識(shí)人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的尷尬。小說(shuō)再現(xiàn)了新知識(shí)人在強(qiáng)大的物質(zhì)力量面前的無(wú)力感。《頭發(fā)的故事》似乎不像小說(shuō),不過(guò)是雜文式的走筆,全篇都是對(duì)白,但對(duì)于國(guó)人的健忘的感嘆,和辛亥革命苦澀記憶的表達(dá),看出魯迅在彼時(shí)的思想色調(diào)。對(duì)比作者批判愚民的語(yǔ)態(tài),對(duì)于知識(shí)人的譏諷,也毫不弱的。《風(fēng)波》將看似田園的鄉(xiāng)下社會(huì)內(nèi)在的暗流,很形象地點(diǎn)染出來(lái)。百姓價(jià)值觀念系在皇權(quán)社會(huì)里,時(shí)光流逝著,不變的是人的奴隸意識(shí),小說(shuō)借著九斤老太太的口,也譏諷了進(jìn)化思想對(duì)于古中國(guó)的不通。《兔和貓》《鴨的喜劇》在形式上都不太像小說(shuō),表面是童趣式的短章,其實(shí)也暗含著不少悖謬式的感覺(jué)。生命都有自身的限度,人的愛(ài)意可能也藏著殘酷的東西,弱肉強(qiáng)食是生命界可怕的存在。魯迅一面反諷,一面在荒誕的畫(huà)面里照著自己的形影,內(nèi)在的痛感,是可以時(shí)時(shí)感受到的。
《吶喊》中最有分量的無(wú)疑是《阿Q正傳》。作品是發(fā)表于1921年《晨報(bào)副鐫》一個(gè)“開(kāi)心話”的專(zhuān)欄,這副刊原來(lái)是李大釗所編,后任者是孫伏園。孫伏園是魯迅在紹興教過(guò)的學(xué)生,他搞了一個(gè)欄目“開(kāi)心話”,找魯迅來(lái)湊趣,《阿Q正傳》就這樣誕生了。開(kāi)筆的時(shí)候,他說(shuō)要寫(xiě)《阿Q正傳》很久了,可見(jiàn)那形象在內(nèi)心沉淀之深。作品始終帶著幽默反諷意味,看得出對(duì)于彼時(shí)風(fēng)氣與環(huán)境的揶揄。高一涵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形時(shí)說(shuō),有人看《阿Q正傳》連載,越來(lái)越擔(dān)心,怕下一步該罵到自己了。小說(shuō)發(fā)表時(shí)用的是筆名巴人,巴人是誰(shuí)?當(dāng)時(shí)大家都不知道。魯迅以匿名的方式,快意地?fù)]灑著筆墨,有意地與社會(huì)搗亂,和讀者搗亂,忽地揭開(kāi)被蒙在睡夢(mèng)里的人們的被子,一個(gè)觸目驚心的畫(huà)面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
阿Q這個(gè)形象,用學(xué)界一般的看法,寫(xiě)了中華民族那種負(fù)面的東西。后來(lái)有人研究他,指出是一種國(guó)民性的表現(xiàn)。這都不錯(cuò),也符合魯迅的思想。這個(gè)形象有樸素、勤勞的一面,也帶著游民的劣態(tài)。他在未莊里沒(méi)有地位,與人交往,既有樸實(shí)的一面,也染有狡猾與無(wú)賴(lài)氣。不太會(huì)與人正常的交往,求愛(ài)的失敗與在趙家人面前的失態(tài),說(shuō)明心智是扭曲的。他最大的問(wèn)題是精神勝利法,欺人又自欺。在弱者的面前表現(xiàn)出主子的兇狠,在強(qiáng)人面前就是一個(gè)奴才。所以魯迅最痛恨中國(guó)人多重角色和身份,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下多沒(méi)有定性,這是一種劣根表現(xiàn)。魯迅寫(xiě)他,讓人看到了人的奴隸相,自以為是,無(wú)特操,思維的模棱兩可……這作品絲毫不是超功利的愉悅,也不是什么雅趣的散步,作者以大的悲憫之心,寫(xiě)出深的悲劇,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就是這樣的吧。
小說(shuō)有許多片段極為精彩,比如革命那一章,就賦予了小人物時(shí)代的元素,阿Q一看革命的風(fēng)云起來(lái),也要湊過(guò)去。但是他不知道那革命的指向是什么,朦朧地感到要打倒財(cái)主們,于是以為有了機(jī)會(huì)。不過(guò)他要參加革命的目的頗為可笑,暗想的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shuí)就是誰(shuí)”。這就是當(dāng)年中國(guó)底層人的基本思想,千百年來(lái)農(nóng)民起義的因由不過(guò)如此。可是幾經(jīng)變化,趙家的人和假洋鬼子不準(zhǔn)他革命,便挨了哭喪棒。他回到土谷祠的時(shí)候,我們覺(jué)出了他的可憐,在這個(gè)等級(jí)制森然的社會(huì),鄉(xiāng)下的游民是沒(méi)有地位的。小說(shuō)的結(jié)尾,阿Q便被抓起來(lái),最后被送到了刑場(chǎng)槍斃掉了。這個(gè)時(shí)候,在滑稽和可笑中,散發(fā)出強(qiáng)烈的哀涼感。怪誕的人以怪誕的方式生活,也以怪誕的方式死掉,世界不是為不幸者設(shè)計(jì)的。魯迅寫(xiě)阿Q的革命,其實(shí)是對(duì)辛亥革命的一種回望,中國(guó)的革命是自上而下進(jìn)行的,可是在底層,參與者還是小農(nóng)意識(shí)主導(dǎo),充滿了國(guó)民性的陰暗面。國(guó)民性不變,不管是共和還專(zhuān)制,照例不會(huì)收獲幸福。
《阿Q正傳》的筆法很有意思,作者用雜文的思維入文,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寫(xiě)意和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幽默之感交織在一起。結(jié)構(gòu)不太講究,卻氣貫始終。他用反小說(shuō)的筆調(diào)為小說(shuō),就是讓很多人想起了《堂吉訶德》《奧勃洛摩夫》這樣的作品。周作人說(shuō)魯迅的《阿Q正傳》是受到了塞萬(wàn)提斯的《堂吉訶德》和日本的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的影響,也不無(wú)道理。夏目漱石的小說(shuō)是有反諷力度的,魯迅延續(xù)了夏目漱石的某些思想,他們的作品是有相同的意義的。偉大的小說(shuō)家都在司空見(jiàn)慣的人世間,見(jiàn)到我們常人不易見(jiàn)到的存在。阿Q是我們可憐人間的常態(tài)的人物,人們多視之不怪。魯迅卻寫(xiě)出其變態(tài)與可笑,在特定所指里,又多了發(fā)散性的隱喻。
《吶喊》是對(duì)于衰弱的民族的生活散點(diǎn)透視,不僅僅透出歷史之影,也有指示著進(jìn)化的艱辛。時(shí)間在這里是凝固的,生命被什么抑制住了。在這些風(fēng)格并不統(tǒng)一的文字里,折射著作者矛盾而痛苦的情感,但有時(shí)候又能夠以堅(jiān)毅的目光,瞭望那些被遮蔽的領(lǐng)域。他筆下的未莊、魯鎮(zhèn),成了老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縮影,集中了中國(guó)文化的許多元素。作者畫(huà)出了眾生相,也描出各類(lèi)人的心態(tài)。他移植了域外小說(shuō)的心理描繪手法,也善于從中國(guó)古小說(shuō)的筆調(diào)里吸收養(yǎng)分,敘述的方式靈活而多變。而他的審美意識(shí)也看不到儒家的說(shuō)教氣與道家的俗風(fēng),在入木三分的筆觸里,戳到了人們的痛點(diǎn),刺激了世人的思考。在那些不幸的、可憐的、無(wú)可救藥的人物命運(yùn)里,也鏡子般照出國(guó)人自己的樣子,但那鏡子里的世界是破碎的,到處都是錯(cuò)亂與雜音,曾被扁平化的世界,第一次被立體化,且呈現(xiàn)出不同的側(cè)面來(lái)。
魯迅小說(shuō)集一問(wèn)世,喝彩者不計(jì)其數(shù),很快就成了文壇的耀眼的存在。《吶喊》出版不久,《晨報(bào)副刊·文學(xué)旬刊》《民國(guó)日?qǐng)?bào)·覺(jué)悟》《時(shí)事新報(bào)·學(xué)燈》等媒體就作了報(bào)道。茅盾在1923年10月寫(xiě)下的《讀<吶喊>》,就說(shuō)了許多贊佩的話,認(rèn)為作品奇異的文字背后的隱喻,超出了尋常小說(shuō)的意味。他閱讀《狂人日記》時(shí),“只覺(jué)得受著了一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jiàn)了徇絕的陽(yáng)光”。同時(shí)又說(shuō):“在中國(guó)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chuàng)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shuō)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shù)人跟上去試驗(yàn)”。這樣的評(píng)價(jià)代表了讀者的普遍感覺(jué),內(nèi)中充滿贊佩與肯定的態(tài)度。1925年1月,張定璜在《魯迅先生》一文,對(duì)比了魯迅與蘇曼殊的作品,感到是全新的氣流的涌動(dòng),文章寫(xiě)道:
我若把《雙枰記》和《狂人日記》擺在一塊兒了,那是因?yàn)榈谝唬矣X(jué)得前者是親切而有味的一點(diǎn)小東西,第二,這樣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吶喊》的地位。《雙枰記》等載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fā)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guò)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按:相)去多么遠(yuǎn)。兩種語(yǔ)言,兩樣的感情,兩個(gè)不同的世界!在《雙枰記》《絳紗記》和《焚劍記》里面我們保存著我們最后的舊體的作風(fēng),最后的文言小說(shuō),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清波,最后的中國(guó)人祖先傳下來(lái)的人生觀。讀了它們?cè)僮x《狂人日記》時(shí),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聚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里來(lái),我們由中世紀(jì)跨進(jìn)了現(xiàn)代。
但也有批評(píng)家對(duì)于魯迅的小說(shuō)提出批評(píng)。創(chuàng)造社的成仿吾在評(píng)價(jià)《吶喊》時(shí),就以為過(guò)于寫(xiě)實(shí),惟有《不周山》尚可,因?yàn)榉侠寺傻目栈弥肌:髞?lái)的郭沫若、阿英都曾對(duì)于魯迅有些微詞,說(shuō)起來(lái)對(duì)于那文本有諸多隔膜之處。新文化人迷信自己所鐘愛(ài)的概念,而魯迅之于小說(shuō),恰是因了觀念不能覆蓋精神的非邏輯的一面。倒是審美的靈動(dòng)的莫測(cè)之影,反到能觸動(dòng)存在的一角,那些被遺漏的圖景,也被觸摸到了。
創(chuàng)造社諸人疏遠(yuǎn)《吶喊》,有觀念上的差異,他們視野里的文本,是被涂上主觀的顏色的,客觀性的眼光被遮住了。倒是一些了解魯迅的人,看出那書(shū)里重要的隱含。在創(chuàng)造社成員中,只有郁達(dá)夫認(rèn)可魯迅,他曾說(shuō),“我對(duì)于魯迅哩,也無(wú)恩無(wú)怨,不過(guò)對(duì)于他的人格,我是素來(lái)知道的,對(duì)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見(jiàn)解。我總以為作品的深刻老練而論,他總是中國(guó)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從前這樣想,現(xiàn)在也這樣想,將來(lái)總也是不變的”。
而那時(shí)候的青年學(xué)子,對(duì)于魯迅的作品是十分入迷的。馮至《魯迅與沉鐘社》寫(xiě)道:
從《史記》、漢賦、唐宋古文轉(zhuǎn)到魯迅的《藥》,是一個(gè)要費(fèi)很大力氣的跳躍。文字,當(dāng)然比古文容易懂得多了,可是理解其中的涵義,并不容易(中略)此后,凡是魯迅發(fā)表作品,我都找來(lái)讀,有的自以為懂得了一些,有的并不懂。印象最深的,是魯迅小說(shuō)中最短的一篇《一件小事》。我記得清楚,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寒冷的一天,我得到一份《晨報(bào)周年紀(jì)念增刊》,在課堂里聽(tīng)課時(shí),我把增刊中發(fā)表的《一件小事》反復(fù)閱讀,那人力車(chē)夫崇高的形象感動(dòng)得我留下淚來(lái)。
這還是一般性的閱讀感覺(jué),尚沒(méi)有上升到深入的思考里。許多年后,魯迅的學(xué)生孫伏園,就對(duì)《吶喊》中的十篇作品,作了專(zhuān)門(mén)的解析,每一篇心得,都有特點(diǎn)。他認(rèn)為《吶喊》對(duì)于人的變態(tài)心理的描述十分深刻。《魯迅先生的小說(shuō)》寫(xiě)了筆下人物“被瘋”“被禁閉”“被打”“被殺”“被吃”五個(gè)狀態(tài):
魯迅先生用了上列的五項(xiàng)來(lái)說(shuō)明一個(gè)革命的先知先覺(jué)者所身受的苦難。這些苦難是誰(shuí)給他的呢?他們正是和他同國(guó)家同民族而且和他無(wú)仇無(wú)怨的大多數(shù)人們。他們?yōu)槭裁匆堰@些苦難給他呢?因?yàn)樗麄冇薮溃麄兪芘f禮教的重壓,年深月久,積非成是,生活得服服帖帖,根本不知道解放為何物,也根本不承認(rèn)解放的可能,自然根本沒(méi)有夢(mèng)想到天下竟有人甘心犧牲自己的一切為謀大多數(shù)人的解放而革命的事了。他們雖然和他無(wú)冤無(wú)仇,但是他竟要?jiǎng)訐u他們服服帖帖的生活,他們于是要以上列五項(xiàng)辦法對(duì)付他。
在表面上看,魯迅先生用盡力是描寫(xiě)革命者的苦難,以反映大多數(shù)人們的愚蠢,偉大的同情似乎專(zhuān)注在革命者一方面。但是實(shí)際上,作者對(duì)于大多數(shù)受舊禮教重壓的人們,只是客觀地描寫(xiě)他們的愚蠢,并沒(méi)有從心底里憤怒、憎惡、嫉恨的情感。反之,他的偉大的同情,決沒(méi)有因?yàn)樗麄兊挠薮蓝鴾p少了分享的權(quán)利,也就是說(shuō),決沒(méi)有因?yàn)樗麄兊挠薮蓝H損了他的同情的偉大。
魯迅的被人喜歡,還因了那筆下的人物形象,與國(guó)人的日常所見(jiàn)所思相同,具有一種親切之感,仿佛身邊的人物被那些文字召喚了出來(lái)。《吶喊》問(wèn)世不久,大學(xué)生們就習(xí)慣于將小說(shuō)人物與身邊的人對(duì)應(yīng)起來(lái),一時(shí)形成一種風(fēng)氣。陸晶清在《魯迅先生在女師大》一文就寫(xiě)道:
有些同學(xué)熟記了許多魯迅先生的口語(yǔ)、名言、警句,常在講話中引用,有時(shí)在和魯迅先生講話時(shí)也搬用態(tài)度語(yǔ)言。他筆下的人物,如七斤嫂、九斤老太、楊二嫂、閏土等等,我們選用作對(duì)幾位同學(xué)戲稱(chēng)。阿Q的大名,常用來(lái)自稱(chēng)或稱(chēng)呼別人。
這也引起人們對(duì)于魯迅那文本的好奇。胡適覺(jué)得是接受了日語(yǔ)、德語(yǔ)、文言的緣故,許壽裳感受到了野史的影子,周作人認(rèn)為是域外作品影響的結(jié)果。多年以后,談及那時(shí)的作品的出世,作者自己說(shuō),是受到域外小說(shuō)的影響,那是夫子自道。從他的翻譯歷史看,譯過(guò)英國(guó)、德國(guó)、法國(guó)、美國(guó)、日本、俄國(guó)的小說(shuō)家的作品,尤以俄國(guó)小說(shuō)最多。他受過(guò)托爾斯泰的影響,但在表現(xiàn)手法上,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對(duì)于他的影響更大。不過(guò),那也是間接的影響,所以他自述時(shí),認(rèn)為尼采、果戈理、安特萊夫更讓他注意。他說(shuō):
在這里發(fā)表了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shuō)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xù)的出現(xiàn)了,算是顯示了“文學(xué)革命”的實(shí)績(jī),又因那時(shí)的認(rèn)為“表現(xiàn)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dòng)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dòng),卻是向來(lái)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xué)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guó)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jīng)寫(xiě)出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shuō)過(guò)“你們已經(jīng)走了從蟲(chóng)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chóng)豸。你們做過(guò)猴子,到了現(xiàn)在,人還尤其猴子,無(wú)論比那一個(gè)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式的陰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雖然脫離了外國(guó)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魯迅的自述,也遺漏了知識(shí)庫(kù)里另外的元素。郁達(dá)夫就認(rèn)為,在俄國(guó)作家中,契訶夫?qū)τ隰斞傅挠绊懸彩谴蟮摹_@是從短篇小說(shuō)的結(jié)構(gòu)和思想層面得出的結(jié)論。為什么說(shuō)契訶夫?qū)τ隰斞甘种匾峭袪査固┖屯铀纪滓蛩够窟@里含著不少未被注意的因素。通常的讀者認(rèn)為,魯迅的精神氣質(zhì),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更為接近。因?yàn)槠鋽⑹隹臻g和時(shí)間觀念,都是多維的,不確切性的。這也很像尼采所云的超人之眼。這里幾乎看不到傳統(tǒng)士大夫的目光,在陌生的筆觸里,世界被賦予了另一種意義。但魯迅身上的別樣元素,郁達(dá)夫是感受到了,那就是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存在一種糾結(jié)。納博科夫就說(shuō),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傳統(tǒng)的斯拉夫人,而契訶夫是與斯拉夫的傳統(tǒng)是遠(yuǎn)的。端木蕻良在一篇文章里說(shuō)俄國(guó)的一些作家像是病人,而魯迅卻是一名醫(yī)生,這道出了魯迅與一般作家的某些區(qū)別。從這個(gè)角度看,《吶喊》《彷徨》等作品所以有巨大的魅力,與那文字背后的非儒家元素有關(guān)吧。
1924年,魯迅的小說(shuō)就已經(jīng)入選到中學(xué)語(yǔ)文課本,后來(lái)也成為大學(xué)教員研究的對(duì)象。但魯迅對(duì)于自己的作品被選入課本,有一種悲哀的感覺(jué),他覺(jué)得自己的作品是有毒的,對(duì)于孩子并非合適的閱讀對(duì)象。可是那時(shí)候的新文學(xué),多還在單一的邏輯里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可謂是一覽無(wú)余。而魯迅的作品則于凡俗里流出深淵的幽思,片段中折射著無(wú)量的悲苦。有時(shí)候似乎是一杯苦酒,傳遞到每個(gè)神經(jīng)末梢,心劇烈地跳動(dòng)起來(lái),讓人在瞬間有了蠕活的感覺(jué)。北大的學(xué)生顧隨在致友人的信中就說(shuō):
契霍甫(按,契訶夫)有云:人,誰(shuí)也不是托爾斯泰呀!若在中國(guó),則又當(dāng)云:人才一作文,誰(shuí)也不能立刻成為魯迅先生也。
對(duì)于魯迅的小說(shuō),翻譯界的反映也是快的。1922年,《孔乙己》就被譯成日文;1925年,敬隱漁將《阿Q正傳》譯成法文;1926年美國(guó)華僑梁社乾將《阿Q正傳》譯成英文;1927年,朝鮮人柳樹(shù)人把《狂人日記》譯成朝鮮文;1929年俄國(guó)翻譯家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禮)在列寧格勒推出俄文版《阿Q正傳》;1936年,捷克漢學(xué)家普實(shí)克與魯迅建立聯(lián)系,開(kāi)始系統(tǒng)翻譯《吶喊》,次年在布拉格出版。在眾多的譯介中,日本的譯者人數(shù)最多,態(tài)度都很認(rèn)真。日本學(xué)者、作家欣賞魯迅者,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文字。比如作家佐藤春夫在1932年寫(xiě)下的《<故鄉(xiāng)>譯后記》中說(shuō):
他的作品中,的確具有很深的傳統(tǒng)意味。他從學(xué)者生涯蟬蛻之后,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一面誘掖指導(dǎo)建設(shè)新文學(xué)的運(yùn)動(dòng),一面自身也從事新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中略)1921年終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傳》問(wèn)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種,都使他名聞天下。創(chuàng)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國(guó)文學(xué)的翻譯介紹,經(jīng)過(guò)不懈努力,終于成為中國(guó)近代文學(xué)之父,完全盡到職責(zé)。他的成長(zhǎng),即使放在中華民國(guó)近代發(fā)展史上來(lái)看,也是非常偉大的。在今天,他不僅是“中國(guó)最偉大的小說(shuō)家,全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領(lǐng)袖”,而且還因羅曼·羅蘭的介紹而名噪法國(guó)。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譯本。魯迅是世界的。
按照芥川龍之介的看法,佐藤春夫是一名帶有詩(shī)人氣質(zhì)的小說(shuō)家,他的文字有“世紀(jì)末的情緒”。他的看重魯迅,也許是從作品中嗅出灰暗的氣息,以及愛(ài)意的力量吧。而這背后還有穿越現(xiàn)象對(duì)本質(zhì)的透視,這才是別人不及之處。日本人對(duì)于魯迅的喜愛(ài),也持續(xù)了一百多年。他們或許在這位中國(guó)作家的文本里,看到了島國(guó)的某些影子,或者說(shuō),在那面鏡子里看到陌生的自己。但中國(guó)的學(xué)者在不同時(shí)期,對(duì)于《吶喊》的理解則是另一種樣子。本土的糾結(jié),一直沒(méi)有散去。而日本人則感受到那文字散出的,東亞式的讖語(yǔ)。這是中國(guó)大陸學(xué)者許久沒(méi)有意識(shí)到的。魯迅的世界性意義,多年后才被國(guó)人一點(diǎn)點(diǎn)談及。
世界各地的讀者對(duì)于魯迅的評(píng)價(jià),似乎都沒(méi)有日本學(xué)者和作家那么深刻徹骨。羅曼·羅蘭與法捷耶夫?qū)τ隰斞傅脑u(píng)價(jià)都是印象式的,但日本知識(shí)界發(fā)出的聲音似乎纏繞著更為復(fù)雜的隱喻。這大概觸及了東方人敏感的神經(jīng),帝國(guó)文化向現(xiàn)代文化轉(zhuǎn)變之痛,于思想自新過(guò)程的艱難也于此可以見(jiàn)到許多。魯迅翻譯過(guò)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有島武郎等人的作品,內(nèi)心對(duì)于一些意象未嘗沒(méi)有親切之感。這里涉及“文明”“開(kāi)化”“現(xiàn)代”“解放”諸多話題,2008年,我在魯迅博物館與大江健三郎有過(guò)一次交談,聽(tīng)他談對(duì)《吶喊》的理解,才明白日本知識(shí)界欣賞魯迅更為深切的原因。
無(wú)數(shù)的讀者親近魯迅作品,不僅僅是那東亞式的困境的描摹,也非俄羅斯氣息的流轉(zhuǎn)。在魯迅那里,外在于東方人的哲思是顯而易見(jiàn)的。在無(wú)數(shù)可感的、悲劇性的畫(huà)面外,站著一個(gè)清醒的審視者,那上帝般的眼睛穿過(guò)世俗社會(huì),直逼精神的痛點(diǎn)。在《吶喊》的眾生相里,少有醒來(lái)的個(gè)人,多是“無(wú)信者”的木然和病態(tài)。世界被舍斯托夫所說(shuō)的“天然無(wú)知者”所充塞。但是魯迅又克制著自我形象的過(guò)多投射,而是盡力讓自己筆下的人物自己活動(dòng)與說(shuō)話。就如卡爾維諾所說(shuō):“以眾多的主體、眾多的聲音、眾多的目光代替惟一的能思索的‘我’”。這構(gòu)成了個(gè)體的知識(shí)人與眾生相的復(fù)雜關(guān)系,它不僅僅是一種生活的記錄,而是一種選擇。是進(jìn)入苦難者內(nèi)心而拯救的悲憫。這種情調(diào)在儒家與道家的世界里沒(méi)有,倒是與基督教與佛教的某些精神相近,但魯迅又不是基督徒和佛教徒。于是我們?cè)谶@里看到了另一個(gè)審美意識(shí)的閃動(dòng),這是以往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家里沒(méi)有的存在,而這些,恰恰鏡子般照出靈魂里的原色。
新中國(guó)成立后,《吶喊》研究日趨深化,所涉獵的范圍,既有辛亥以來(lái)的文化經(jīng)驗(yàn),也有對(duì)世界文學(xué)格局的思考。陳涌以蘇聯(lián)文學(xué)理論為參照,討論的是魯迅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問(wèn)題;而王富仁的博士論文則受列寧對(duì)于高爾基評(píng)價(jià)的影響,認(rèn)為《吶喊》是反封建的一面鏡子,后來(lái)的汪暉的研究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哲學(xué)的理念,從“反抗絕望”看出魯迅的精神氣質(zhì)里誘人的動(dòng)因;不久王乾坤在《魯迅的生命哲學(xué)》里思考了有限性的問(wèn)題,就與海德格爾的思想碰撞在一起。嚴(yán)家炎、高遠(yuǎn)東、吳曉東對(duì)于魯迅的小說(shuō)也做過(guò)不同的解釋?zhuān)渲懈哌h(yuǎn)東的《吶喊》研究說(shuō)得頗為深切:
魯迅的小說(shuō)產(chǎn)生于文學(xué)和文化典范轉(zhuǎn)移的革命時(shí)代,面臨著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寫(xiě)作規(guī)范的“兩面夾攻”;其思想和心理發(fā)生的過(guò)去的經(jīng)驗(yàn)與肩著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種種陳規(guī)“閘門(mén)”而從事新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矛盾,決定了他為現(xiàn)代小說(shuō)乃至現(xiàn)代文學(xué)重建文學(xué)范式——作為經(jīng)典的意義,主要表現(xiàn)于語(yǔ)言、思想、形式等方面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化的創(chuàng)造性上。他的小說(shuō)所具有的鮮明的民族品格和現(xiàn)代性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力的結(jié)晶,這也是當(dāng)今魯迅小說(shuō)的價(jià)值之所在。
當(dāng)年出版《吶喊》,魯迅不過(guò)是呼應(yīng)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風(fēng)潮,希望以此敲敲邊鼓,讓更多的人醒來(lái)。雖然后來(lái)說(shuō),自己的寫(xiě)作,是反映人生,而目的在改良人生,但他對(duì)于文字的效果如何,并無(wú)把握,他也曾表示,并不奢望那些作品永傳于世,希望它們能夠速朽。倘若自己攻擊的對(duì)象與那文字一同消失,其任務(wù)也算完結(jié)了。可是時(shí)光過(guò)了一百年,《吶喊》依然是不斷被閱讀和敘述的文本,一些人物還被標(biāo)簽化于日常的口語(yǔ)里,因此,說(shuō)他的文字已經(jīng)融化于國(guó)人的血液里也是對(duì)的。先生曾希望燃燒后的灰燼永逝,但那光澤卻在廣遠(yuǎn)的地方擴(kuò)散著,依然呈現(xiàn)著存在的不可思議之狀。這是怎樣的耐人尋味。魯迅的形影伴著數(shù)代青年,迎著浪頭趕去。那路有多長(zhǎng),先生的影子就有多長(zhǎng)。一個(gè)敢于喊出自己心音的思想者,是無(wú)所畏懼的,《吶喊》就這樣啟迪了一代又一代勇于尋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