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啟示錄——從《皮囊》到《命運》

明湖讀書會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個在暨南大學中文系現當代專業老師指導下由愛好讀書寫作的學子組成的讀書會,成員含本科生、碩士、博士百余人,成員從2019年起曾參與《作品》雜志的“品藻”專欄及“明湖杯”大學生文學評論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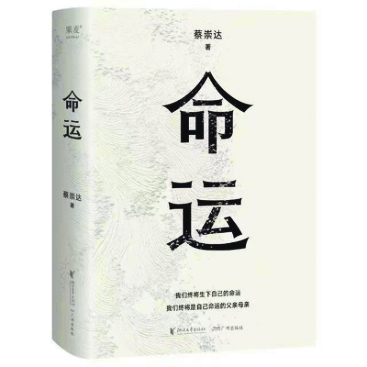
申霞艷:明湖讀書會這次讀長篇《命運》,這本書很感人,百歲老人阿太的一生給我們諸多啟迪。蔡崇達的非虛構作品《皮囊》讓我們結識了阿太,她是作者外婆的養母,也是《命運》的主角。附錄引用《皮囊》與開篇形成圓環,將虛構導向真實。紀德說:“人應該時時懷有一種死的懇切。”阿太正是如此,她無數次迎接死神、觀摩葬禮、拜訪神明、眺望大海、憑吊人生……阿太不能生育,卻在丈夫下南洋后拉扯大三位子女,素樸、寬廣而仁慈的阿太乃中國婦女精神的縮影。小說中對閩南民俗尤其是神明的刻畫可圈可點,作為敘事空間的大海對人們精神的熏陶等方面都值得大家深入討論。
邱毓賢:《命運》是一本海邊之書。99歲的阿太輕柔地回憶她的一生。在多重代際的故事中,“海”乃核心意象,“討海”的“討”一字微妙點出人與海的關系。疍民向海“討”來了生活,也“討”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大海洶涌的波濤折射出人們的生存鏡像。阿太的母親在礁石上滑落葬身大海。阿太的丈夫出海掙錢,前往臺灣的人從此匆匆登陸。來自北方的饑荒家庭就此投海,臺風掀起的海水將人覆沒。北來、西來、百花三個孩子來自不同地區。蔡屋閣、北來、西來乘船前往馬來西亞。這片海因此成為“故事之海”,也成為“命運之海”。人們尋找心頭的壓艙石,使自己不要為命運所流放。它看似接受生活的推動,實則捏住存在的變數。阿太平視命運,既供奉神明,向神明求助,亦敢于與神明吵架。這種善意與不屈支撐起獨特的閩南生存哲學。最終,面對人應該如何活著的難題,《命運》給出“海我相融”的答案。站在入海口的阿太往陸地回望。她的故事匯于浩瀚汪洋。
曾 嶸:《命運》以幾代人的故事探討故事之于生命的意義。小說主要由阿太的回憶敘事構成,文中頻繁出現的“我阿太”“我阿母”“我阿妹你太姨”“你外婆我女兒”這類主語,制造出重巒疊嶂的敘述效果,命運也由此獲得了復雜的表現形態。我們從中不僅看見個人的婚喪嫁娶、家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感受到歷史的時隱時現——二十世紀百年中國史中的戰爭與革命。小說提出了一個嚴肅命題:故事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神婆搜集故事、反哺世人,是民間最有魅力的“講故事的人”。蔡也好的通靈本領并非神靈所賜,而是來自包容和堅忍的品格。她懷抱廣闊的時空,將“神話”“鬼話”“人話”盡收耳中,打破了海與陸、天與地、生與死的區隔,這是經受歲月磨煉后的智慧和魄力。蔡屋樓傾聽命運,接納苦難,在死神面前傲然挺胸,展示“認命”和“抗命”的樸素辯證法。她通過敘事賦予時間以意義,賦予生命以尊嚴,丈夫楊萬流、妹妹蔡屋閣,還有孩子北來、西來、百花,都經由講述再次獲得了生命。原來“講故事”就是生命的通靈術,我們需要故事,包括老者的口述、抽簽詩、僑批、電報、悼詞……讀者作為聽故事的人,正如文中的“死亡觀摩團”,在貯存記憶的同時獲得療愈,獲得直面死亡、修改命運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命運》關于故事也關于生命。
邱文博:《命運》的主體是阿太的五段回憶,每一段回憶皆以死亡作結。小說中的死亡大致可分三類:一是如果子成熟后自然掉落般的死亡。蔡屋樓坐在被玫瑰花包裹的院子里,看著身旁一生的物品,和曾孫講述屬于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如同一條潺潺流淌的溪流,緩慢平坦地匯入死亡的海洋。二是內心的不甘與執念始終無法疏解,最終郁結而死的死亡。“阿太”的祖父一生都在與命運抗爭,試圖幫助宗族延續香火,卻始終搞不明白命運,被人生的問題卡住無法掙脫,最終行至暮年,內心始終不甘,郁郁寡歡而死。三是被命運戲弄,生命的溪流在經過山谷時突然墜落成瀑布,在拐彎后就突然匯入大海消失不見的死亡。“阿太”的阿母突然墜海、北來入海自殺,西來突然病故,他們都是被命運戲弄,生命突然走向死亡。小說通過對死亡的書寫來討論“人的一生應該怎么活”這一話題,正如“阿太”的阿母陷入生存困境時,神婆只是帶她去看葬禮,去目睹死亡、聆聽故事。在小說看來,無論哪一類死亡,都蘊含了不同人生選擇和命運抗爭下的生存哲理。漂浮的魂靈、庇護的神廟、神圣的神明、守護的祖先,便是死亡教給這座小鎮居民的生存哲學。小說也希望借對死亡的書寫,傳遞著向上的生存力量,慰藉著每一個正在人世間辛苦生存的人,支撐著每一個正在與命運洪流抗爭的人。
古格妃:《命運》的敘述節奏從容舒緩,凝結著作者關于時間、命運、死亡等重大疑難的體悟。“怎么活”的人生難題橫亙在每個人面前。臨海而居,信奉神明,自給自足的人們靠海活著,也靠故事活著。神明崇拜盛行的閩南地區,香火繚繞于城中與心間,但不同于簡單貼上的迷信標簽,小說中,神界與人間的界限并不分明,神會因為忙不過來轉而求人幫忙,人也可以和神嬉笑怒罵,人們進神廟,聽故事,討說法,在神殿靜坐的時刻,靈魂得以晾曬,命定的說法因而有了多重的解釋空間。在這里,神更多是人內心信仰的投射,可以和鬼神對話的神婆,從人性中發掘到了神性,并將其放回神龕。此外,神性也能在講述中生長,老年的阿太通過講述故事,成為當地最好的神婆,人性與神性相依相生。神廟里的故事積攢的是生人的遭際,葬禮上的故事沉淀的則是逝者的一生。阿太的阿母走投無路時,神婆只是帶著她看葬禮,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前人故事的集合,自我的心靈秩序也在觀看中得以喚回和重塑。小說沒有去糾纏“命運”的存在,而是直接往前一步,追索與思考命運從何而來,又該如何去對待。在阿太跌宕了近百年的人生故事里,命運的讖言在場又不在場,她看透了一個時代,也看清了自己的命運,因生活的負重激起對命運的抗爭,由此籌劃種種生存的可能性,這是一種“于無常中向上而生”的生存智慧。阿太最終完滿地生下了自己的“命運”,她的人生故事也將在后輩的人生中繼續生長。
許哲煊:《命運》里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神明世俗化的書寫。神明并非神秘的命運掌控者,而是被賦予了人一樣的千姿百態,會愛美,會斗嘴,會在業務繁忙時兵荒馬亂,也會在被忘卻時依依惜別。神明被安放的空間也具有世俗化特征。神所在的廟宇并非高高在上的朝圣之地,而是溫馨的日常空間,人們與神明絮叨家常、召開集會、躲避災難……在極端政治環境中,神明更被藏在生活的縫隙里,例如被窩、骨灰盒,甚至廁中。這些空間隱蔽而瑣碎,凸顯神明在人們心中的親近地位:它作為信仰潛藏于個體內心,甚至沉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更進一步看,神明的來源也是世俗化的。閩南多數神明原為人所化。當個體為這人間承擔下大苦難,他就可以被奉為神。這背后體現的是對民間歷史經驗的傳承與紀念,同時也展現出一種集體觀念:個人的苦難被放到集體與歷史語境中,人在對抗命運的過程中漸趨神化,而這種神化由集體賦予。個體與集體、人與神成為共擔者。這也展現出一種特別的人神關系,神明既是人類的庇護者,也是同行者。阿太會對神明嘮叨生活瑣事,蔡也好會與神明談天斗嘴。人對著神既能祈禱,又能爭吵,神成為一個可以商量的對象。作者在后記中也將神稱為“朋友”。若說神明掌握人的命運,那么以神為友的人,其實也在與命運做朋友罷。或許人生的起伏其實是偶然性與主體性的結合碰撞,而神明以其超世的一面成為人們在偶然性面前的寄托與希望,又以入世的一面陪伴大家度過凡俗的人生。
林蓓珩:比起神明的陪伴,《命運》里“家”的建構尤為使我感動。它的內核是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美好感情。位于故事中心的三代人都過早地經歷了家庭的破碎。作為“留下來的人”,他們有著身世飄零的宿命感和對精神安定的本能渴求。不管是阿太想盡辦法受孕,還是太姨為了生個孩子送給姐姐而出嫁,都是千方百計地想組建完整的家,在血脈的賡續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在原有的希望落空之后,北來、西來、百花三個來自天南海北的無家可歸的孩子,卻使得家庭以另一種方式成立。這種不以血緣關系為前提的牢固牽絆,打破了傳統認知中“家”的定義。每個人都在需要和被需要的良性互動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即使條件艱苦,也能甘之如飴。如同阿太的人生哲學所言:“這世界最容易的活法,就是為別人而活。而如果那人恰好也是為你而活的,那日子過起來就和地瓜一樣甜了”。對生命脆弱的自我認知、執著生存的原始本能和在此基礎上蘇醒的責任感,構成了這個特殊家庭強大的向心力。時世的艱難反而使它愈加堅不可摧。此后的歲月里,直到人生盡頭,每個人都頻頻回首,望向他們共同建立起來的,無窮變數中的穩固支點。同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命運相比,家作為一股隱藏在文本之下的潛流,賦予了人們瞻望前景的勇氣和坦然面對命運的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