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中的“輕盈”

綠逸讀書會(huì)成立于2020年春,由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擔(dān)綱意大利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的魏怡副教授負(fù)責(zé)指導(dǎo),高如老師協(xié)助修改文稿,參與者是意大利語專業(yè)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本讀書會(huì)旨在利用語言優(yōu)勢,在中國推介、研究意大利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家及其作品,以便有更多讀者在閱讀中了解意大利的歷史傳統(tǒng)和當(dāng)今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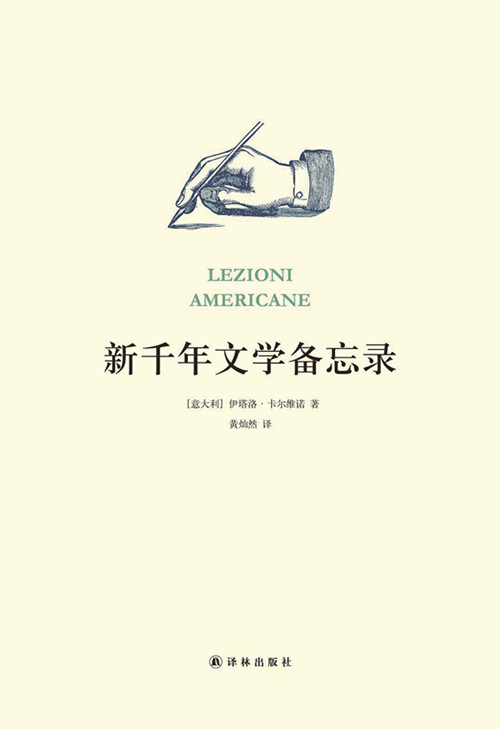
伊塔洛·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dāng)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20世紀(jì)世界文壇的大師,與博爾赫斯同享“作家們的作家”的美稱。他一生中創(chuàng)作了包括小說、論文、隨筆、文學(xué)評(píng)論、影評(píng)等在內(nèi)的眾多作品,而且被普遍認(rèn)為是20世紀(jì)意大利最富想象力的作家。《新千年文學(xué)備忘錄》(又稱《美國講稿》)創(chuàng)作于1985年,是卡爾維諾為赴美講學(xué)準(zhǔn)備的系列講稿,包括輕盈、迅捷、確切、可視性和繁復(fù)等五個(gè)章節(jié),代表著文學(xué)應(yīng)該具備的重要特征。卡爾維諾的這部遺作,如同以五個(gè)主題命名的“書架”,上面陳列著作家最為鐘愛的書籍。在講稿的創(chuàng)作當(dāng)中,作家針對(duì)每個(gè)主題進(jìn)行了天馬行空式的闡述,讀來妙趣橫生而又不無難度。作品以“輕盈”開篇,表明這是文學(xué)的第一要素。參加本次讀書會(huì)的同學(xué)正是針對(duì)該章節(jié)中引用的作家作品展開思考,分別從思想的輕盈、虛構(gòu)的輕盈、概念的輕盈、意象的輕盈以及將文學(xué)作為尋求輕盈和直面重負(fù)的方式等方面,對(duì)“輕盈”這一概念在文學(xué)實(shí)踐中的應(yīng)用進(jìn)行了深入的探討。
@周子涵:蝸牛痕與玻璃碎——?jiǎng)邮庯L(fēng)暴中的輕盈反擊
意大利詩人蒙塔萊的詩集《暴風(fēng)雨及其他》中出現(xiàn)的那些輕盈渺小的意象:蝸牛的痕跡、碎玻璃閃光的碎屑,還有粉餅與小鏡子,都是日常生活中看似無足輕重的事物,卻能抵御滔滔風(fēng)暴,并且顯現(xiàn)出非凡的光亮。詩人將詩篇置于世界末日的框架當(dāng)中,用黑暗與災(zāi)難的反襯,突出那些細(xì)微的閃閃發(fā)光的痕跡。它們就像詩人那些以零碎而微弱形式存在的思想,脆弱卻并不偶然。在他看來,人類的價(jià)值就來自于道德所具有的微小卻頑強(qiáng)的光芒。它們存在于苦難時(shí)堅(jiān)守的信仰與頑強(qiáng)的希望,個(gè)人的驕傲與謙卑以及對(duì)代表自身尊嚴(yán)的小小光亮的捍衛(wèi)當(dāng)中。正是這種“輕盈”,才使得人類在災(zāi)難的重壓下得以喘息,自身的光芒也不至于熄滅。這正是意象之輕盈和用文學(xué)之輕抵御生活之重的酣暢體現(xiàn)。
@金惠瑩:米蘭·昆德拉的“逃離”——在輕重躍遷中尋找存在
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沉疴,米蘭·昆德拉認(rèn)為:人類復(fù)雜的生存境遇要求小說以簡練為手法,減輕結(jié)構(gòu)重量,直達(dá)事物核心。如果反抗沉重是輕盈的內(nèi)在邏輯,那么“逃離”便是其外在表征,也是一份試圖重塑存在方式的趨于未知的賭注。昆德拉筆下的“逃離”充滿現(xiàn)實(shí)的意味:在行為上,它包含著深思熟慮的輕;在價(jià)值上,它是一種退無可退的重;在思想上,它又是從主人公將自我毀滅視作證明自我存在的孤注一擲,到在異質(zhì)文化對(duì)記憶的割裂中重構(gòu)身份認(rèn)同的掙扎,最終走向作者對(duì)現(xiàn)代性的反詰。如此的描述,使人類最殘酷的生存困境一覽無余。輕與重譜寫了存在的兩種真實(shí)形態(tài),“逃離”又在兩者之間構(gòu)建起虛無的紐帶。通過在不同境遇間的躍遷,人類得以窺見存在之可能。
@張羽揚(yáng):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以“輕盈”消解“沉重”
卡爾維諾稱盧克萊修的《物性論》是“關(guān)于詩歌的第一部偉大著作”。作品中,盧克萊修并未著重詮釋世界運(yùn)作的原理,而側(cè)重描繪遼闊世界中的微小粒子,并試圖勾勒虛空而細(xì)微的世界。在他的筆下,肉眼無法觀察到的粒子以輕盈的方式游移于穩(wěn)固的物質(zhì)世界與虛空世界之間:黑暗的房間里,一束照射進(jìn)屋的微光,會(huì)凸顯在空中翩翩起舞的塵粒的腳步;細(xì)密而肉眼難以觀察到的蛛網(wǎng),會(huì)在我們步入?yún)擦謺r(shí),輕輕裹住我們前行的身軀。卡爾維諾指出,盧克萊修一直在嘗試減輕物質(zhì)世界的沉重質(zhì)量,他對(duì)事物的認(rèn)識(shí)方式,也擴(kuò)及到了對(duì)可見世界諸方面的理解:人的存在應(yīng)是自由的。對(duì)盧克萊修而言,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伊壁鳩魯式人生是至高無上的,而輕盈的文學(xué)與詩歌,則能夠打破宗教禁欲主義的藩籬,讓人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認(rèn)識(shí)世界,進(jìn)而消解世俗生活的重量。
@張馨元:奧維德的《變形記》——詩人筆尖的輕舞
卡爾維諾在作品中征引了奧維德《變形記》中的柏修斯與美杜莎之戰(zhàn)。他將世界的沉重化為美杜莎令人石化的目光,柏修斯憑借鏡中反射的形象擊敗女妖則是英雄承擔(dān)現(xiàn)實(shí)的方式:“輕盈”于此,是脫身于現(xiàn)實(shí)桎梏的捷徑。再者,奧維德的輕盈還在其寫作筆法上得以體現(xiàn)。譬如,阿波羅對(duì)達(dá)芙涅的追求可謂是一次狩獵和強(qiáng)奪,但詩人卻有意弱化這一帶有強(qiáng)暴意味的追逐,更多借助于清風(fēng)、流水、枝葉等輕盈的意象,著墨于對(duì)少女形象的工筆細(xì)描,并以豐滿的想象力加以點(diǎn)染。原本靜止、凝滯的畫面,在他的筆下舞動(dòng)起來,故事的悲劇性色彩也因蓄滿輕盈之美的筆觸得以稀釋。想象力、創(chuàng)造性、巧妙的語言,使詩人筆下的各人物能夠輕盈且連貫地完成轉(zhuǎn)變。在他細(xì)膩并富有彈性的筆觸下,一切都變得輕盈而有序。
@周夢雪:卡瓦爾坎蒂與但丁的語言對(duì)比——意象的輕盈
在卡爾維諾看來,世世代代的文學(xué)都存在著兩種相互對(duì)立的傾向:一種將語言變?yōu)闆]有重量的東西,像云彩般漂浮;另一種則賦予語言重量和厚度,使之具體化。卡瓦爾坎蒂和但丁正是分別代表了這兩種文學(xué)傾向。卡瓦爾坎蒂的詩句輕盈、細(xì)微、永呈動(dòng)態(tài)。在一首十四行詩中,為體現(xiàn)情人之美,詩人并沒有一板一眼地刻畫情人的眉眼與妙俏身姿,而是在列舉了眾多美麗的事物(彪悍騎士、靜謐黎明、婉轉(zhuǎn)鳥語、紛飛白雪)后,突然筆鋒一轉(zhuǎn),稱世間萬物都不及情人之美,以此輕盈地勾勒出情人的嬌俏身姿。與他相比,詩人但丁更加看重賦予事物具體的形態(tài),哪怕是最為抽象的腦力活動(dòng),也要賦予其準(zhǔn)確的形態(tài)。比如在《神曲》當(dāng)中,但丁構(gòu)建了一個(gè)等級(jí)森嚴(yán)、有序可循的世界。即使客體本身重量輕微,他也會(huì)精準(zhǔn)地說明其分量之輕。
@譚鈺薇:不存在的堂吉訶德——以文學(xué)之輕載生活之重
卡爾維諾以“堂吉訶德舉矛戰(zhàn)風(fēng)車巨人”一幕作為形象之輕的例證。《堂吉訶德》這部作品的輕盈顯然不止于形象之輕,而更在于其近乎癡狂的想象以及理想浪漫主義的內(nèi)核。塞萬提斯以滑稽的筆觸書寫偉大的信仰精神,諷刺僵化的騎士教條,其筆下的堂吉訶德對(duì)騎士文學(xué)走火入魔后自命為模范騎士,就算碰得頭破血流也依舊滿腔熱忱地走南闖北。這就是一種舉重若輕。塞萬提斯一生潦倒,幾度因無妄之災(zāi)入獄,很難否認(rèn)小說的啼笑皆非中其實(shí)也藏著作者的一份執(zhí)著。卡爾維諾也以同樣的輕盈在《不存在的騎士》中寫下阿季盧爾福的故事,讓文學(xué)之輕跨越世紀(jì),從理想之贊再到存在之辯,承載起生活之重。無論是那套破爛的拼湊盔甲,還是完美的銀白盔甲,都體現(xiàn)出文學(xué)如何借助輕盈之術(shù)消解生活的沉重。我們很難在現(xiàn)實(shí)中找到文學(xué)騎士的蹤影,但生活的答案也許恰存在于生活之外。
@李李冰清:《格列佛游記》——靈魂之“輕盈”與科學(xué)之“沉重”
科學(xué)無疑是18世紀(jì)最重要的思潮:牛頓力學(xué)問世不久,啟蒙群星層出疊現(xiàn),人類樂觀空前未有。在中世紀(jì)教會(huì)統(tǒng)治下沉睡千年的古典文化重現(xiàn)世間,卻缺少了輕盈、審慎與克制。從它灰暗的陰影中,我們依稀能預(yù)感到20世紀(jì)的沉重夢魘。斯威夫特作為時(shí)代的先覺者,旁觀彼時(shí)的科學(xué)潮流,最早對(duì)啟蒙籌劃提出了質(zhì)疑。書中“飛島”憑借磁力懸浮空中,住民卻終日沉湎覃思,對(duì)其他一切漠不關(guān)心,行事怪誕,淪為只顧仰頭觀察星際的科學(xué)怪人,丟失了自然人應(yīng)有的靈魂人格。盧梭有言:“科學(xué)愈臻完美,道德愈發(fā)腐敗。”啟蒙本是讓我們免受盲目支配,但過度理性反而異化和壓抑了人類本身。飛島上的專家和政客們癡迷于抽象科學(xué),罔顧人世生活,以“沉重”的科學(xué)將自身鐐銬,失去了生活與靈魂的“輕盈”。
@劉芳芮:伏爾泰的想象力——從沉重現(xiàn)實(shí)到失重太空的輕盈一躍
借助想象力,伏爾泰為沉重的現(xiàn)實(shí)披上一件科幻的外衣,又借助令人啼笑皆非的情節(jié)去映射現(xiàn)實(shí)的荒誕。作者輕盈一躍跳出現(xiàn)實(shí),進(jìn)入浩瀚無垠的太空,跟隨天狼星巨人尋求解脫。同時(shí),現(xiàn)實(shí)也從未被遺忘。在新的宇宙中,作者借米克羅梅加斯之口傾訴著現(xiàn)實(shí)的沉重。相比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手法,想象力的加入使得故事更加輕盈,也更有利于讀者的理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學(xué)賦予了巨人星際旅行的可能,也為想象力的輕盈加上可靠的限制,使故事既能在星空翱翔,又不忘腳踏實(shí)地,從而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手法,虛構(gòu)為故事加上點(diǎn)睛之筆,賦予故事更輕盈的骨骼,也為情節(ji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它最終擺脫現(xiàn)實(shí)的枷鎖。這樣,既不過分沉重,也不欠缺思想內(nèi)涵,從而彰顯文學(xué)的魅力。
@李曉婉:以輕盈的月光,聊慰永恒的沉重
卡爾維諾對(duì)萊奧帕爾迪的評(píng)價(jià)是:“他的奇跡在于使語言變得輕如月光”。在萊奧帕爾迪的詩歌中,月亮的存在并不張揚(yáng)耀眼,而是“靜謐”而“皎潔”,以一種懸浮、飄忽的姿態(tài)烘托詩歌的底色。月光如繚繞的云霧籠罩著漆黑的夜色,也撫慰著詩人難以排解的愁緒。常年疾病纏身不斷消磨詩人的意志,落后保守的家鄉(xiāng)與家庭又如囚室般禁錮詩人的自由,黑壓壓的現(xiàn)實(shí)更使詩人內(nèi)心始終彌漫著濃稠的悲傷與憂郁,甚至試圖以自殺來終結(jié)痛苦。因此,他希望從像月光般輕盈的對(duì)青春歲月回憶中汲取勇氣,渴望月光帶他脫離病痛,獲得自由。然而,月光并不能改變?nèi)缫股銤庵氐默F(xiàn)實(shí),夜晚的主宰仍將是永恒無盡的黑暗。詩人寫道:“往事的回憶固然令人悲傷,而痛苦卻地久天長!”
@潘晨:無法消解的沉重與帶來希望的輕盈
《鐵桶騎士》的創(chuàng)作背景是一戰(zhàn)后奧地利的寒冬。堂吉訶德尚有瘦馬洛西南特滿足他對(duì)于英雄的想象,而生活在20世紀(jì)的主人公卻只能以空煤桶為坐騎。御“桶”飛行的虛構(gòu)故事具有魔幻般的色彩,飛行的輕盈也化解了流浪的疲憊。騎士懸浮于殘酷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之上,讀者也仿佛得到片刻喘息。卡爾維諾以鐵桶騎士的旅途承接薩滿教的靈魂飛翔,串聯(lián)早期民間傳說里女巫的魔力,反映了文學(xué)如何面對(duì)生活的重負(fù)。然而,現(xiàn)代文明給“秘索思”留下的空間愈發(fā)狹窄,人類滿懷期望試圖離開沉重現(xiàn)實(shí),但所及之處并不能滿足自己的想象。盡管如此,卡爾維諾或許仍懷有善意與期待。當(dāng)他筆下的人物馬可瓦爾多走出蝸居多年的地下室時(shí),被消費(fèi)社會(huì)和生活重負(fù)折磨的心靈,仍會(huì)被城市的微風(fēng)觸動(dòng)。這大概就是現(xiàn)代人在現(xiàn)實(shí)世界追尋輕盈的模樣。
(本文發(fā)于中國作家網(wǎng)與《文藝報(bào)》合辦“文學(xué)觀瀾”專刊2021年10月25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