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和池魚》:錦鱗繡羽,水陸藏心

本期讀書集結“和光”四位成員,探討海外實力派作家張惠雯的最新小說集《飛鳥和池魚》。不同于“在他鄉”主題的《在南方》,該作品集將視線收歸于故鄉或舊地,以多種身份的“我”作為敘述主體,撥開往昔的帷幕,勾勒出目之所及、心之所念的舊事故友。記憶和現實穿梭,幻想與真相纏繞,互為因果,也互為深淵及救贖。故事里的人,應和著里爾克詩歌的傾訴:“我的感官像鳥一樣,我用它們從橡樹高攀到多風的云天,而我的感覺仿佛腳踩魚脊,沉入了池塘里被竊取的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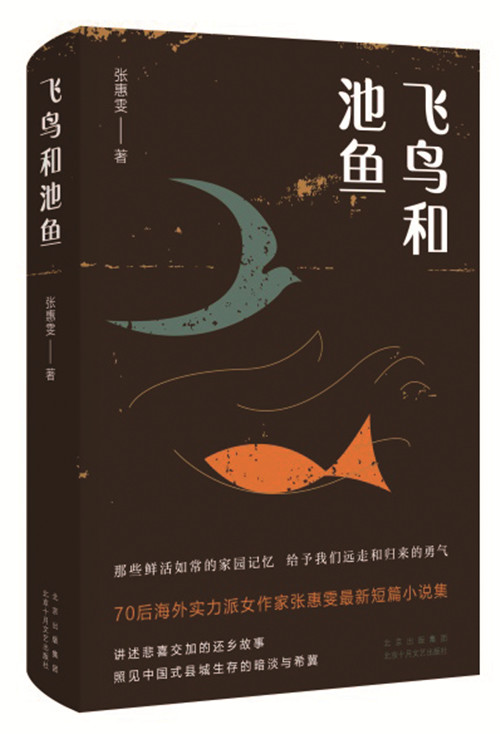
@趙鼎:渡“池魚”為“飛鳥”:愛的和解與救贖
在小說集中,張惠雯將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及其內在維度的本質上,以探求更具普遍性意義的人性問題,盡管她也描繪了人性中鄙薄丑陋的一面,但總體而言,她始終保持著真、善、美的倫理價值追求。
在作者筆下,“飛鳥”與“池魚”的意象頗具象征性意蘊,“我”以“歸鄉者”的身份凝望審視著故土小城的種種困厄,呈現出由“飛鳥”——“池魚”——“飛鳥”的轉化過程:作為個體的“飛鳥”陷入某種道德倫理困境而滯化為“池魚”,幾經掙扎后最終憑借人性的愛與善擺脫囹圄,重歸自由的“飛鳥”。事實上,小說里部分主人公始終未能徹底掙脫現實生活的泥淖,他們的蛻變源自思想的轉換和心靈的超脫。正如羅蘭在探究文學作品中“鳥”的意象時曾指出,“小鳥代表著不朽的靈魂,而不是身體,鳥代表著精神世界,而不是世俗。這種觀點非常普遍。”張惠雯的小說也是如此,所謂“飛鳥”并不單指身體層面的解放與逃離世俗困擾后的自由,而更傾向于強調歷經滄桑后,個體從外在的矛盾與沖突轉向對內在空間的探索與叩問,進而達成的一種釋然豁達的心理狀態與精神世界的主體性超越,即個體與自我、他者、生活乃至命運的和解。因此,從“池魚”化作“飛鳥”之過程,就是一次個體對自由和諧心境的曲折性探求,并最終以“愛”完成的精神領域補償性言說。
在其同名短篇《飛鳥和池魚》中,愛與孝成為“我”折翼的主因。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身為人子的責任義務和母子間的親情羈絆將原本生活在“更好更廣闊的地方”的“我”逐回故鄉小城。母親精神的異常與前景的迷惘使“我”的生活始終浸染著一絲憂郁灰暗的色彩。看到池中游魚,母親歡欣雀躍仿若孩童,而“我”卻“寧可池子永遠是空的”。常言道,“久病床前無孝子”,在疾病生死面前,人性的矛盾與掙扎往往會暴露無遺。盡管“我”未曾放棄,但長期的生活壓力和精神折磨早已令“我”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母親已從昔日的庇蔭凋敝為難言負擔與壓力之源,將“我”徹底縛為一尾難見天日的“池魚”。然而,在小說的結尾,作者還是為這不知期限的困局瀉下一線光亮:“我”于一片“巨大、黑暗的安寧”中焦慮地尋找著母親,擔心她真的會如鳥兒一樣飛走,當她安然無恙地出現在陽臺時,“我感到心臟重新在我的胸腔中平穩地跳動”,在“我”抓住母親的那一刻,“我和她又連在了一起,無論是身體還是命運……這比什么都好”。在那一瞬間,久違的安逸與輕松得以復歸,壓抑扭曲的母子關系得到緩和修繕,親情最終平復并超越了平日的幽怨和苦難,渡“我”與生活諒解。
在其他幾篇小說中,讀者同樣可以窺見與之相似的轉換軌跡:《對峙》中原本是警察的“我”因沖動殺人而面臨法律制裁,輪番心理博弈中,道德理智終占上風,遂選擇死亡作為贖罪和解脫;《昨天》《良夜》《天使》的主人公則是通過邂逅記憶中的幸福與憧憬,依據善與美完成了對當下裂隙或創傷的療愈;《漣漪》中的教授陷入情愛和責任的兩難抉擇,在家庭與生命“永遠不可能交融”的孤獨中,曾經的愛戀成為他余生的溫暖與慰藉;《尋找少紅》《臨淵》皆以充盈著愛意的美好想象來彌補現實的缺憾,賦予人們跨越深淵、繼續生活的勇氣信念。
當人們墜入晦暗淵藪,唯有愛可成為救贖,無論是在現實中轉瞬即逝還是只留存于幻想虛構之中,哪怕只有一瞬的光明與溫暖,也足以點亮一個寂寞迷惘的靈魂,將其從“池魚”再次拯救為“飛鳥”。于失落絕望中探求愛意與希望、在倫理困境中堅守真善美的追求、為躊躇彷徨的心靈指引迷津,這正是張惠雯小說中人文關懷精神的內涵之所在。
@于明玉:庸常者·沉淪者·救贖者
當作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展開敘述,人群的微妙區分便隱藏著寫作者的主觀介入。小說通過持續性回憶建構出周邊環境,在平鋪直敘中顯現不同生存空間的本真狀態。因其獨特的生活體驗和自覺的舊日重審,親人、故友、愛人、陌路人,都難以逃開作者對其是否淪為平庸的評判。“庸常”作為生活的中軸,任由低賤與崇高上下翻騰,而邊緣模糊的三類人就此浮現。他們圍繞“我”再現,粗略地涵蓋了生存的每一姿態與側面,也揭示了文學所能折射出的無限現實空間。
圍繞“重返故土”這一過程,通過認知偏差體現了敘述者的心理落差,這不僅針對環境,更是直接指向“老家的人”。人物的無知和淺薄往往具有不自知的屬性,因此極易誘發“我”情緒的放大與復雜化,進而從塵土飛揚的書寫中流露出刺痛與貶損的意味。“癡愚”“勢利”“衰頹”的形容與“憐憫”“厭煩”“悲哀”的心境相呼應,呈現出一抹面對故土內心矛盾的情感色彩。“我”與爺爺奶奶的對峙(《尋找少紅》)、與史濤關于結婚成家的辯論(《昨天》),主人公的持續性發問省思了鄉土文明和人性倫理,在純粹道德感之外又留存著從時代濁流中解救個體,實現精神獨立自由的意圖。透過“外來”投射的目光,小縣城里繼承陋習、流于世俗的人們逐漸扁平、黯淡,單向度地對應著鴿灰色世界的每一條棱,最終淪為活生生的“庸常”。
“沉淪者”的出現或許是作者對現實進行突圍的一次嘗試,即一口氣下潛到生命最晦暗處,見證著無法挽救的下墜與痛苦的徘徊。他們從社會的邊緣緩步攀爬,向圍觀者顯露出羸弱又蒼老的面目。這種尖銳的揭示在敘事中卻往往是以“理應如此”與“不期而遇”的形態出現,肉體與精神的悲慘處境被日常化,縮短了讀者與悲劇的距離。而在重復體驗個體苦痛的異質世界中,“我”從悲劇頂點回落,劫后余生的釋放感也順其自然地成為了“我”與平庸和解的推手。
由于“我”在小說中的身份多樣性,“俯視”的敘述立場可以轉瞬更變為“仰視”。一如太陽因高懸刺目而于眼中輪廓模糊,來自于心理波谷的傾訴也呈現出一片因情緒外露而失去清明的迷蒙。當“我”撩開精神衰敗的垂幕,重見澄徹往昔,理性的言語被纏綿裹挾,尊嚴的防線為軟弱陡然侵入,新的情感體驗從帶有“救贖”意味的人群中矗立起來。
在作品集中,“救贖者”出現于“庸常者”與“沉淪者”之中,將我從蒼白的生活中解圍。需要注意的是,人總是在極為微妙的處境中與美好短暫相觸,“救贖”一詞本身就蘊含著被救贖者的感性言說,尤其是過往與當下兩條時間線交叉行進,真實情景的記錄與主觀感受的虛構相互依附,而內心獨白又使得現實與想象的混淆擁有了合理的存在方式,為形象的失真創造機會,換言之,這類形象的背后隱藏著扭轉視角后就淪為平庸的可能。
但作者竭力將這美好凝固。她所使用的技巧就是塑造“片刻”。
人與人的相逢即是命運線的交錯,在短暫擁合后迅速背道而馳。當模糊陳舊的碎片記憶成為描摹獨立個體的惟一素材,針對確定對象的寫作欲望又抹殺了全盤虛構與中立敘事的嘗試,此時原本屬于“人”的片面便過渡為文本中情景事件的瞬間。《昨天》中的“她”被“我”封存在有所指向的“初冬早晨”;在《良夜》里,屬于“小安”的善意僅于兩個夜晚撲朔浮現,在當下與記憶共同的折射下泛出一片夢幻的瑰色,二者都在推向過去的書寫中凝結為主人公霎時的人生高亮;《漣漪》與《天使》則竭力放縱感覺的震顫與急轉,“一個下午或幾個小時”“極其封閉、狹小、溫暖的空間”共同為扎根靈與肉的重逢提供了合適的溫床。一切敘述刻意地繞過歲月與世俗,有關過去的鋪墊與對未來的規避在此時此刻迸發出奮不顧身的勇氣。追逐幻影的原始沖動與“可望不可及”的悲觀情緒反復推拉,使得“他”或“她”的完美側面在極端明亮中消弭了扁平的缺憾。當最終其“存在”于特定的節點猝然定格,便強行還原了情感初次覺醒時的朦朧往昔。被極力壓縮的時間與空間共同營造出遠超當下的對象,恰到好處地填補了主人公靈魂與理想的裂縫,而這也許就是其僅在瞬間存在的真正原因。
@高瑞晗:天使在人間
小說集很多篇都有“天使”的存在,它是美好女性的象征。張惠雯筆下“天使”有三類,她們大多是交織著幻想與現實的成熟少婦,也有存在于父親記憶中的女兒和奮不顧身保護孩子的母親。她們美麗、善良、溫柔,但并非超塵脫俗,而是生長于真實的生活,有些沾染了世俗和歲月的痕跡,有些富有母性的溫情,有些已成為美好的定格。
《天使》中,她曾點燃過少年的“我”,又讓死滅的“我”再度燃燒。多年后,她已經沒有那種讓人心驚的美麗了,失去了曾屬于少女的“驚心動魄”的美,但依然有天使一般、屬于女性的特質——溫柔、成熟、風情萬種。與此相似的是《漣漪》中的情人,她溫暖而羞怯,是光或夢想,誘惑穩態生活模式中的“我”,使我甘愿背離信條。《昨天》里的“她”是“我”記憶中的“天使”,曾有一個初冬的早晨,我們的心靈曾經向彼此敞開,重遇時“她”已沾染歲月的痕跡成為走向衰老的平庸少婦,眼神里的熱烈天真被倦怠取代,“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
面對死亡、瑟索、污穢的生活,她們是美好的幻影。幻影來源于并歸屬于過去,交織了幻想,短暫地出現于當下,但不會長久駐留。在支離破碎的世俗生活中,她們不露痕跡地帶來稍縱即逝的深情。她們“是別的維度里的別的生活……在此處,我們似乎僅僅有權決定愛,卻無權決定生活”。
另外兩類“天使”,她們在小說集中所占篇幅較短,形象卻足夠生動。對于《臨淵》中的老人,去世的女兒就是他的“天使”,老人以女兒為傲,逢人便聊起她,將她成長的點滴整理保存并視若珍寶。老人主動制造一次次談話,令女兒從人間復活,擦亮命運深淵。《對峙》里的母親是小男孩的“天使”。她在這場漫長的對峙中不卑不亢,盡己所能地保護孩子,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展現出柔(外表)與強(內心)的對峙。
@張林:兩條時間線的對位寫作
對位法是音樂寫作中使兩條或多條獨立旋律同時發聲并相互融洽的創作方法,在樂曲中形成復調效果。在作品集里,張惠雯將過去與現在兩條時間線“對位”,兩個時空交雜并置,互相滲透,交響出復雜而豐富的情緒體驗。
“過去”由“現在”進入,切入點皆是主人公人生中“節外生枝”的一次“停頓”,是游離于主流生活之外的部分(如因母病父亡短暫歸鄉、因事而故地重游、無所事事的垂釣等),“一切都停頓在這個點,一切陷入困局……全都卡在這里”。但這停頓卻極具“日常性”,可以是一次相聚(《良夜》《昨天》《天使》)、參觀(《漣漪》)、出游(《飛鳥和池魚》)、垂釣(《臨淵》)、散步(《街頭小景》)、遠行(《尋找少紅》)。過去經由“日常”的入口漸次降臨。
在日常場景中,作者以細膩入微的筆觸尋覓著現在與過去共同的載體。它可以是一個特殊的時間段,如傍晚,在《飛鳥和池魚》《昨天》等篇章里,作者將現實中“傍晚”的嘈雜混亂與過去的寧靜美好比對,勾連出懷念之情的同時也指向了記憶的虛幻性質。它也可以是某個地點,如《天使》里的老屋,舊物依然,但今時和往日感受迥然相異,而更多的情形是時間使地點變化,甚至面目全非,只殘留著一些零散的昨日證據以供辨認,如“名字”,《漣漪》中,“街道的樣子變了,但名字依舊,那些字就像一根根突然擦亮的火柴,照亮了我心里連接往昔的幽暗通道”。在《關于南京的回憶》內,盡管“我”再沒回到過那座城市,但“聽到這城市的名字,那些鮮明的東西就突然蘇醒……”再如“樹”,《街頭小景》提到“這些樹自我中學時候就在……它們讓我想起過去的光陰”。有些媒介則是更具體的,《良夜》老友聚會時,“我”和小安的座位排序與多年前一樣(“和那晚一樣,我坐的位置和小安之間隔著大超。”);《對峙》中那孩子的呼吸聲讓“我”想起兒子小時候;《飛鳥和池魚》里“我”想起那封保存多年的舊信。當今與昔在某個細節上重逢,過去也就在現實的身體里轟然而至。
“對位”作用下,過去與現在兩條時間線獨立存在卻也彼此包納對方。從“講述者”角度(書中故事皆為第一人稱敘事,講述者即主角)來看,體現為一種“干擾”產生的“噪聲”。一方面是現在對過去的干擾,“這一路沒有半點我熟悉的東西,它不僅無法和我往昔的印象有絲毫的交集、重疊,還形成一種痛苦的干擾”,當下的時間里,承載記憶的載體因變得陌生而對回憶造成間離,而當現實環境被弱化,過去將再次照臨,即當“我”和“她”走在因感應燈壞掉而漆黑一片的樓道里時,“那個初冬早晨的感覺又會在心里全然蘇醒過來……連氣味都不曾改變”(《昨天》);另一方面也是過去對現在的擾亂,在《臨淵》中,“我”講述回憶時,兩次捏住煙盒卻又松開,反映了心緒之混亂,而在《天使》里舊人重逢也擾亂了“我”平靜的生活,《關于南京的回憶》講述了發生在南京的舊事,這舊事塑造了現實中“我”對男性和那座城市的看法。
整部作品集常出現的一個意象似乎可以為這種“噪聲”作一個注腳,即“煙霧”。在“少紅”所在的村莊中,“一切都蒙在一層又冷又潮的霧氣里”(《尋找少紅》),《昨天》中“我”記憶深刻的那個早晨“浮著一層奶白色的薄霧”,《漣漪》里故地重游那一日的末尾,“燈光和暮色交織成一團半灰半藍的煙霧”,《臨淵》那片釣魚的河面上,有“要散不散的霧”,在《天使》里,作者提到了“時光的霧靄”。當過去和現在同時奏響,于文字間和諧交織,一種霧氣般輕柔又沉重的閱讀感受便翩然降臨了。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5月21日第7版)
- 張惠雯:“天使”在人間[2021-05-21]
- 張惠雯小說集《飛鳥和池魚》:臨淵寫作[2021-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