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園:關于劉醒龍的四個思考片段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 蔡家園 2021年04月26日07:22

劉醒龍(1956~),湖北黃岡人。1984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協(xié)。現(xiàn)為湖北省文聯(lián)主席,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說《鳳凰琴》《秋風醉了》,長篇小說《圣天門口》(三卷)、《蟠虺》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散文獎等。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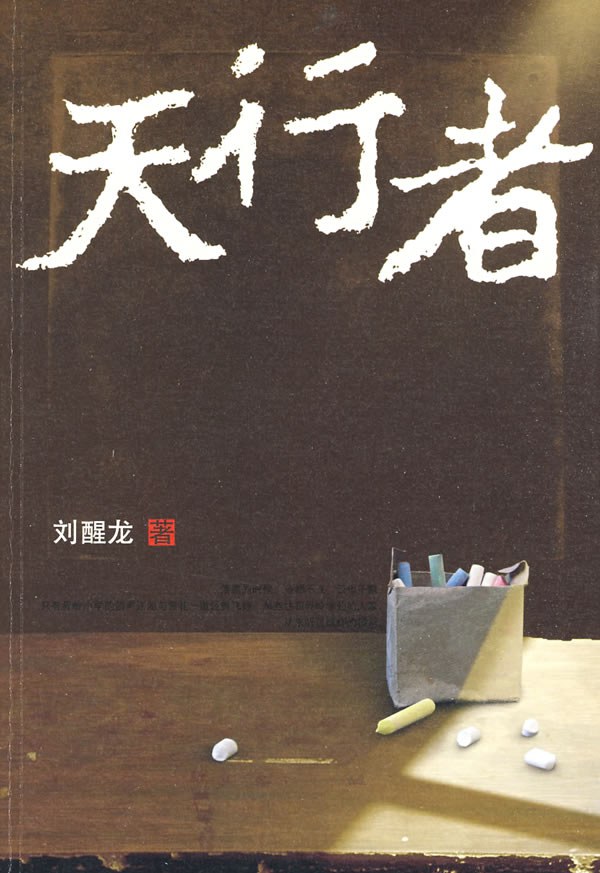
《天行者》
一
如果拿劉醒龍和“先鋒”一起說事兒,可能不少人會覺得似在意料之外。
《劉醒龍文學回憶錄》中講了一個故事:“我不善飲,更不多飲,卻是武漢文學圈公認的酒桌上的開先河者。別人喝啤酒可以喝上半箱一箱時,我在一旁獨自飲著干白葡萄酒;好不容易讓別人也開始愛上干白葡萄酒時,我又一個人喝上了干紅葡萄酒;等到別人也將干紅葡萄酒往天上吹,我又轉(zhuǎn)頭去喝那只需兩杯下肚準保額頭出汗的真正醬香型白酒……”
劉醒龍其實并不好酒,在文學自傳的開篇就拿酒來說事兒,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一個追新者,對新鮮事物保有敏感,引領著“酒桌上”的風氣;“我”是一個執(zhí)著者,始終鐘情于“酒”;“我”是一個自律者,頗有拿捏分寸的自信;“我”也是一個孤獨者,因為率先嘗試,所以總是“在一旁”“一個人”,寂寞卻不乏驕傲……
這個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酒事”,實乃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它既關乎著劉醒龍的“心結”,也提出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面對那些懷有巨大理想、堅定不移的寫作者,研究者、評論者在言之鑿鑿時,真的就明了他們的苦心孤詣和真正價值嗎?優(yōu)秀的作家從來都需要拉開時空距離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和全面。
從1984年公開發(fā)表第一部小說算起,與劉醒龍37年的文學歷程相伴隨的評論早已構成一部劉醒龍闡釋史。尋根小說、新鄉(xiāng)土小說、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新歷史小說與“重塑傳統(tǒng)”無疑是其中的關鍵詞。作家就是被置于這樣的一個個“灰闌”中解讀而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可是,這就是真實的劉醒龍嗎?
“大別山之謎”系列被視為尋根小說,作家在回望中國傳統(tǒng)的同時表現(xiàn)出的超越渴望是不是被忽略了?當我們認同《村支書》《鳳凰琴》植根鄉(xiāng)土現(xiàn)實、還原生活本相的姿態(tài)時,那字里行間煥發(fā)出的前所未有的、近乎神圣的道德理想激情是不是被曲解了?人們贊揚《分享艱難》直面現(xiàn)實問題的敏銳,是否留意到了作家深沉而痛苦的憂思與憐憫呢?《圣天門口》解構了宏大敘事和革命倫理,可是它在神性與人性的雙重視野中重構了新的倫理價值是否受到了重視?《蟠虺》《黃岡密卷》當然是“重塑傳統(tǒng)”,可是由地方文化破譯并建構中國人的精神密碼算不算獨辟蹊徑?假如我們認同先鋒是一種不循常規(guī)的理念和勇于“破圈”的姿態(tài),將劉醒龍從既有文學思潮框架中解放出來置于更加開放的美學視野中考量,他是否也可以被視作一種“先鋒”?
二
2011年劉醒龍在華中師范大學曾做過一場題為《啟蒙是一輩子的事情》的文學演講。作家結合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和重要作品,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自己的文學觀,主要包括:“一個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據(jù),也是文學情懷的根源”,作家除了天賦之外還有無限的“天職”,文學要有生命的理想,“一個民族的文學必須表現(xiàn)這個民族的靈魂力量”,經(jīng)典文學的血統(tǒng)是高貴的,通過對現(xiàn)實的多重質(zhì)疑來表達自己的理想,“生命之上,詩意漫天”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內(nèi)容雖然都被歸在“啟蒙”的題目之下,其實卻迥異于學界通常所談論的“啟蒙”。在另一篇文章中,作家有更明晰的表述:“人人心里都有一個‘圣’的角落,這樣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啟蒙。”劉醒龍將“啟蒙”思想之根扎在中國傳統(tǒng)的土壤里:“潛意識里的道德體系規(guī)范著我的寫作行為,而這個道德體系還是來自鄉(xiāng)村。”他還有許多類似的宣言式表述,隱約透露出其自我正名意識。然而3年后,在該校召開的劉醒龍文學創(chuàng)作30年研討會上,依然有不少評論家將其創(chuàng)作納入啟蒙話語體系,強調(diào)立足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品格,圍繞文化性、批判性、隱喻性來論證他續(xù)接了啟蒙精神。檢索關于劉醒龍的研究論文,也大多是在這樣的文化立場和美學視野之下的肯定或批評。誠然,這樣的闡釋在很多時候是有效的,但有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人們對一個獨特而豐贍的作家的全面認知。
新時期以來,以啟蒙主義為標準確立的一套美學原則在極大地推動著當代文學發(fā)展的同時,也“規(guī)范”著文學的發(fā)展。毫無疑問,劉醒龍從寫作之初也選擇了啟蒙立場,表現(xiàn)為對人的人格、價值、尊嚴的關注。但是,對“啟蒙”劉醒龍顯然還有著自己的“僭越”了既有規(guī)范的理解。所以,從《村支書》到《分享艱難》,其作品不時遭到批評界的討論和批評。當作家的文學實踐更加豐富、思想根基更加堅實、藝術技巧更為嫻熟之后,他開始直接發(fā)聲,通過闡釋自己的價值觀和美學觀來爭取話語權。其“策略”之一就是將概念內(nèi)涵進行置換,所以此“啟蒙”并非彼啟蒙。綜觀其創(chuàng)作,作家的思想來源較為復雜:啟蒙主義只是其一,傳統(tǒng)儒家思想堪稱底色,兼有道家思想,還受到楚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影響。他的基本姿態(tài)是建構性的,但也并沒有放棄反思與批判。他始終保有對人的憐憫與關懷,并有著更為寬廣的視野和別樣的情懷。
與作家的“啟蒙”觀點相關聯(lián)的還有“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就學理性而言,劉醒龍似乎并沒有將這個概念說透徹。但是,他旗幟鮮明地倡導一種肯定性的正面價值觀,呈現(xiàn)出強烈的道德化色彩。他也許是在提示文學史家,他的現(xiàn)實主義寫作與“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根本就是貌合神離。通過不斷地演講、對話、發(fā)表創(chuàng)作談等方式,這些年來劉醒龍不斷地闡釋著自己的文學觀。也許希望藉此為自己的寫作正名,為多樣性文學存在的“合法性”正名。
三
“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必須以筆為家,面對著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營造那筆尖大小的精神家園,為那一個個無家可歸的靈魂開拓出一片棲息地,提供一雙安撫的手。”劉醒龍一直強調(diào)作家的社會責任對社會進步的正向作用。在他看來,“在這個社會變革時代,我們應承擔起責任,通過寫作承擔責任和表現(xiàn)這種責任”,文學必須是“為人生”的,讓人“變好”“變善”。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承載著強烈的道德意識,甚而就是理想道德的“化身”。
在長篇小說處女作《威風凜凜》中,盡管“惡”踐踏了知識、美好和人的尊嚴,但是趙老師身上的知識與文明為西河鎮(zhèn)的“威風”文化注入了新內(nèi)涵,彰顯了道德的力量。《生命是勞動與仁慈》認為生命的意義在勞動中凸顯,勞動是一種道德力量,能夠拯救潰敗的社會,救贖墮落的靈魂;生命同時也是仁慈的,可以挽救物欲時代異化的人際關系。陳東風式的勞動創(chuàng)造人、創(chuàng)造道德并自我完善的理念,雖然帶有烏托邦性質(zhì),但其鮮明的道德化立場仍然不失感染力。《痛失》痛心的是一個基層優(yōu)秀干部喪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良知,批判了物欲時代人格和靈魂的墮落。
如果說劉醒龍早期的這些長篇小說在價值層面偏重于“破”,那么以《圣天門口》為標志,“立”的意圖更加顯豁。他說:“寫這部小說時,我懷有一種重建中國人的夢想的夢想。”他立志要寫出人倫的高貴。這部具有寓言氣質(zhì)的史詩性作品反思中國暴力革命和權力話語,在消解歷史的同時也重構了歷史,確立了一種終極精神價值立場:在政治倫理之外,不僅有民間倫理,而且還有一種精神倫理——以梅外婆、梅外公、雪檸等人為代表的非暴力救世精神。它呼喚和平,倡導寬容與博愛,具有超越性。《天行者》則是一曲對于山村民辦教師的深情頌歌,高舉著道德理想主義的旗幟,將鄉(xiāng)村知識分子的無私奉獻精神和自我燃燒的理想激情張揚到了極致。《蟠虺》將知識分子視為國之重器,以青銅器隱喻詩性正義、君子之風和守誠求真精神。曾本之堪稱傳統(tǒng)人格理想的化身,他在對真的堅守、對良心的忠誠和對欲望的抵抗中,實現(xiàn)了人生超越。《黃岡密卷》中的老十哥既有堅定“黨性”,又胸懷“大愛”,無比珍視“人情”,他身上煥發(fā)出強大的道德感召力,是一個堪稱民族脊梁的“父親”形象。
所有偉大作家都具備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在洞悉了時代的真相和人性的秘密之后,仍然能對這個世界抱有信心,對人懷有憐憫、慈悲與愛。這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劉醒龍始終堅信:“惟有愛是偉大的永恒。它關懷一切,撫摸一切,化解一切。只要有愛,所有應該改變的,最終肯定會改變。”因此,他的道德理想主義構筑在深廣的人道主義基石之上。
傳統(tǒng)道德力量作為一種面向傳統(tǒng)的價值取向,寄望它來感化人心與解決當代社會問題只能是一種理想。劉醒龍不可能不明了這一點,但是他依然篤信:“文學畢竟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文學一定要成為世界的良心。”也許是身為黃岡人的“一根筋”使然,這種“執(zhí)念”像一束光,至少能照亮人性風景之一隅。
四
有人說,劉醒龍是最“中國”的作家之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于他而言是融化在了骨子里。
梁漱溟曾說,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以道德代替了宗教。劉醒龍正是在倫理層面實現(xiàn)了對“中國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精準把握。“道德至上”不僅是他的主體人格追求,也是其創(chuàng)作的價值基點:“敦厚、和善、友愛、憐憫等,這類被自身過度消耗了的營養(yǎng),而我正是將它們作為藝術的靈魂。”劉醒龍的“道德”,其實已非我們?nèi)粘I钪兴f的道德規(guī)范和倫理準則,而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普適性的終極價值。
在他的小說世界中,仁慈、寬容與愛等道德精神像珍珠一樣熠熠閃光。他以仁愛與善良來消除誤解和仇恨,用寬容、悲憫來化解矛盾沖突,以基于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化的重義輕利的道德觀念和人倫溫情來對抗、消解城市化進程中顯露的某些欲望和邪惡。他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承載著傳統(tǒng)道德的人物形象,寄望以他們的人格力量來改良弊端、拯救人性沉淪。他說:“我相信善能包容惡、并改造惡,這才是終極的大善境界。”“大善”其實就是大愛,亦即“仁”,指向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
劉醒龍固然是一個勇于“出圈”的“先鋒”,但同時也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然而這種立場,卻并不影響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抵達現(xiàn)代性。他曾說:“文學中的中國傳統(tǒng)一直是我所看重的,我始終沒有停止過這方面的探索。”無論時代如何變幻,他始終堅定地走在自己認定的路途上。近年他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又有新探索,譬如植根于文化傳統(tǒng)的“青銅人格”“黃岡人格”中所包蘊的時代新內(nèi)涵;將中國古典小說的野史雜傳傳統(tǒng)與西方現(xiàn)代小說技巧融合,并借助文體互滲將“小說”引向“大雜文”等,這些都為當代文學有效實行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提供了鏡鑒。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