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講故事的人”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季進 王敏 2021年02月26日08:13

麥家(1964~),浙江富陽人。1986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2005年加入中國作協,曾任浙江省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等。曾獲第六屆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小說家榮譽、第13屆上海國際電視節最佳編劇獎等。《暗算》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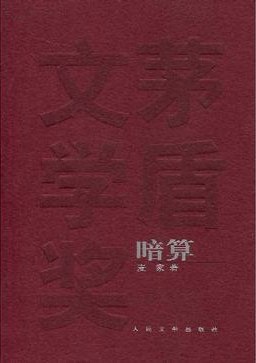
麥家《暗算》書影
麥家筆下的主人公在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可謂獨樹一幟。這些神秘的天才因身份特殊而游離于世俗生活的邊緣,身負神圣使命和濟世情懷踽踽而行,頗有些“獨行俠”的意味。《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里的安在天、《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莫不如此。某種意義上講,麥家的小說世界確有幾分江湖氣息,相似的超現實場域、超人式的英雄人物、驚險跌宕的生死對決以及嚴肅而悲情的游戲之道等,作者以“說書人”的偽裝復活了一個詭秘奇譎的傳奇世界,塑造了一個個身懷絕技的英雄/俠士形象。這或許也是麥家留給讀者的印象:特立獨行,劍走偏鋒。
用文字詮釋孤獨
真正的寫作從來都是孤獨的。對麥家而言,這種孤獨似乎格外深徹。2008年《暗算》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在斬獲榮譽的同時也引來一些質疑之聲,認為作品某些類型化的特征,與茅獎一貫秉持的嚴肅性似乎大相徑庭。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如果沒有看到小說關于人性、命運思考的深層意蘊以及作者的敘事追求,茅獎也不可能頒給《暗算》。但不得不說,麥家一直在誤解與爭議中負重前行,從《解密》《暗算》到《風聲》,再到《人生海海》,他以一部又一部優秀作品彰顯自己作為嚴肅作家的創作意圖與創作才華。寫作曾經是麥家抵抗現實世界的方式,他曾經在訪談中坦言,幼時因為家庭身份問題受盡歧視與冷落,那時起就時常“陷入孤獨的幻想世界”,先是日記,后來是小說,文字為他構建了一個“安全的桃花源”。如果說早年的孤獨是他被動躲避外界敵意與不公的惟一方式,那么功成名就后的麥家依舊堅持“孤獨和純粹”的寫作,則是一個作家的使命和良心使然。
可以說,孤獨成就了麥家的文字,而麥家又反過來用文字詮釋了孤獨。在麥家的小說世界中,主人公揮之不去的孤獨感固然同他們的身份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源自其內心執著的信念,這份執著讓他們沉浸在理想世界中,甘愿畫地為牢,同現實人生保持疏離之態。在這個意義上,麥家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反英雄的個人敘事進行了顛覆性的改寫。我們知道,孤獨是現代文學反復表現的母題之一,現代人的孤獨感深植于世界的異化與信仰的跌落,個人與世界之間橫跨著被撕裂的鴻溝與深淵,就像加繆筆下那個備受爭議的“局外人”默爾索,生命的熱情已然消耗殆盡,盡管未曾向這個荒謬的世界屈服,惟一的抵抗方式卻也只是近乎麻木不仁的冷靜與超然而已。雖然在后來的作品中,這種冷漠疏離的人生態度被西緒弗斯式的反抗所取代,但在他們竭力挽救人類尊嚴與幸福的行動中,曾經燃燒于古典神話、傳統戲劇及浪漫主義文學中的那些形態各異的生命激情卻已不復存在。這種缺失同樣造成了中國當代文學中英雄主義理想的落潮——當然,是在完成它批判式自省的神圣使命之后。麥家筆下的孤獨更多的是因為過度執著的熾烈,就像《解密》中的數學天才容金珍,人生惟一的樂趣是將自己封閉在密碼破譯的思維殿堂之中,日以繼夜,廢寢忘食。還有《暗算》中的黃依依,縱使“701”的高墻重樓,也鎖不住她恣意奔放的情感追求,而他們最終的毀滅,雖則回蕩著命運的嗟嘆,卻也多少同靈魂深處那一團過度炙熱的生命之火有關。這種深刻的孤獨感清晰地映襯出當代文學長久以來黯淡了的理想主義光芒,從這個角度講,麥家的寫作有著不可否認的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把故事演繹到極致
遺憾的是,“諜戰小說”“特情小說”“類型文學”之類的標簽遮蔽了大眾對麥家作品價值的認知,大而化之地將其作品歸到了類型小說的定式想象之中。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麥家的創作軌跡,便不難發現作者在人性探索與敘事技巧方面一以貫之的用心。從《解密》到《暗算》,從《風聲》到《風語》再到《刀尖》,面對外界的質疑與非議,他沒有輕易放棄“特情”“諜戰”這些充滿爭議的題材,而是選擇在諜戰和密碼的世界中埋頭深耕,以一種冷靜精細又飽含力量的敘述姿態,反復去書寫那些縝密的情熱、疲憊的亢奮、隱秘的偉大,把所謂的“類型故事”演繹到極致。麥家幾乎是用戲謔的方式回應了那些質疑之聲。有人說他的作品只是類型文學,只是會講故事,作者便索性繼續講故事,講更精彩的故事,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不動聲色地傳達自己對人性、對命運、對生活以及對文學的思索與洞見。麥家自己也說,寫到《刀尖》,諜戰題材已經幾乎被他寫到極致,情感及素材的積累也有了捉襟見肘之感,這是作品寫到一定高度之后必然面臨的困境。對一個類型作家而言,止步于此已然足矣,但麥家與類型作家的根本區別是,他從不滿足于自我重復的寫作狀態。從《刀尖》到《人生海海》,麥家幾乎是“十年磨一劍”,在全新的文學書寫中華麗轉身,從題材到人物甚至敘述時空與情感記憶,都突破了此前諜戰故事的定式,展現了自己作為嚴肅作家的才華與實力,也再次證明了小說形式的可讀性并不必然有悖于文學主題的深刻性。
以故事性為依托建構自己的文學世界,這是麥家一貫秉持的寫作原則。他不止一次強調,如果必須在故事、思想以及人物與語言之間做一個選擇,自己一定選擇前者,因為他堅信小說家的根本任務即是“塑造人物、講好故事”。可以說麥家的寫作始于故事,卻絕不止于故事。他對“故事”的堅持,往往讓人想起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雖然本雅明將講故事的“說書人”與憑空想象的“小說家”相區別,但在麥家這里兩者卻產生了微妙的融合。他的新作《人生海海》一改此前聚焦單一人物或單一故事的敘述方式,將不同時空的人物故事交織融合,以結構的起落去應和意義的波瀾與聲響。同樣是一個跌宕起伏精彩紛呈的故事,即使選擇全知全能的視角和更為簡單的線性結構,從主人公出生寫起,按成長的時間順序鋪陳敘事也絲毫不會減弱其人生經歷的傳奇性,但作者卻選擇以第一人稱來封鎖敘事視角,刻意給整部作品的寫作增加敘述難度。在游戲之中探索文學創作的門道與技巧,以期“玩出一種藝術手段”來,這種自覺的探求意識和“陌生化”的藝術追求是冒險,也是挑戰,更是作家打磨寫作技巧、塑造個性化敘事風格的必經之路。這條路麥家走得并不輕松,甚至有點孤獨,但他用自己的努力向讀者證明了,優秀的文學作品與故事性并不矛盾,而他也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不斷地實現了自我突破。寫作之于麥家,似乎是一種嚴肅專注而又充滿激情的游戲之道,以游戲精神編碼智力游戲,與其說這是類型小說形式與嚴肅文學主旨之間的對抗,不如說是作者一個人的博弈,是他與自我的較量,我們從中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對刻畫與成全一種孤獨、崇高、悲愴的精神力的執著。從這個意義上講,麥家對寫作本身的探索與堅持同其筆下人物的那種激情和孤獨何其相似。
彰顯類型小說的敘事張力
麥家以諜戰小說豐富當代文學向度的創作實踐,讓人想起上世紀60年代末香港文壇關于武俠小說的爭論。武俠小說作為娛樂化、商業化的通俗小說類型,其程式化的書寫方式固然存在難以突破的局限,但并不能從根本上否認其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可能。面對評論界的質疑,金庸曾以莎士比亞的作品為例,對武俠小說寄予了樂觀期待,他認為,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在發展初期都必然經歷一個粗糲的階段,作品的文學性有賴于創作者以自己的才華賦予作品本身深刻的內蘊以及精致圓融的形式技巧。古龍甚至指出,通過“汲取其他文學作品的精華”,武俠小說完全有可能再“創造出一種新的民族風格的文學”。作為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與革新者,金、古二人的小說體現了文學創作的自覺轉變,而麥家對諜戰小說的執著又何嘗不是對前者的一種回應呢?相比武俠世界的虛幻與縹緲,諜戰小說聚焦真實的歷史時空與人性幽暗,因而更能準確地勾連個人傳奇與宏大敘事之間的對話。更重要的是,一如所有嚴肅作家一樣,麥家的寫作姿態是一貫的,在如何寫作以及通過寫作傳達什么的問題上,他始終保持著自己鍥而不舍的追求。這些追求的邊界或許模糊多變,但它的內核始終是明確清晰的,那就是人性的解碼與追問。正是這種內在的品質,才使得麥家小說收獲了海外的無數贊譽,使西方讀者得以進入到遙遠中國的歷史空間,亦讓當代文學在他者與自我的雙向視域中實踐建構性的書寫,在世界文學的眾聲喧嘩中發出中國作家的聲音。
麥家小說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固然得益于包括翻譯者、出版商和媒體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場運作,但歸根到底離不開作品本身的價值。除了嚴肅的文學主旨以及圓熟的寫作技巧等一般性的文本因素外,關鍵還在于麥家作品中東西方元素的共鳴。《解密》和《風聲》的英譯者米歐敏認為,麥家對西方偵探故事中解謎因素的借鑒令其作品具備了暢通無阻的“世界性元素”。如此一來,縱使小說涉及西方讀者稍顯陌生的歷史背景,也不會感到閱讀的滯澀。不可否認,麥家在很多作品中都巧妙地使用了西方小說的敘事技巧,尤其是《風聲》,從小說對解謎過程、懸疑效果與邏輯推理等濃墨重彩的描述來看,它確實比麥家的其他作品都更接近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結構,而故事的精彩程度即使同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者迪克森·卡爾筆下最經典的謎題相比也毫不遜色。但《風聲》終究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偵探小說,偵探小說看似隨意的行文中隱藏著一種“確定的風格類型”(克拉考爾語),包括作為核心敘事線索的真相推理與富于象征意義的人物塑造等等;而麥家作品卻相反,在“諜戰小說”“特情小說”“新智性小說”等諸多標簽的背后,恰恰是類型的模糊與曖昧不明,這正是作者不拘一格跨界寫作形成的藝術風格。
從《風聲》到《人生海海》,麥家的小說以圓熟的敘事技巧打破類型書寫的限制,借與之相悖的“真相不白”的結局,隱喻了類型文學的模糊性與可塑性,彰顯了類型小說也可能具備的敘事張力。盡管麥家作品不乏偵探小說或懸疑小說的元素,但其內核卻是純文學的。其中既包含對歷史話語的批判性思考,也表現出復活崇高英雄理想的悲憫精神。前者集中體現在早期的作品中,比如《風聲》,小說以虛構的真相為“序言”進入歷史真實的核心場域,在“東風”“西風”與“靜風”的交互視角中以復調手法再現皮埃爾·諾拉所謂的歷史的“記憶之場”,不僅隱喻了歷史話語的不可靠,更以文類本身影射歷史敘事的虛構性。后者則在《人生海海》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麥家一改此前對智力游戲以及間諜故事的偏重,將筆觸投向鄉村社會中普通人的日常,在批判人性幽暗的同時又為“后英雄時代”信仰失落的現代人指出了一條精神出口,即坦然接受世事多變命運無常的事實,在對苦難的擁抱中學會熱愛生活、熱愛生命。“人生海海”,讓人想起加繆《鼠疫》中所傳達的反抗哲學:戰爭的爆發讓這位才華橫溢而又滿懷人道主義精神的小說家,從早期西緒弗斯式的“內心反抗”走向全面的“行動反抗”。面對世界的荒誕以及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反抗不僅是通往幸福的惟一方式,也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惟一方式。反抗的背后,則浸潤著古典悲劇精神的底蘊。這種崇高的悲愴性無疑給麥家筆下那些看似曲折離奇的傳奇故事增加了幾分歷史的厚重與哲思的深沉。
由此可見,從戰爭密碼到人性密碼、從特情機構到鄉村日常、從解構性批判到建構性反思,麥家拓展了純文學的認知視域,為當代文學書寫注入了新的生機。特別是《人生海海》的敘事張力,讓我們看到了麥家作為嚴肅小說家的才華和用心,也驚嘆于他自我突破的勇氣以及堅守“說書人”本色的決心。總之,閱讀麥家是一種奇妙的體驗,他的故事看似一個回旋往復無懈可擊的封閉圈,又仿佛只是某個宏大敘事鏈中小小的一環。當你在這個故事中同他告別時,不覺已經開始期待下一場的相遇。或許這是麥家之于當代文學的另一重意義,在反復的故事敘述中探尋中國文學之于世界文學敘事鏈中自我衍生的可能性。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