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記憶與空間符號認同的東北書寫
來源:中國作家網 | 2020年06月24日09:10

“和光讀書會”的成員是大連理工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點的師生,主持人戴瑤琴,啟動于2018年6月。去年,讀書會部分成員參與了中國作家網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專題的系列讀書活動,“和光”已顯示出更明確的定位:本碩貫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以主題沙龍和作家課堂的形式把讀書與創作同時推進。本期讀書會,6位“和光”的“90后”成員,共同討論雙雪濤的《獵人》、班宇的《冬泳》和鄭執《生吞》,議題核心不是單純的“東北書寫”,而是小說中開放的時代感、文化質地和美學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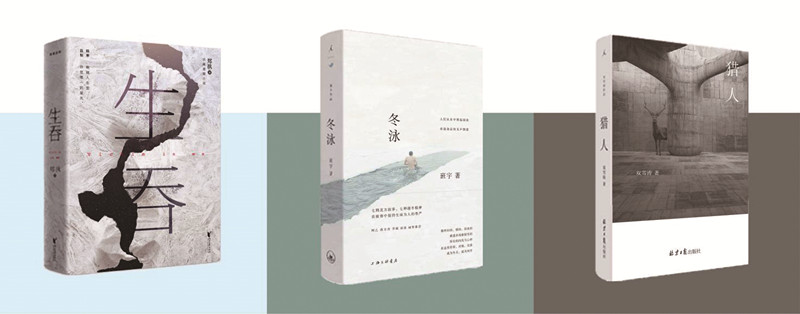
陶兆基:當我們發現“東北”作為一種地域文化背景在青年作家雙雪濤、班宇、鄭執的若干作品中“共時式”出現時,考察“東北”元素就成為主動論題。越過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的民俗色彩,當代青年究竟如何在社會與時代的夾縫中描摹東北的文學面貌?作家如何通過寫作東北,為當下的讀者重塑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記憶?東北青年作家近年寫作的相似點非常多,甚至令人好奇他們是不是都在同一街道長大。小說主要人物可粗分為小城少年、文學青年、底層中年;敘事的話語形態基本是間接引語與自由間接體的混雜;氛圍基調常為苦澀灰暗。但就更細節、更重要的寫作技巧來講,首要的應該是語言問題。金宇澄通過《繁花》給出了地域書寫的吳語摹本,如何將東北方言融入書面便也呼喚著一個范例的出現。雙雪濤寫作中的隱含作者往往試圖專斷地代替人物說話,直接引語的風格與人物身份的脫節似乎從未得到解決,這也給我們拋出了問題:出走的青年知識分子能否代替中年民眾言說?這種思量并不出于對創作意圖的揣摩,而是源自對小說技巧的批判。班宇提供了更好的方案,他對東北方言的書面化處理恰到好處地運用“夠嗆”“不能吧”“挺有主意”等口語,而不是刻意地拋出幾個裝飾意味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名詞(地名、物件等),在地域特色塑造上非常純熟。鄭執在《生吞》中將敘事視角分為王頔(第一人稱)和馮國金(上帝視角),這是聰明的寫法,因為規避了后者難以把握的同敘述者聲音,即如何將一位東北中年民警的語言實施書面化的相應難題。
除了歷史和方言,“地方”還意味著什么?當我們觸摸到故事的肌理,比如雙雪濤《冷槍》《松鼠》的小鎮青春,班宇《盤錦豹子》一地雞毛的日常、《空中道路》工人下崗的命運轉折,鄭執《生吞》中黑警勾結與爛尾樓、校園暴力和街頭炸串過量的添加劑,這些并不是東北獨有的,而是在那個年代中國南北各地都能找尋到。東北作家并不先天具有“文學化”東北的義務,選擇家鄉作為作品背景也僅僅是創作者寫作生涯起步時的慣常選擇。暫時拋開“東北”,便能發現三位遼寧青年作家不約而同地指向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時代記憶書寫。
王玥梟:流行于網絡的“東北話”,既是一個抽空歷史深度與文化內涵的能指,又是一個充滿偏見的隱喻。這種文化陰影,必然是雙雪濤、班宇、鄭執的書寫要正面迎擊的困境。重述東北,也是一場文化的斗爭。3位作家在敘述中,都高頻使用一位或多位第一人稱敘述者,擔任小說的主角或核心事件的觀察者。這一言說主體在方言與書面語中切換自如,例如班宇的諸多小說,并不構成對“真實”的破壞,反而完成了語言的突圍。敘述選擇造就出新的言說主體,它既不流于傷感,也不淪于世俗,而是飽含尊嚴。而文學創作,記錄且呼喚著在日益分裂的文化環境里整合差異、尋找集體的可能。
正如瘋狂與罪愆構成現代小說的主題,刑事案件展現出“成問題的個人”對于自我的找尋。《生吞》是其中一個重要文本。小說在懸疑案件的外殼中講述一段殘酷青春,故事結構并不新穎,但內容頗值得關注。青春屬于由王頔、馮雪嬌、高磊、秦理和黃姝等工人子女、商人子弟、天才組成的集體。青春的消散就是集體的分崩離析,伴隨著同伴間彼此的背叛與分離,伴隨著殺人真兇多年來的逃逸,伴隨著階層分化、東北衰退的歷史宏大背景。
“人們之所以這么多的談論記憶,是因為記憶已經不存在了。”在閱讀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小說時,皮埃爾·諾拉這句話讓我深深感到觸動。如果說這段歷史理應作為一種公共的文化記憶,那對于新世紀的我們來說,這種記憶卻是由虛構的小說所創造的。我并不認為,將一部小說緊密比附于時代是對所謂“文學性”追求的貶低和侮辱,反而正是這種鮮明的時代特征給予作品以無比厚重的歷史感。它并不指向抽象而又膚淺的哲思,而是關于時代的記憶,鮮活、生動,飽含尊嚴與溫暖。《生吞》結束于地洞中的星光,它既是對青春的追憶,又是對一個時代和兩個生命的致敬,還是對生活自身的探尋。
趙 鼎:雙雪濤、班宇和鄭執從“子一代”的角度敘述著世紀之交的東北,展現社會變革,描摹眾生百態,探求人生哲學。鄭執的《生吞》里,有一開始便處于瘋癲狂亂狀態下的“失語者”,亦有被生活步步緊逼而走向“非人”之人,最后他們只能發出如野獸般嘶啞的怒吼,以暴力的手段使遲來的正義得以伸張,抑或走向茍活的沉默。可以說,在道德與良知消磨殆盡的邊緣,底層生命已然淪為社會暴力的最大承載者,“鬼”早已從故事和傳說中融入現實,侵蝕著無數的心靈與生命。班宇的《冬泳》著重刻畫小人物的掙扎與潰敗, “棄子”似乎成為共同命數。他們曾努力改變現狀,也嘗試過出走逃離。無數迷惘的靈魂在悲涼現實與渺茫希望中徘徊,已成光下的黑影,那么,從父輩傳至子輩的生存難題與精神困境該如何破解,答案難尋。與《生吞》和《冬泳》不同,雙雪濤《獵人》中的許多人物雖然具有“東北”特質,但其故事發生地與敘述側重點已不是東北本身了:《女兒》中遲遲不來的女兒可以從《等待戈多》中找到回應;《武術家》和《Sen》將目光投向了歷史之維;《預感》是融匯過去、現實、未來的想象碰撞;《獵人》則描寫了身處北京等地的邊緣性小人物的碎片化生活,這些小說大多在現實與虛構之間游走,構思精巧,手法新穎,頗具荒誕性意味。《獵人》可以說是雙雪濤意圖突破其“東北作家”標簽的一次嘗試,我們從中感受到他超群的創作稟賦與野心,然而遺憾的是,或許正是力求突破創新之故,部分小說技巧有余而內力不足,略顯急于求成。
從記憶倫理學角度來看,班宇的《冬泳》、鄭執的《生吞》與雙雪濤前期作品,更傾向于對東北苦難記憶的書寫。站在當下重構過去的創傷記憶敘述、集體記憶的傳承和輸出,無疑對重審、補充與反思東北文化具有歷史和文學上的雙重價值。我認為,上世紀末出現的生存困境如今依舊延續,并且已逐步從經濟層面延展到了文學話語權層面。那么,在新媒體時代,在大眾傳媒和公眾輿論為東北貼上層層標簽的今天,除重新敘寫歷史之外,如何在現今的文化環境中打破固有的誤讀標簽還原真實東北,如何從地域文化出發進而反映普遍人性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牛煜琛:在東北,但凡稍具規模的城市,你總能從中找到一條街道或社區,以“興工”為名。而在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小說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種類似的存在:對東北這片土地無意識的眷筆,以及走出它的愿望。
在“小說”的路上,雙雪濤較之班宇跋涉得更遠。《武術家》里,他放棄了解釋上一代人故事的專屬權利,放棄了“子一代”敘事的天然合法性,指引我們追溯至更難以構想的舊“東北”,作者握住廣泛且自由的傳奇話語,即探測歷史底層。孤注一擲的時空轉移是雙雪濤在地域開發上的努力,而更加強烈的“出走”愿望亦寄寓其中。
《生吞》作為情理完備的長篇,其所摹擬的“東北”環境也相當詳實——尤其貼合閱讀期待。無論是道上仇殺、命案尚懸,還是東北的土語粗話,都為故事鋪開提供了親切的設定。但從文學性來看,鄭執只是借此背景講述一個青春、生命與救贖的案件,一切只是恰好發生在東北,并非秦理、黃姝等人對地域情有獨鐘。“東北”于此,只是充任一種道具。
東北更多時候只在代言一處方位和一種溫度,而我們對“東北”文學的誤讀也如是。東北愈漸被以一個籠統的、附之引號的范疇加以解讀,甚至其自身也在外來偏見中甘于“他者化”,3位青年作家就在反抗這一趨勢。
高瑞晗:雙雪濤、班宇、鄭執的作品各不相同,但都與東北老工業區有緊密聯系。他們將自己最熟悉的語言——東北話融入作品中,字里行間夾雜著東北人特有的幽默及自嘲、殘酷和決絕。在敘述背后,他們表現出對城市小人物的關注、對歷史與現實的惶惑,以及由此產生的逃離渴望。
在鄭執的《生吞》中,秦理和黃姝相依為命,卻被殘忍的集體合力推向死亡。親歷者“我”認為是自己的膽怯、懦弱將好朋友推下深淵,事實上,社會才是幕后黑手,它給人希望卻又將人生吞活剝。鄭執通過5位青少年與命運的輪番抗爭,展現被現實“生吞”的小人物的生存實況。
需要留意小說中提到的“艷粉街”,這是沈陽的一處棚戶區,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獵人》也涉及這片區域。艷粉街的秘密都被收藏于暗夜,雙雪濤的少年時代就在艷粉街度過,這個在小說中被形容為“爛泥塘”的地方,是他最熟悉的地點。關于艷粉街,雙雪濤曾提到:“我并不是只寫東北。我只是借用東北的一些素材,來寫人和人性。艷粉街早已經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經模糊。”因此,艷粉街早已成為一個符號,用來標記城市中的邊緣群體。
與艷粉街功能相似的是班宇筆下的“工人村”。《工人村》記錄著各式各樣普通且悲傷的故事,如足療店的呂秀芬,超度法師李德龍和董四鳳,從小混到大的同學戰偉。《冬泳》有一個屬于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背景“下崗”、“買斷工齡”。“下崗潮”席卷東北工業區,無數家庭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與骯臟破舊的棚戶區、筒子樓遙相呼應,這是東北“80后”作家對已逝時代的惶惑。 他們用冷靜平和的筆調,在作品中勾勒出被“生吞”的小人物群像。
小人物無力感的來源是生命個體在歷史與現實的裹挾下,無法回避又無力改變的無奈。他們只是時代碎片,命運的悲劇產生于歷史細節,偶然性的背后埋設著必然結局。就在與命運的殊死搏斗中,他們發現,比現實更殘酷的還是人性。
劉靜瑤:3部小說的敘述中都穿插著創作者對于自身故事的解碼。鄭執《生吞》藏于“懸疑”標簽之后的,是作品作為青春傷痛文學的事實。王頔坦白當初曾送給黃姝一盤磁帶,磁帶分A面與B面,文章的段落劃分及敘述視角也基于二維,王頔與馮國金分別位于敘述首尾,在不斷交織、不斷印證中推動故事層層遞進,第一人稱的成長故事便是對第三人稱的案件重構的解碼。班宇小說的方言化語言往往在敘述臨近尾聲時倏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統書面語。這般抽離的敘述寄身于故事之中,也在潛移默化中消解故事里日常的寡淡,在賦予作品更強敘事張力的同時,發起了基于既有社會邏輯的新一輪試探。雙雪濤會將筆觸盤桓于小人物,就如《獵人》中的呂東,仿佛是作者的一種投射。人物憑借著故事現有身份而成立,卻因成為作者自身觀點的話語媒介而存在。同時,雙雪濤作品中存在大量同名角色,如“劉一朵”,小說體現著“省力的懷念”,即在虛構自我與虛構故人中情感互動。
東北書寫,一方面記敘了作家的東北記憶,另一方面也促進東北人對自身文化符號的認同。《生吞》的結尾,長大后的王頔等人再次回到防空洞,望著洞內的光景,回憶舊友,想著“原來真的有星光”。同樣的情節興許也可以發生在其他地方,但防空洞指向了敘述無形中綁定的東北本土經驗。
雙雪濤的小說帶著鐵色,班宇的小說起伏著暖黃色,而鄭執的《生吞》回環著墨綠色。3位創作者具備不同的文字氣質,相似的下沉式“取景”,重建大時代中小人物的社群身份。我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東北地域文化的影子,那是源于作家不自覺中流注于筆端的文化理解。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0年6月24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