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小說的現實主義內在轉換
石頭金屬等紀念碑的材質相異,但都“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過去的某一事件,同時也是對這一事件后果的鞏固和合法化──即國家形態意義上的中央權力的實現和實施”(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紀念碑是權力與秩序的昭示宣諭,成為國家、種族、文明、政權、政黨等總體性的象征。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不同歷史階段雖有不同提法,但為革命事業、為人民、為英雄、為時代等樹碑立傳的要求一直是其題中之義,規訓著現實主義建造文字的紀念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就是為農民運動、土改、解放戰爭、合作化運動等樹立的紀念碑。“紀念碑性”本指紀念碑的紀念狀態和內涵,本文中指現實主義不斷演變的歷史內涵和功能。由于文學必須經由作家主體創造,文學的獨立性和意識形態化的現實主義形成復雜的纏繞,這就使得現實主義的紀念碑模式雖然不變,但其“紀念碑性”一直在發展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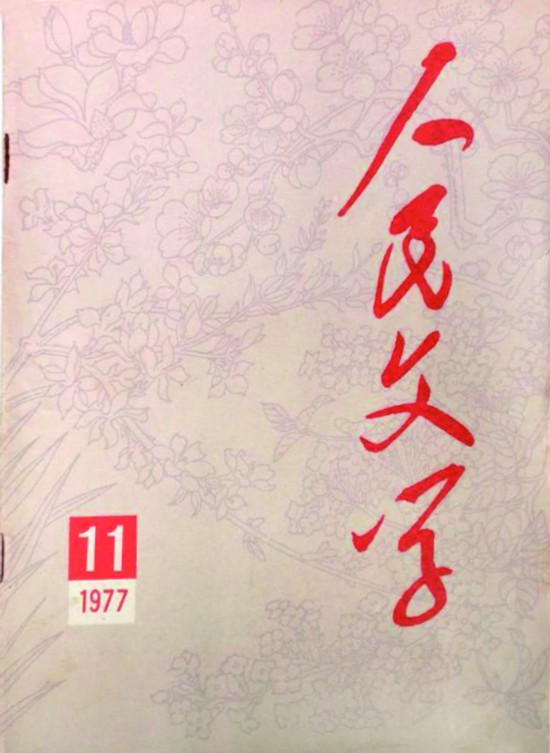
短篇小說《班主任》發表于1977年《人民文學》第11期。
1958年在《讀書》發表《談〈第四十一〉》,是劉心武創作的起點。但真正“人盡皆知、朝野轟動”,還是因為1977年其在《人民文學》發表的《班主任》,這一已載入史冊的標志性文本被稱作“新時期小說的第一聲吶喊”,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已成為當代文學的坐標點。當時的中國作協領導馮牧說,“劉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給我們當前的創作提供了范例,這樣的范例可以起到開辟道路、引導和促進其他作者在一個新的創作道路上探索前進的作用”(馮牧《打破精神枷鎖,走上創作的康莊大道——在〈班主任〉座談會上的發言》)。
沖破禁區,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開路者、奠基者、領跑者,這是劉心武刻進歷史的身影。在新時期政治、社會、文學“否定文革”的共識高度一致的背景下,真理標準討論的政治文本與傷痕文學的文學文本等協同呼應甚至文體互相滲透一并匯成了“新時期話語”,與正在建構的新的政治體制與文學體制互為表里、協同共進,夯筑了新時期的合法性與總體性。劉心武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愛情的位置》《我愛每一片綠葉》等作品大都以新舊政治觀念與思想觀念的矛盾結構情節,解決問題依靠政治方法和政治權力,充滿強烈的政治抒情與政治呼告,由是被推為現實主義的標桿與范例。這些作品與現實政治合拍的強烈政治性,使之成為政治表征。劉心武后來稱之為自以為真理在握說教式的“真理敘述”(傅小平《劉心武:我寫的東西,都和自己的生命歷程有關》),這正是那時現實主義的“紀念碑性”。
此后,劉心武又相繼創作了《如意》《木變石戒指》《立體交叉橋》等作品,這些作品不是簡單的政治訴求與政策圖解,而試圖將現實主義的“紀念碑性”轉向人性人情、轉向底層大眾,這一階段積淀的最高成就是長篇小說《鐘鼓樓》。《鐘鼓樓》以一天為經,以北京的一個四合院為緯,以一場婚禮為主軸,萬花筒般轉開四合院中9戶人家的家世浮沉,編織出相關幾十個人物的遭遇,這些人物的活動連接起歷史現實、城市鄉村、首都外省和機關工廠街區,立體編織起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社會空間。他們上輩是滿清貴族、喇嘛、農民、乞丐、民間藝人、妓女等,他們的職業是售貨員、司機、廚師、綠化工人、修鞋匠等,雖然也有高干、翻譯、編輯、演員、醫生等中高層人士,那也不過是為了映襯出底層社會的深廣復雜。《鐘鼓樓》是新時期文學中最早的民族志敘事作品之一,接續《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墾殖北京文化的京味小說傳統,歷史化地塑形城市及城市空間,追溯現代城市的初始印記和混合空間的變遷,又是都市志化的城市文學的奠基作品之一。
《立體交叉橋》發表后,有批評家勸導劉心武,“作家可以刻畫小人物,但作品里不能全是小人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應當塑造出先進人物把讀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導”(《神會立交橋》)。很明顯劉心武并沒有接受這樣的教令。《鐘鼓樓》中他只在一個有改革精神的局級干部張奇林身上體現了當時的政治主題改革,整部小說基本還是小人物的小日子,寫他們想把自己日子過好的努力,寫他們微弱的善念與小小的惡,薛大娘偏心小兒子在大媳婦面前擺婆婆架子、澹臺明珠與師姐爭戲、海老太太總是瞎編自己家的傳奇、新媳婦潘秀婭打算盤一樣算計出自己的婚姻、詹麗穎熱心卻無禮、慕英嫁給殘疾英雄才從僻遠小鎮跳到京城又拋棄了英雄、大混子盧寶桑總犯渾、小廚師路喜純善軟弱因父母出身低賤而自卑、梁福民兩口子省到牙縫里又不能吃一點虧……蕓蕓眾生吵吵嚷嚷熱熱鬧鬧的日常生活,讓現實主義也豐沛起來。《鐘鼓樓》是一部北京市民生活世態與底層社會的紀念碑,很明顯,這部作品中的“紀念碑性”已從政治表征轉為社會表征與文化表征。第二屆茅盾文學獎授予《鐘鼓樓》也體現了意識形態對現實主義的開放。
《鐘鼓樓》前后的劉心武一直在文學體制的中心,甚至可以說就是中心。茅盾、冰心、巴金、蔣孔陽、馮牧等前輩作家理論家都對他充滿期許和信任,王蒙、劉再復等崛起的文學力量也對他極其友好。他曾調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后又任主編。他的創作也是順風順水拓展精進,《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私人照相簿》等紀實小說與個體歷史隨筆相繼引起轟動,引領風氣。劉心武在上世紀90年代的創造力依然旺盛,相繼創作了《風過耳》《四牌樓》《棲鳳樓》《樹與林同在》等四部長篇和《小墩子》等眾多中短篇小說和大量隨筆,其中最優秀的當屬《四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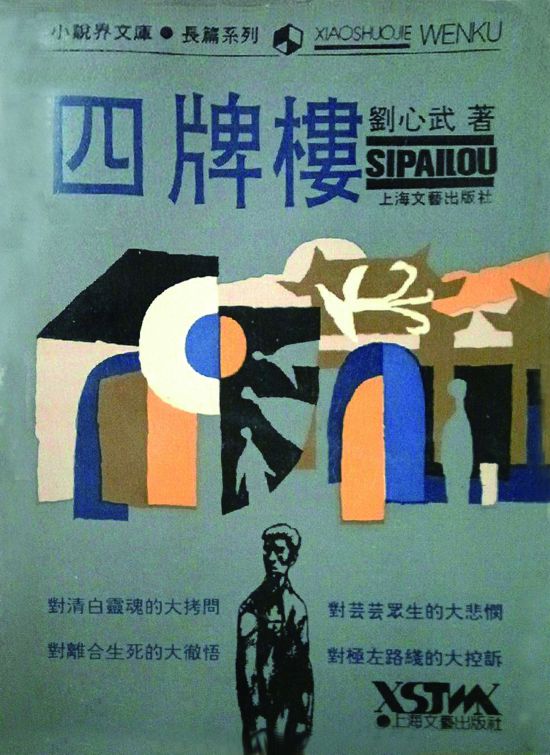
《四牌樓》是劉心武創作中藝術最為純熟、人性探揭最為深幽、歷史感最為厚重的作品,它動用了作家最為隱秘真切刻骨銘心的家族生活資源。小說以作家蔣盈海及其四位哥哥姐姐的人生起落情感流變為主線,穿插進蔣氏家族及其親好在20世紀百年中國的離散榮衰生死悲歡,在時代與生命個體的相互搏擊中叩問人性之實、探求存在之真。蔣家四代人,蔣盈海的爺爺是清末舉人,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后又參加北伐,他的七舅也是早期共產黨人,姑父是畢業于西點軍校的國民黨親美派將軍,后起義投誠;姑母早年隨父參加大革命擔任何香凝的秘書;父親一直在海關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調到海關總署,其后歷次運動中蔣家傾覆離散枝葉飄零,為了生活奔走在東西南北,從弄潮時代到飄萍時代,蔣家代有英才卻蹭蹬磨滅。《四牌樓》承繼了家族小說的傳統,既有《紅樓夢》的繁華散盡悲霧縈夢,又有《家》《財主的兒女們》等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更有時代驚濤中潮頭翻船、瓜果飄零的離散敘事(臺灣文學中的離散敘事已是文學史常識概念,大陸文學中敘述時代惡浪、家庭覆巢、親族分離、背井離鄉的作品也可用離散敘事的框架分析)。《四牌樓》的題詞之一是《紅樓夢》中的“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點明的不但是小說的師承,還有其為女性立傳的動機。小說從蔣盈海初三時就有的一個愿望開篇,那愿望就是寫一本小說《阿姐》。小說結尾,蔣盈海追溯這部書的緣起,越過寫《阿姐》的初愿,他突然想到少年時四牌樓下照相館櫥窗里陳列的一幀女子照片,他曾多日癡癡凝視。這首尾的呼應,確立了《四牌樓》的敘事更偏重于女性人物。小說的主體內容是蔣盈海的姐姐蔣盈波和她的三位高中同學崩龍珍、鞠琴、田月明命運波折的青春、婚戀、工作、家庭生活,以及關聯的眾多女性的經歷,在蔣盈波四位同學之外還刻畫了姑媽、八孃、四孃、童二孃、歐媽、香姑、曹叔原配、爺爺最后的戀人女赤衛隊長等上輩女性,以及澗表妹、邢靜、邢玉、甘福云等平輩,還有蔣唱、颯颯、常嫦等晚輩,揭示大時代碾壓下女性的苦難和政權、男權下女性的壓抑、犧牲與扭曲,而最小一輩的颯颯、常嫦也顯示了新時代女性獨立的意志和力量,預示了女性的希望與未來。《四牌樓》是少有的20世紀中國女性畫廊和女性生存的心史,這部小說是唱給生命、家族,唱給女性,唱給20世紀的一曲長恨歌。這部小說的成功不單在于眾多人物的生動塑造和故事的跌宕起伏,還有像照相一樣精微逼真的描寫、諳熟的人物群雕、各種敘事人稱的自由轉換和強烈的抒情風格。劉心武自己也認為《四牌樓》是他最好的作品,“我最滿意的是《四牌樓》”(《〈劉心武文粹〉總序》)。
“除非發生某種難以預料的災變,北京的鐘鼓樓將成為社會歷史和個人命運的見證而永存。鼓樓在前,紅墻灰瓦。鐘樓在后,灰墻青瓦。鐘鼓樓高高地屹立著,不斷地迎接著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這是《鐘鼓樓》的結尾。在《鐘鼓樓》中,現實主義的總體性還在,鐘鼓樓就是一個總體性的象征,象征著神圣的時間,確立一種永恒的秩序。作者把小說中所有人物的活動、他們的過去現在未來全部統領進鐘鼓樓的象征。而《四牌樓》中,四牌樓早已拆毀,成為曾經實有的虛無。
進入21世紀,劉心武趕上了文化傳媒變革和大眾文學興起的機遇,在百家講壇開講《紅樓夢》再次走紅,他的創作力不減,長篇小說《飄窗》《無盡的長廊》等相繼出版,他依然在現實主義的路上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