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文書信集》的七封佚信及其他
來源:澎湃新聞 | 雷強 2019年01月25日08:06

《胡適中文書信集》,潘光哲主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適紀念館,2018年10月出版
11月5日,筆者突然收到臺北舊香居書店吳先生的留言,告知“中研院”版《胡適中文書信集》和《胡適時論集》即將上架,這著實令人興奮,尤其是這兩種書的定價比聯經新版《胡適日記全集》(據吳先生說只是翻印,并未增補)親民許多。于是,筆者斗膽開口求其代購,承蒙吳先生費心,親往南港近代史研究所取回厚厚五大本,并以航快寄送北京,19日晚《胡適中文書信集》就出現在筆者的書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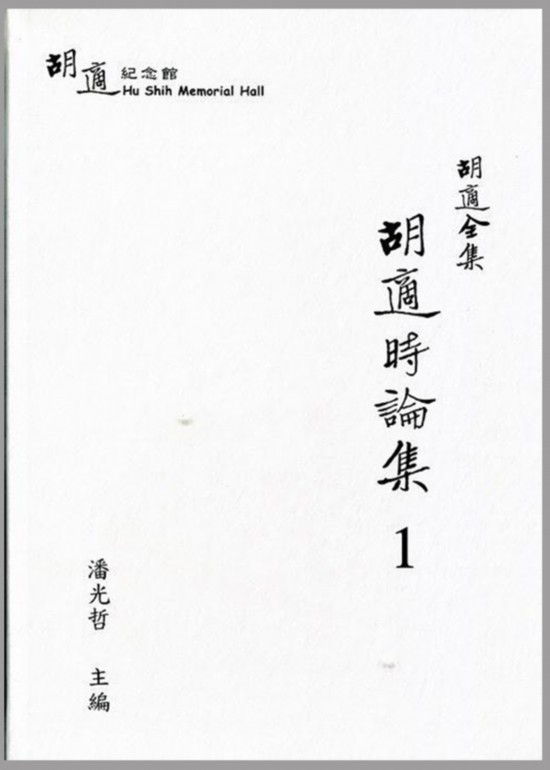
《胡適時論集》,潘光哲主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適紀念館,2018年10月出版
“中研院”版《胡適全集》共分為“文存”“書信集”“時論集”“日記”“詩存”“單行本論著”以及“文章編年”,其中“書信集”和“時論集”最先付梓。相對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2013年),《胡適中文書信集》僅收錄胡適先生的手札,他人的來函概不入選。此法雖略有遺憾,但編者既然設定了揀選原則,必然有其初衷。即便如此,“較之舊版《胡適全集·書信》字數約為一百一十余萬字;新版《胡適中文書信集》多達一百六十余萬字,搜羅整理更為完整,從而為了解胡適的思想與人際網絡,提供更廣泛全面的線索”。胡適紀念館的介紹絕非虛言,即便不收來函,新版書信集也比《胡適來往書信選》多了近六萬字。筆者稍稍翻閱即發現了很多首次公開的書札,譬如1931年4月19日致趙萬里函、1958年3月22日致袁同禮函,它們均屬胡適檔案檢索系統中新披露者,從未被學界所知,讓筆者為之狂喜。可以預見,《胡適中文書信集》將為廣大學人提供更多的珍貴史料,極大地推動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
一、佚信
“中研院”版“書信集”雖然沒有冠以“書信全集”之名,但隸屬《胡適全集》之下,且“以‘精益求精,后來居上’為目標,期可為學界提供最完整(毫無刪易)與最精確(匯總各種版本,進行編校)的胡適著作文本,以便利用”。潘光哲先生在編者序中如此表述,其目標和志向自然是盡其所能求全,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來臨之際,假該書為胡適先生作一總結與紀念。
然而就筆者所見所知,尚有胡適先生七封親筆手札未被編入《胡適中文書信集》,這著實令人遺憾,故撰文希望有所補充。這些佚信的情況各不相同,其中袁同禮先生家人藏有胡適先生書信三封,均寫于1919年,筆者獲得其特別授權,予以公布;上海市檔案館曾刊布過一封;另有三封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依照其時間順序,整理如下,原文中的小字改用括弧標注。
(一)
守和先生:來信說清華學生要辦一個“白話文學研究會”,我聽了非常高興。那時我若有工夫,一定來加入討論。定期何時,請早日告我。
弟胡適 敬上。
三月七日
按:此信寫于1919年3月7日,清華學校“白話文學研究會”成立于是月初(見《清華周刊》第一百六十一期“校聞”一欄)。此信為筆者所知胡適、袁同禮兩位先生交往的最早記錄,后者時在清華學校主持圖書館事務,廣泛邀請學界人士前往該校演講。從上款的敬稱——“守和先生”亦可推斷二人剛剛結識不久,自此友誼日漸深厚,直至1962年初胡適先生去世。
(二)
守和吾兄:那天我從教育部會場回來,翻出我的記事簿,方才知道我曾應許送吾兄一本哲學史,并不是應許孟先生的,是我記錯了。所以我把書送上,請你賞收。還有中學白話文學會要我(四月十九日)來演說的事,我一定來。但是如果他們能改在四月廿六日,便更好了。因為二十六日我要來清華做評判員。
適
按:此信應寫于1919年3月底4月初。“教育部會場”似指教育部所開“全國教育調查會”,該會自3月27日開幕(見《申報》3月29日第三版“專電”一欄)至4月初結束(見“教育調查會第一次會議報告”,《教育雜志》第十一卷第五號)。“哲學史”即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年2月初版,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孟先生”待考。4月26日(周六),胡適在清華學校禮堂做“白話文學何以必須研究”的演講;同日晚八時,清華學校舉行國語演說比賽,參賽者羅隆基的發言——“中國留學生”最為引人注目,胡適、金邦正(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趙國材(清華副校長)為裁判員(見《清華周刊》第一百六十八期“校聞”一欄)。
(三)
守和吾兄:前幾天在清華,可惜不曾見著你談談。現在我因有一事,要想借貴校的留美學生季報(自一九一七年起)一用,準于二十六日帶回奉還。不知可以嗎?
胡適 敬上。
(四月十五夜)
按:此信應寫于1919年4月15日。《留美學生季報》的前身為《留美學生年報》(1911-1914),1914年3月正式改組成為“季報”,其主編多由清華學校(大學)留美學生擔任,如陳達、沈鵬飛、羅隆基等人,該刊先由中華書局出版,1917年改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
菊生先生:我譯的白郎寧的詩,只有二篇曾發表過,今抄出奉上。尚有一篇,系早年用古文譯的,一時檢不出了。
又聞一多、徐志摩二君有譯白郎寧夫人的情詩二篇(見新月第一卷第一號),聞君譯了二十一首(見新月第一卷一、二號),徐君作解釋,皆甚用功,也送上。
胡適。
十九,七,十三。
按:該信藏于上海市檔案館,收錄于《上海市檔案館藏近現代名人墨跡》(2014年,435頁),陳子善先生對此信有詳盡的解讀(見2015年11月1日《文匯報·筆會》),筆者不再贅述。
(五)
守和兄:前晚承賞飯,感謝感謝。珍本經籍刊行合股,先繳一股,俟安居后有余力當續繳一二股。另送上拾元零貳角,為購刊之四種書之價,其書已收到了。兩項共六十元零貳角,合開支票一帋奉上。
胡適。
十九,十二,十。
按:該信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未曾公布過。1929年11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刊行珍本經籍招股章程》公布,開辦費暫定一萬元,共分二百股,發起人為學術界、文化界名人,共計三十位,胡適先生與袁同禮先生均在其中(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五期)。左側“退十元〇貳角”非袁同禮先生親筆,可能為具體經辦人的備注。
此外,筆者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92年,376-378、407頁)中亦曾見到胡適的兩封書札,分別為1933年5月3日致段錫朋和錢昌明、1935年3月5日致袁同禮,未輯入《胡適中文書信集》。這兩封信又經《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2009年,241-242、272頁)排印過,筆者就不再重錄了。
二、問題
直至今日,筆者尚未翻完五冊《胡適中文書信集》,但已發現兩個值得商榷的小問題,故提出供學界探討。一是該書雖然廣加引征,利用各種資料,而某些材料的原作者曾修訂過舊作,編輯小組的老師們似乎并未就此類文章前后兩個版本予以必要的甄別,導致誤系;二是胡適先生少部分信札于落款處并未注明日期,編者對此僅做了大致限定,若更加仔細翻閱胡適紀念館館藏資源,或有進一步明確撰寫時間的可能。
(一)
《胡適中文書信集》第二冊中收錄了1932年7月9日致江紹原的兩封信,其出處為張挺、江小蕙《雪泥復見飛鴻爪——胡適又六封佚信箋注》一文(見《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八期,26-27頁)。這兩封信又都收錄于《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華書局》,2006年,205-206頁),江小蕙女士在手札影印本中將其中第一封信改為1932年6月17日。這一變動似乎并未被書信集編者所注意到,江小蕙女士也并未解釋修正日期的緣由,但筆者認為這封信應該寫于1934年7月初,另外一封由胡適本人標注“七月九日”的信則,也同為1934年所寫。理由有三——
首先是如張挺、江小蕙“雪泥復見飛鴻爪”文中所言,1933年6月1日《新月》在上海發行完第四卷第七期后正式停刊,雖然該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紀念號)間延宕了半年多,但此種停頓并無停刊之虞,而是在收集徐志摩遺作及親友的紀念文章,如1931年11月26日《申報》登載“徐志摩昨日大殮”,文中明確告知“至徐先生平生創作、將搜集由新月書店出版志摩紀念號”(參見本日《申報》第三張第十一版),而“志摩紀念號”的發行時間應為1932年8月;胡適給江紹原信中提到“近日葉公超兄與我們商議把新月月刊在北平復活”,更似指《新月》正式停刊后,考慮到胡適先生1933年6月11日離平、6月18日晚由上海坐船出洋,這意味著此信極有可能是1934年夏所作。
其次,信中提到“小兒子病猩紅熱,至今已兩星期……令姪女調在傳染病部”,張挺、江小蕙文中特別注明“令姪女”為“江紹原之兄江亢虎長女江兆艾(名菊)”,事實上江亢虎長女為江兆菊、次女為江兆艾,前者1928年獲燕京大學理學士并于1932年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見《私立燕京大學一覽》,1931年,323頁;《話說老協和》,1987年,479頁),后者在1933年秋從北京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話說老協和》,1987年,482頁),因協和與燕大有長期合作,培養的醫生和護士大都先在燕大讀理學科,故1933年燕大發行的《燕京報》中尚有理四江兆艾同學的記錄(見《燕京報》1933年5月1日、12日第一版);究竟是誰在照顧“小三”胡思杜,筆者亦不能確定,但更趨向于江兆艾,因為她出身護士專業,具備在病房應對猩紅熱這類傳染病的實操能力,而江兆菊的專長似在婦幼助產方面,且不晚于1934年初即南下到“中央”醫院任職(見《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職員錄》,1934年1月,25頁)。
最后,胡適先生日記中雖無胡思杜患猩紅熱的明確記述,但1934年8月30日提到“帶小三去協和驗身體,醫生(Dr. Hall)說他可以進學校了,但不宜做猛烈的運動”(見《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2004年,138頁)。這位醫生的全名是Dr. G. A. M. Hall,與胡適先生亦是舊識(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2004年,630頁),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執掌北平結核病防治中心(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p.120),對治療同為呼吸道傳染病的猩紅熱應有絕對權威,此次就醫或許是胡思杜愈后的最終復診。
(二)
承蒙幾位前輩學者照拂,筆者有幸從臺灣得到一批有關袁同禮先生的檔案資料,其中一通書信為1950年5月20日所作,亦藏于胡適紀念館。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日前奉到十五日賜書,諸承指示,至為心感。此間所藏英國皇家學會N. C. B.學報適有數期為他人借去,無法檢閱。又Zucker及Franke所譯之文尚未覓到,俟日后查明再行補入。茲先將近日搜集之論文簡目隨函奉上,即乞鈞閱。至于Hoffman所譯之“四十自述”系分期刊載,似未全譯,而該期刊亦在第二次大戰時停刊,一俟查明其住址,當與之通訊一詢也。關于編輯專集事,先生未免謙虛,敝意仍主張印甲乙兩集,仍祈考慮。檢閱各方志目錄,光緒三年鄞縣志系最后所編印,以后并無續修之本。普仁斯敦事是一極大榮譽,將來如能打開一條路,亦一大收獲,于中美文化促進貢獻極大。內人聞尊夫人已抵香港,甚為欣慰,盼不久可以覓到妥便。昨史語所何君(北大畢業)見告,孟麟先生不久可以來美,如能同船來美,實一好伴也。專此,敬頌
著祺
同禮 拜啟
五月二十日
《胡適中文書信集》第四冊收錄了一封標注為1950年5月致袁同禮函(31-33頁)。將其與上信對照互見,不難發現其中所談內容完全匹配,如Hoffmann所譯《四十自述》《鄞縣志》版本問題、普林(仁)斯頓葛斯德圖書館延攬館長等事,也無中間再有它信往來的可能,據此斷定書信集中胡適先生的信寫于5月15日,而僅標為5月的方式就略顯不妥了,尤其考慮到胡適紀念館同時藏有這兩份書札。
補語
筆者草就此稿后,突然收到西泠印社陸先生寄贈的2018年秋拍圖錄,其中“中外名人手跡暨戊戌變法120周年紀念專場”上拍了胡適先生致孫壯(字伯恒)先生五封書札,這著實令人驚嘆!孫先生不僅長期執掌商務印書館北京事務,更是活躍在清末民國學術、文化界,但事跡和學問至今不得彰顯,其稿本“商逸日記”除《張元濟年譜長編》(2011年)略加引用,一直秘不示人,世間凡有只言片語均可視為稀見史料,何況是胡適先生的書札呢!
回歸正題,“全集”古難全,不必過分苛求,倘若學界中人都能為胡適先生的集子盡一份心力,即便先生的墓木已拱,卻仍未遠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