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世界與你的彼岸——讀《出西藏記》
來源:文藝報 | 谷禾 2017年12月25日0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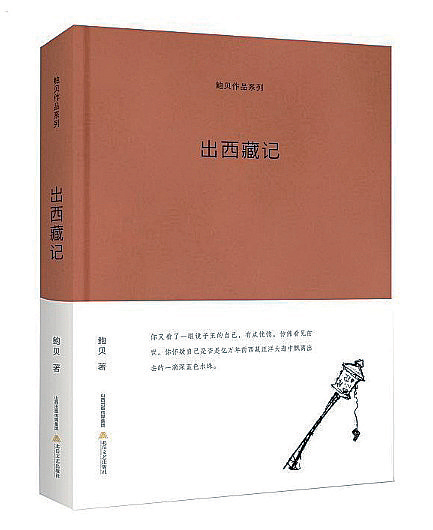
拿到《出西藏記》這個小說,第一眼讓我想到了《圣經》中的“出埃及記”。但一口氣讀完整部作品,我發現作家鮑貝并沒有約定俗成地把《出西藏記》寫成人類的某個族群被上帝救贖或者施誡、彌漫著強烈宗教氣息的故事,或者對她心中的雪域高原進行重構,而是通過幾個人物對自己信仰的沉迷與背叛,以及他們更加世俗和紛亂的生活狀態的呈現,把作家的思考有意無意地轉向了去探討和厘清宗教和人心的復雜糾葛上去了。對大眾心目中略帶神秘的雪域高原和更神秘的藏傳佛教,鮑貝既沒有去圣化它,也不曾矮化它(我不知道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有哪一片不被圣化或矮化的凈土還能保持著它處女的純凈)。雪域高原只是鮑貝精心設置的一個供他筆下的人物活動的場在而已,《出西藏記》所致力于書寫的依然是被作家洞悉的世道和人心。這也證明了,小說作為古老而現代的藝術形式,作家所呈現的個體作品不管如何翻新花樣,其內核仍然在亙古如常地傳達著他對生活和現實本身的還原、發現、思考和重構。也唯此,作家才有了一代代薪火相傳地寫下去的勇氣和光榮。
很久以來,諸如作家為什么寫作、寫什么和怎樣寫的問題,一直屢受問詢和質疑。拿這個問題去問許多作家,得到的答案也五花八門。是的,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作家對文學書寫的固執堅守似乎越來越不合時宜。我記得有人回答說:“寫作是為了讓自己更自由的呼吸。”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更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在這個時代,寫作是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人的最重要的途徑。”聯想一下伊凡·克里瑪所處的時代,我能理解作家的言外之言和意外之意。盡管我們已經遠離了那個時代,但事實上,作家總要通過自己構思的故事告訴讀者一點什么,他為藝術的勞動才有時代的價值和意義。
退一步說,我沒見過哪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會因為自己構思或者書寫了一個多么精彩的、迥異于其他講述者的故事而得意揚揚。作家的責任更在于要創造一個與現實世界息息相通的藝術世界,亦或有意識地、自覺地去厘清 “人和他人的關系,人和世界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鐵凝語)場景、故事、命運等元素毫無例外是構成一部小說的主要部件,但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系”的確立,才能使其交融成為一個藝術的個體,作家鐵凝由此還提出了“對‘關系’的獨特發現是小說獲得獨特價值的有效途徑”的寫作主張。
從這一維度考量《出西藏記》,我們可以嘗試著分析一下幾個人物之間的關系。
第一個人物:“你”。盡管讀完《出西藏記》,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某種神秘氣息一直籠罩著的白馬旺姆,但專業的讀者一定會覺察到,“你”才是《出西藏記》的主人公。因為“你”到拉薩的來去,才有了在不同的節點“你”與粉墨登場的白馬旺姆、索朗頓珠、牛魔王等各色人物的相遇;因為“你”到拉薩的多次來去,才與白馬旺姆之間產生了那種相互欣賞、理解又相互防范的復雜微妙的關系,才有了與牛魔王的相識;因了牛魔王的牽線搭橋和信譽擔保,又有了對所謂的企業家、唐卡大師索朗頓珠的輕信,不自覺地走進了他們預設的投資騙局,成為了和白馬旺姆一樣的受害者;更多次的往返中,“你”漸漸明晰了幾個人之間糾纏不清的復雜關系,他們各自晦暗而神秘的生活狀態,以及由這種復雜關系和他們與世界的關系所構建的世俗的拉薩。無休無止的扯皮官司,把“你”折磨得筋疲力盡,讓你在放下和執念之間徘徊和糾結,最終不得不通過一次置生死于度外的對岡仁波齊的朝圣,才完成了自我的救贖和靈魂洗禮。這一次的朝圣,并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對白馬旺姆的承諾,更是一次自我的置之絕境而后生。作家似乎無意呈現“你”的完整的生活。換句話說,“你”的階段式的故事,仍然只是“你”在作家講述《出西藏記》的時候所帶出的零星碎片而已。小說呈現了這一方面,而忽略了她的全部生活(盡管“出藏”“入藏”并非“你”全部的生活),既有敘述的限制,更因為“你”已經徹底陷進這種煩擾而不可自拔,生活的另一面不知不覺被徹底遮蔽的合理性。“你”從白馬旺姆、索朗頓珠、牛魔王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純潔無瑕的雪域高原,而是等同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欲望膨脹的世界,他們各自呈現了人性中最真實的一部分,保留了人性中的善與惡、丑陋與美好。說到底,拉薩也好,宗教也好,作為夢想和信仰總是完美的,不完美的是真實存在的和人性本身。在我看來,作家鮑貝開始似乎沒把“你”刻意塑造為小說的主人公,“你”只是勾連起小說中其他幾個人物命運的引線,是“你”自己半道兒站出來,出乎作家意料地成了《出西藏記》這惟一的主人公。我以為,對小說家來說,這樣的結果并不尷尬,因為恰恰在大多數時候,并非是作家在寫他小說中的人物,而是小說中的人物在寫著作家,并且一如既往地把控著作家對小說人物命運的把控。
第二個人物:白馬旺姆。從白馬旺姆在拉薩機場候機大廳意外出現,到和“你”成為相互欣賞的朋友,到一路陪伴、勸誘、說服和引領,直至消失。既是一個真實書寫于《出西藏記》中的白馬旺姆,也一直作為一面鏡子存在著,“你”從鏡子中看到的白馬旺姆,也許就是心靈的另一個自己。在“你”的講述里,她令人不解地“把自己變成了一棵樹,從香艷繁華的故土大上海連根拔起,移栽到了拉薩圣城,一邊經營她的文化公司,一邊游走于藏地的各個角落”。白馬旺姆漂亮而優雅,讓所有的人一見傾心。她有自己的上師,堅持晨跑,定時練瑜伽,泡溫泉,喝茶,食用最正宗的蟲草,虔誠地轉八角街或者布達拉宮。用她自己的話說,“下定決心離開前夫,離開上海,移居拉薩,就是因為她已不再想取悅于任何人,不希望自己再次被愛。她只想在這座空氣稀薄的城市獨善其身。就像一朵花和任何一種植物那樣,存在于這個世界,自美自足,自生自滅。”一切似乎都在確證,白馬旺姆所追求并正在享受的正是這樣不受羈絆的心靈自由,一種被信仰所洗滌的、半隱居狀態的理想生活。但隨著以“你”被騙為線索的故事作為載體被剝絲抽繭,真相也漸漸大白于“你”眼前——白馬旺姆不但也是一個和“你”一樣的索朗頓珠詐騙案的受害人,還是一個晚期乳腺癌患者。事業的挫折和肉體的病痛已經擊潰了她,讓她作為一個失敗者轉而求助于宗教和信仰,越來越堅持“頭頂三尺有神靈,人在做,天在看”“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等等,為今生的遭際感到罪孽深重,祈禱通過這樣的“移栽”求得超脫和慰藉,寄美好于虛幻的來生,最終把生命也交給了岡仁波齊圣山。每一個人的信仰都應該得到尊重,但信仰的力量并非是無止境的。在此,我無意于腹誹白馬旺姆對信仰的癡迷堅守,但“你”卻從她的命運和遭際隱約看到了未來,幡然醒悟,毅然離開了心中的圣城,回到了出發的地方。這樣的結局本身就是白馬旺姆的又一次失敗。至此,我們抬頭打量身邊的時候,能看到更多人身上何嘗沒有白馬旺姆的影子。白馬旺姆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她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每個人的認慫和對命運的屈從。那么,由她所引出的關系通達了我們每一個人。可以說,《出西藏記》的幾個人物里,白馬旺姆著墨最多,形象也最為豐滿和典型。她有特殊性,也兼具了普遍的意義。
相較而言,作家對索朗頓珠和牛魔王兩個人物就顯得陌生和不夠游刃有余。這兩人只是演技拙劣的騙子而已,根本不是什么企業家、唐卡大師、裕固族昔日王爺。弄清真相的白馬旺姆一針見血地揭開了其畫皮:“索朗頓珠是個身份非常復雜又吊詭的人物,而且他的人生也是復雜而吊詭的。他做過喇嘛,還俗后與人結婚,生子,離開牧區到拉薩創業,和妻子離異,他賺過錢,也虧過錢,救過人,也坑過人,當過董事長,也做過騙子,被抓進去坐過牢,又突然被放了出來,現在繼續當他的董事長,繼續挖坑,繼續騙人錢財。”兩人像魔鬼的分體,在現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配合相得益彰。他們拙劣的騙術之所以屢屢成功,就在于巧妙地抓住了內地人被雪山、藍天、白云、喇嘛廟、使徒的虔誠所震撼、凈化后內心所滋生的天真和對從前的生活方式的短暫懷疑,給畫出了一張伸手可觸的燦爛的大餅,從而騙取了他們對西藏那篇圣土的信任。等你發現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回到小說對藝術性的探討上來。我們會發現,“你”的西藏,并非只有純凈的雪山、藍天、碧水、白云、喇嘛廟,更涵蓋了形形色色的白馬旺姆這樣的信徒,索朗頓珠、牛魔王這樣的騙子,“你”,以及由他們外延的更多他人所構成的人與世界的關系。這才是一個完整的西藏。作家通過對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多重關系的展示、呈現和書寫,讓《出西藏記》有了文學和社會的雙重價值和意義。所以我們說,在小說寫作上,“題材”從來就是一個偽命題,作家是否通過他的書寫揭示出了世界存在的真相,多大程度上抵達了人性的真實,才是我們更應該看重和思考的。
《出西藏記》的敘述視角也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在談及小說的敘述空間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巴爾·加斯略薩曾經這樣說:“敘述者是任何長篇小說(毫無例外)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其他人物都取決于他的存在。敘述者永遠是一個編造出來的人物,虛構出來的角色。與敘述者‘講述’出來的其他人物是一樣的,但遠比其他人物更重要,因為其他人物能否讓我們接受他們的道理,讓我們覺得他們是玩偶或者滑稽角色,就取決于敘事者的行為方式——或表現或隱藏,或急或慢,或明說或回避,或饒舌或節制,或嬉戲或嚴肅。敘述者的行為對于一個故事內部的連貫性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而連貫性是故事具有說服力的關鍵因素。小說作者應該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誰來講故事?’”巴爾加斯·略薩這段話的重要性在于向我們廓清了敘述人的確立和敘述視角的有效運用才是一個小說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
從敘述視角方面來考察《出西藏記》,我們能看到,這個小說選擇了最具難度的“第二人稱”“你”作為惟一的敘述視角,并且這個人物既是小說的主人公、故事的參與者,又是故事的敘述者。我們說任何小說當然都存在一個敘事空間和敘事者空間,兩者之間的關系被敘事學研究者稱之為“空間視角”,在“第二人稱”的敘事空間里,敘述者不再是一個無所不知的上帝,而變得褊狹和逼仄,閃轉騰挪起來異常困難。我曾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第二人稱”敘事最直接的好處是便于抒情,而非揭示故事的真相,但抒情恰恰是小說不可忽視的敵人之一,它甚至某種程度地疏離和抵制著作家的敘述,讓后者變得模糊、曖昧和混亂,直至被遮蔽。所以使用“第二人稱敘事”就如同在刀尖上跳舞,作家往往不能自已地越界,混淆作者和敘事人的界限,從而讓小說偏離了它必須直接面對的真實。當然,“第二人稱”敘事更容易讓讀者在閱讀中生發角色的轉換,從而更直接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和用心。《出西藏記》的可嘉許之處在于鮑貝一直保持著敘述的小心翼翼而不越雷池。她通過“你”同各個人物的巧遇(當然,作為同行,我更希望這種巧遇是一種必然而非偶然)來推進故事的有效進程,通過視聽來補充和完成因果的轉換,一步一步地構建起了屬于《出西藏記》的小說倫理。只有當她的主人公甩脫了所有羈絆,獨自朝向岡仁波齊海拔5700米埡口、朝向死亡攀登的時候,鮑貝的敘述才游刃有余地進入了忘我的境界。在這里,敘事者和主人公合而為一,不再受到任何干擾,作家的敘述也變得專注而酣暢淋漓。當“你”終于望見了繁星似雪的蔚藍蒼穹,“一路走來,所有的勇氣、墮落、痛苦、追求、情愛、希望、怨恨、抗爭,與種種放不下的情結,皆在剎那間破滅消散。一切所執的事物,都不過‘唯是夢幻’的力量。與你相遇的,竟是一場幻化般的‘緣覺’。所有的轉山轉水,最終低達的皆是幻覺般的‘菩薩地’。”小說的敘述也抵達高潮:“你”終于頓悟,反身離開了岡仁波齊,離開了似乎永遠走不出的西藏。也讓《出西藏記》得以誕生。
(《出西藏記》,鮑貝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