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凱長篇小說《導彈和向日葵》: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
來源:文藝報 | 傅逸塵 2017年12月11日0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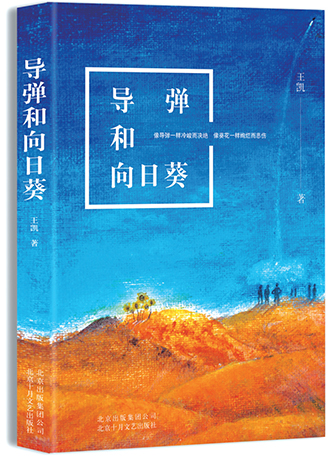
“疼痛,是生命最為敏銳的感覺,也是王凱小說最有魅力的美學質素。這疼痛關乎世俗、欲望,關乎愛情、成長,最終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
我們的文學應該從狹窄的個人視域和封閉的內心世界走出來了,應該以一種客觀的態度面對豐富駁雜的外部世界。”
一
讀王凱的小說,常會感覺到疼痛。那是一種從青年時代綿延而來的成長的痛感,夾雜著生命的青澀和稚拙,裹挾著大漠的荒涼與粗糲,似挽歌般傳遞著軍人的理想與執著。從軍校到沙漠,從機關到連隊,王凱小說的生活幅面相對固定,人物大都似曾相識,故事也談不上有多復雜,反復書寫的就是部隊基層的日常生活和青年軍人的生命情態。
長篇小說新作《導彈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9月版)中,葉春風、鐘軍、車紅旗、蘭甘、白雪歌……這些青年軍人的成長故事又一次擊中了我。現實生活磨煉、砥礪著年輕的生命,雖談不上苦難,卻充斥著無奈與壓抑、欲望和沉淪。眼看著青春的激情、鋒芒乃至生命本身一點點遁入大漠深處,消弭無形,你不得不服膺命運的邏輯,為富于痛感的生存經驗喟嘆、感傷。疼痛,是生命最為敏銳的感覺,也是王凱小說最有魅力的美學質素。這疼痛關乎世俗、欲望,關乎愛情、成長,最終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小說的結尾宛若寓言般,綻放出燦爛奪目的精神光芒。始終葆有赤子之心的葉春風,終于跳脫了世俗欲望的羈絆,穿越了幽深的時光隧道,闖入一片充盈著理想情懷和英雄主義的精神荒原——似重獲新生般,打量著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沙漠,腦際陷入一片輕盈的迷惑。王凱以一種極富象征色彩的抒情筆調,回望疼痛纏繞的軍旅青春,在生命的自我省察中描摹出軍人靈魂的面影。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報之以歌。”泰戈爾在《園丁集》中更多地融入了青春時代的體驗,細膩描敘了愛情的幸福、煩惱與憂傷,成就了一部青春戀歌和生命贊歌。王凱的《導彈和向日葵》又何嘗不是呢?他深諳部隊生活的現實種種,以辛辣而又戲謔的筆調,真實生動地揭露出過往軍隊內部存在的不堪和暗面,將部隊領導、機關干部、連隊官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得窮形盡相。尤其是將外部世界對個體生命的威壓和規訓書寫得細致入微,令人感同身受。然而,王凱并沒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而是將尖銳的痛感轉化為寬廣、堅韌、通透的人生態度;他的文字充盈著厚重的現實經驗和超拔的哲學思辨,似歌者般吟唱著軍旅生活宏闊遼遠、高蹈正大之氣象。
二
當下青年作家的寫實能力漸趨下降。大家似乎過于依賴觀念和想象寫作,能夠細致入微地再現某種場景、生動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實在太少了。在一個主觀傾向占上風的文學時代,我們通常很難讀到像生活一樣真實、鮮活、飽滿的客觀性作品。但在《導彈和向日葵》中,我們不僅能讀到對沙漠天氣、風物及環境的精確、優美的描寫,還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的外貌、行動、言談和性格,連同他們微妙復雜的內心世界也同樣精確而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如果說,小說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現深刻的主題內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那么,追求小說真正意義上的客觀性效果就難上加難。要寫出客觀性的作品,需要作者花費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夠的耐心進行認真的觀察、冷靜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斷。
小說虛構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詭異、奇特,最后都必須服從生活經驗邏輯和內心情感邏輯的制約。就像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那樣:“不管小說是多么胡說八道,它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經驗之中,從中吸取營養,又滋養著人們的經驗。”小說家若想更逼真地還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華和造作,就必須對鮮活真實的世界充滿敬意,就必須具有樸素誠懇的情感態度。王凱對巴丹吉林沙漠深處的軍營、對自己同代人的軍旅青春都懷有深深的敬意和濃厚的興趣。他秉持一種理性而扎實的客觀態度,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現實生活,更細致、更真實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筆下的軍旅生活,具象而沉實、細膩且綿密。對于小說中的人物,不管地位高低,無論正面反面,王凱都懷有一種深沉的情感——悲憫與誠摯的愛。正是這種悲憫的情懷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得那些遠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如車紅旗、蘭甘、曹助理、凌科長、白雪歌等等,雖然有著道德、性格、或行為上的缺陷和瑕疵,依然會在某一時刻流露出質樸、善意與誠摯的一面。正是基于對現實經驗的熟悉,王凱沒有拘泥于表淺的日常事象,更不愿做出廉價而淺薄的價值判斷。他選擇沉潛入現實生活的深層肌理,再反身而出,試圖以一種跳脫和超越的視角賦予現實生活以一種整體性的觀感,對人物的現實遭際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小說主人公葉春風,盡管在很多事情上表現出幼稚與迷茫,但內心深處純粹、清高,有著濃烈的英雄情結,而且能一以貫之地堅守,不因境遇的改變而令心靈蒙塵;在經受了種種潛規則和世俗欲望的考驗之后,依然不失赤子之心,最終收獲了精神的成長和靈魂的超越。王凱在故事層面進行批判和思辨,而在人物身上寄寓激情和理想,這正是小說動人之處、價值所在。
當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說敘事中,總是顯示出一種簡單和片面的傾向:每每將一種情感結構推向極端,而缺乏在復雜的視境中平衡地處理多種對立關系的能力。《導彈和向日葵》則始終是在復雜的網絡中展開矛盾沖突和情感糾葛。葉春風和他的軍校同學們之間、同學與同學之間、機關層面的橫向聯系、與基層的縱向關系,凡此種種構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故事的推進和人物的成長都需要在這重重交叉的網絡邏輯中才能實現。而軍營和沙漠宛若龐然巨物,矗立在小說的景深處。冰冷、沉默,悄無聲息地吞噬著周遭的生命,也消耗著內部的能量。小說人物如同陷入了一個巨大的磁場,不管如何逃離,怎樣回避,終究逃不開這無物之陣的籠罩。王凱洞悉外部世界對個體生命的影響和改寫,并將這一過程書寫得纖毫畢露、驚心動魄。的確,我們的文學應該從狹窄的個人視域和封閉的內心世界走出來了,應該以一種客觀的態度面對豐富駁雜的外部世界。客觀性不僅意味著人物形象的精確和真實,更意味著寫作倫理的強健和美學精神的開闊。
三
一部偉大的小說之所以不朽,首先是因為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但是塑造不出令人印象深刻、經得起反復言說的人物形象,恰恰是現代小說的一大危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小說最嚴重的病象正是經典人物形象的缺失。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作家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熟悉、是否充滿理解、悲憫和愛意。
在《導彈和向日葵》中,葉春風、羅慕、白雪歌、車紅旗、蘭甘、鐘軍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王凱循著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觀念,著力“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于生活的流態中寫盡了上一個時代軍隊的重重積弊,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軍人心中的無奈與苦澀。葉春風這個人物就是千千萬萬基層帶兵人的代表,他們有文化、有理想、也有拼搏奮斗的志向。然而,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艱難的政治生態中,葉春風和他的同學們盡管拼盡全力、左支右拙、心力交瘁,卻依然難以實現自身的抱負與理想,只能為了現實利益、仕途進步甚至愛情婚姻而委曲求全、互相傾軋、遍體鱗傷。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軍營中,愛情無疑是一種奢侈品,是年輕軍人們賴以確證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象征。小說中的愛情書寫,作為一條重要線索貫穿全篇,令人唏噓、震撼。在艱辛與孤寂中,愛情既可以彼此溫暖、撫慰;也可以作為一種稀缺的商品,交換世俗的利益;更可以被多舛的命運玩弄于股掌間,暴露生命的卑微和人性的丑陋。女性人物盡管依然不是王凱小說的重點,但是白雪歌這個人物寫得尤為精彩。小說結尾處,這個看似心機深重、行為放蕩的女孩終于表露出她真實、純粹的心靈內面。種種委屈和隱忍、生命的沉重和背負一起涌上心頭。
性與愛在王凱的敘事中都是置于前景的符碼,勾連著身體與靈魂,也對抗消解著人際關系的殘酷和生活的困窘艱辛。葉春風骨子里透出的清高和孤傲,顯示出在殘酷的世俗存在中,個體生命所能保存的選擇生活道路和命運歸宿的最后權力。理想和現實間的巨大落差,構成了悲劇性的審美氛圍。人性的深度、生活的可能、命運的波折、人物的形象,都在悲劇性的故事中次第浮現。青春漸逝,生命豐盈,過往那個積弊累累、充滿矛盾與抵牾的時代原來不過是一個飽蘸人生況味的符號。盡管自己就身處這個“命運共同體”中間,王凱描摹時代變遷和命運嬗變的筆法依然冷峻、犀利,以一種寓言化的寫作倫理傳遞出思辨性的精神力量。
四
疑難、反抗和救贖是《導彈和向日葵》核心的精神價值。王凱在極其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察人物的內心和情感,沒有對外部世界的激烈批判,有的是沉靜深邃的靈魂自省。因為悲憫而理解,因為思辨而救贖。
“瀚海”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不僅描述出沙漠的本質,更勾連著遼遠而寬廣的外部世界。沙漠如海般壯闊,而人物的命運就如同巴丹吉林沙漠深處的弱水,蜿蜒流過干渴、粗糲的河床。堅韌和嚴酷、逼仄和遼闊,諸多反義詞構成的沙漠存在與海洋的意象遭遇,顯得尤為意味深長。
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在小說中,王凱以詩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筆調顯示出作家的理性認識、情感態度和道德立場。他不僅描寫現實,而且解釋現實,不僅傳遞經驗,而且超越經驗。《導彈和向日葵》作為王凱青春疼痛敘事的集大成之作,終于跳脫了狹窄庸常的底層視角,達至開闊遼遠的文學氣象。
■創作談
我希望自己是真誠的
王凱
我從小在戈壁灘上的空軍基地長大,軍校畢業后又回到那里,從技術員到排長,從連隊指導員到宣傳科干事,從少尉到少校,直到快30歲時才離開。那時我很想離開基地,盡管我很愛戈壁灘夜空中的星河。作為一個穿著軍裝的凡夫俗子,我覺得我應該有一個比戈壁灘更像樣點兒的安身立命之處,然而等我真的離開以后,卻又不能不時時懷想。如今我已經在城市生活了不短的年頭,但我基本沒寫過城市的生活。我始終覺得我與城市是隔膜的,城市夜空的星星永遠與燈火成反比。內心里,我更愿意把自己當成一個駐守大漠的軍人,也許只有把自己放置于那一片蠻荒之地,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軍人的價值乃至于人的價值。所以直到今天,我寫的仍舊是漠風永不止息的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沙漠,而《導彈和向日葵》就是其中最耗費我心力的一篇。
這個題目和小說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一樣,都來自我喜歡的唐詩《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只是有的換了一些同音字,好讓它們看上去更像一個名字,有的則原封未動,比如小說中的“白雪歌”。因為這首詩,讓我覺得小說里的人物都有了某個確切的出處,也仿佛給了我一個寫作征途上的立足點。在我看來,岑參這首詩和很多邊塞詩不同,既有嚴寒也有熱血,既有悲愴也有雄渾,詩句摻雜著許多莫可名狀的復雜心緒,而不僅是通常所見的激昂或者傷感。所以寫作時,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說能有一點這樣蒼茫又細膩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說能更充分地表達出軍人內心豐富的情感。
這個小說中的很多生活細節是我親身經歷的,比如我軍校畢業剛分到基地時,就曾跟著老兵學習地空導彈燃料加注專業,那時我對加注車上的閥門和管道毫無興趣,盛夏戴著防毒面具訓練時憋屈的感覺宛如昨天,鼻翼間似乎還留存著導彈燃料極其特別的味道,所有這一切都被我寫進了小說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在小說中寫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說,寫出了諸多自己的一個。但又不止于此。因為我想寫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我們一代軍人的生活。在我看來,遼闊的戈壁大漠不僅是最好的武器靶場和戰術演訓場,同樣也是絕佳的文學現場和心靈試驗場,把年輕的男女軍人們放在此地,也許才能更清晰地展現他們的抉擇與放棄,才能更尖銳地呈現他們的歡樂與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現他們的相聚與別離,也才能讓讀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視的軍營世界與迷彩般斑駁的軍人內心。我試圖在這部小說里探究年輕軍人是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實現精神成長,如何在時光和風沙的磨礪中尋找到生活意義,如何在不為人知的所在中堅守職責,這聽上去可能有點老生常談,但我想,這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都面臨的找尋與追問。
當然,一切的前提是我得在寫作中做到盡可能的真誠,我不確定自己做到了何種程度,畢竟這是個無法量化的指標。所以我寫作的時候,總是會停下來問自己,你寫的這些你到底信不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繼續;如果不是,那就再想想應該怎么寫。無論如何,我希望自己是真誠的,也努力把真誠注入筆下的人物,至少能讓我自己相信,他們或許真的就生活在沙漠中的某處。正如托爾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的結尾中所言:“這個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熱愛的。我要把他的美盡量完善地表達出來,因為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他永遠都是美的。這英雄不是別的,就是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