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民族文藝 >> 人物訪談 >> 正文
從滿族視角到中華文化眼光
——對(duì)話《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作者關(guān)紀(jì)新
http://www.fxjt168.com 2014年07月04日10:52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明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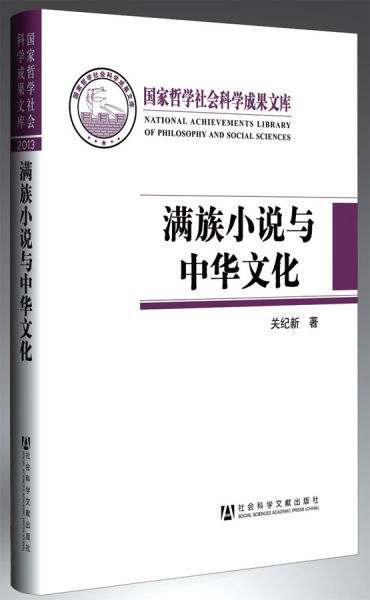
日前,由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聯(lián)合主辦了“《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出版座談會(huì)”。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的最終成果,該書2014年4月由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出版,列入“國家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成果文庫”。在出版座談會(huì)上,數(shù)位專家學(xué)者對(duì)該著作的學(xué)術(shù)成就給予了肯定,認(rèn)為它體現(xiàn)了作者多年來潛心致力滿族文學(xué)及文化研究的豐厚積累和深刻思考,從特有民族的個(gè)性文化視角出發(fā),參照滿族傳統(tǒng)藝術(shù)訴求與中華文化整體背景,對(duì)古今諸多滿族小說家及其作品予以深度剖析,尤其是在《紅樓夢(mèng)》和老舍作品等方面提供了諸多新鮮闡釋,凸顯出獨(dú)到的人文眼光和扎實(shí)的學(xué)術(shù)功力,對(duì)當(dāng)代多民族文學(xué)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示范效應(yīng)。
滿族學(xué)人關(guān)紀(jì)新是滿族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專家、中國多民族文學(xué)理論評(píng)論家,曾任《民族文學(xué)研究》主編,兼任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老舍研究會(huì)會(huì)長、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huì)理事,出版有專著多種,并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和文學(xué)批評(píng)逾百篇。圍繞這本書及相關(guān)領(lǐng)域,記者與關(guān)紀(jì)新展開了有關(guān)滿族文學(xué)與文化的對(duì)話。
記 者:您進(jìn)行滿族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已經(jīng)30多年,但我們知道,“滿族文學(xué)”這個(gè)概念以前就常常受到質(zhì)疑,您對(duì)滿族歷史文化及其文學(xué)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關(guān)紀(jì)新:因?yàn)椤拔母铩钡纫蛩兀疫M(jìn)入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時(shí)已過而立之年。我是滿族人,深深體會(huì)到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積淀特別豐富,但實(shí)際上,從事相關(guān)研究的人卻不多,具體到治滿族文學(xué)者就更少。正如你所說,“滿族文學(xué)”甚至連概念都常常受到質(zhì)疑,滿族作家多用漢文來書寫,要討論它,有時(shí)容易被看成是“偽學(xué)”。
我國自古以來的少數(shù)民族太多了,可是像滿族這樣自一出現(xiàn),便須全方位思考和處理與漢族文化關(guān)系的民族,卻不多見。一部滿族書面文學(xué)史,就是滿族書寫者們?cè)谖膶W(xué)道路上如何學(xué)習(xí)和汲取對(duì)方、同時(shí)又如何尋找和守望自我的歷史步態(tài)。滿族以及滿族文學(xué)從問世起,便跟漢民族緊密相連,貼近到了耳鬢廝磨的程度。故而,我們有必要隨時(shí)提示自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平常看待其他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眼光和方式來看待滿族的文學(xué)。
記 者:滿族作家多用漢語言寫作,在您看來,對(duì)滿族文學(xué)有什么樣的影響?
關(guān)紀(jì)新:依據(jù)人們的習(xí)慣思維,一個(gè)民族的書面文學(xué),就該是這個(gè)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寫下的作品。可是呢,凡事也總會(huì)有個(gè)常態(tài)與非常態(tài)的差異。事物溢出于常態(tài)軌道而以這樣那樣的非常態(tài)面目顯現(xiàn),既在理論層面可以理解,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也不難發(fā)現(xiàn)。滿洲民族17世紀(jì)中期隨清政權(quán)進(jìn)關(guān),身處漢民族文化的汪洋之中,逐漸乖離母語乃是歷史定數(shù)。但是啟用他民族的語言文字,并不意味著自我文化的一了百了。滿族的“精怪”之處恰恰在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還在傳統(tǒng)漢文化的堡壘里翻云覆雨地干了些個(gè)大事情。納蘭性德詞、《紅樓夢(mèng)》《兒女英雄傳》等小說、老舍等滿族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的作品、國粹京戲……都是滿人被世間認(rèn)定“漢化”后的非常作為。滿族文學(xué)即便是用漢文寫就,也呈現(xiàn)出來天然、質(zhì)樸、曉暢、平易、詼諧、口語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賞的風(fēng)格,成為了現(xiàn)當(dāng)代“京味兒文學(xué)”的基本來源。以為少數(shù)民族一旦轉(zhuǎn)用漢族語言文字,就在文化上完全否定自我的說法,不大合適。世界上以及我們國內(nèi)多民族文學(xué)的交往史,都說明這一點(diǎn)。
記 者:這樣看來,滿族小說的確特別值得研究,那滿族小說的以往研究情況如何?
關(guān)紀(jì)新:滿族的小說,包括清代滿族作家的小說作品和20世紀(jì)以來滿族作家的小說作品,是一筆在中華文化史上引人關(guān)注的文化遺產(chǎn)。以往雖然也有研究者對(duì)曹雪芹之《紅樓夢(mèng)》、文康之《兒女英雄傳》、老舍之系列小說等文學(xué)資料,做過專門的研究,但將各個(gè)時(shí)代滿族作家及其小說作品,作為一個(gè)民族特有的文化遺產(chǎn)和文化現(xiàn)象來加以總體觀照,還不曾有過。從前,學(xué)界大多止步于對(duì)滿族這個(gè)民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力的即興贊嘆,至于如何將滿族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顯示的總體業(yè)績,與滿族歷史上的民族文化大規(guī)模流變相聯(lián)系,來加以縱深考量,與滿族曾經(jīng)普遍接受中原漢族文化而又注意葆有自己的審美特征相聯(lián)系,來加以科學(xué)探究,其工作則是相當(dāng)匱乏的。
記 者:那對(duì)于“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這個(gè)課題,您采用了什么方式來研究?
關(guān)紀(jì)新:我知道,圍繞“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這樣人們陌生的題目,方方面面疑問甚多。要有效作答,顯然不能僅憑現(xiàn)有歷史與文學(xué)理論教科書上的路子來泛泛立論。我為自己設(shè)定的頭一個(gè)原則,就是既要把牢科學(xué)研究的普遍性與共性的尺度,也要著力尋取和依賴滿族文化自身發(fā)展的個(gè)性化視角,利用滿學(xué)學(xué)術(shù)窺鏡來觀察辨析滿族的文學(xué)問題。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夠?qū)M族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從過去撇開具體民族歷史文化的大而化之的研討中解放出來,去除遮蔽誤讀,防止隔靴搔癢,力戒指鹿為馬。為此,就得廣泛調(diào)動(dòng)歷史學(xué)、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政治學(xué)、民俗學(xué)、語言學(xué)、文藝美學(xué)、心理學(xué)、倫理學(xué)等多重學(xué)術(shù)范式和研究方法,還對(duì)象以真實(shí)。
記 者:在這本書的出版座談會(huì)上,聽到不止一位專家學(xué)者表示,原本對(duì)于把《紅樓夢(mèng)》說成滿族文學(xué)不以為然,讀了你的一系列詮釋覺得非常有道理。能不能以《紅樓夢(mèng)》為例子談一談?
關(guān)紀(jì)新:那就簡單說幾句我對(duì)《紅樓夢(mèng)》的理解吧。關(guān)于為什么把曹雪芹視作滿族作家,把《紅樓夢(mèng)》視作滿族文學(xué),需要費(fèi)時(shí)費(fèi)力來廓清,這里姑且不談了。我比照了滿洲民族精神文化傳統(tǒng)與滿人入關(guān)之后人文心理折沖的內(nèi)在軌跡后感到,《紅樓夢(mèng)》主題與多年來“紅學(xué)”專家們的結(jié)論不盡一致。《紅樓夢(mèng)》是源起于女媧補(bǔ)天剩下一塊石頭,結(jié)穴于這塊石頭去人世間“瀟灑并且痛苦地”走了一遭之所翻演摹錄出來的大型敘事。小說主人公賈寶玉,這塊來自于大荒山下的“頑石”/“靈石”,乃是被作者寓意塑造的、代表著滿洲民族元文化基準(zhǔn)內(nèi)涵的一個(gè)“喻體”,寶玉從離開大荒山投胎賈府,到復(fù)遁空門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歷,是在暗寫作者對(duì)于清初百年滿、漢之間社會(huì)文化折沖、互動(dòng)的心理感受。曹雪芹的寫作活動(dòng),懷著一個(gè)強(qiáng)烈的目的,即要世人都來認(rèn)識(shí)這烈火烹油般的“紅樓”賈府,與這“紅樓”賈府終歸殘“夢(mèng)”一枕的宿命。他用“既知今日,何必當(dāng)初”8個(gè)字,以及觸目驚心的《好了歌》,抽象出他的歷史文化體驗(yàn),向一個(gè)雖揚(yáng)帆百年卻有可能一朝擱淺的民族,鳴示出尖厲的警號(hào)。這種幻夢(mèng)般的宿命觀,是曹雪芹創(chuàng)作心理的核心。他為作品設(shè)計(jì)了多重寫作脈線,首先演繹了滿洲大家族的盛極而衰,其次又講述著令人憧憬的“木石前盟”毫無前途,再其次則是告訴讀者,包括大觀園里一切少女命運(yùn)的所有美好物約,到頭來都得毀滅,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徹頭徹尾的“懸崖撒手”敘事,是曹雪芹文化宿命創(chuàng)作心理的絕佳證明。他陷于一種根本性的無可排解的民族歷史文化幻滅感,將筆下所書各項(xiàng)悲劇線索彼此互構(gòu),皆由民族文化之折沖來解釋。于是,他追覓痛悔,反省徹悟……
記 者:在這本《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中,您所關(guān)注的內(nèi)容以什么為線索?
關(guān)紀(jì)新:《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的撰寫,首先面臨一個(gè)具體問題,這個(gè)于百年前一度息影于社會(huì)關(guān)注平臺(tái)的民族,對(duì)其歷史、文化、文學(xué),人們普遍缺乏了解,連學(xué)界也不例外。因此,我不能不首先離開話題中心,圍繞該民族的歷史際遇、文化變遷等,展開外圍的探尋和描繪。這是書中的“引言”部分。第一章對(duì)滿族文學(xué)全景進(jìn)行廣角掃描,說明滿族小說取得這樣的成就不是偶然現(xiàn)象,是該民族文學(xué)豐厚積淀之上所綻放的民族藝術(shù)奇葩。滿洲民族的小說書寫,與本民族其他門類的創(chuàng)作同步推進(jìn)并取得重大成就,恰恰是該民族整體文明程度較高的必然反映。
第二章首先給“滿族小說”概念以科學(xué)界定,認(rèn)為滿族小說是滿族作家感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之后進(jìn)行的書寫。他們用漢語進(jìn)行創(chuàng)作,但對(duì)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等有著清楚的認(rèn)定。這一章從康熙年間佟世思創(chuàng)作的《耳書》開始,依次評(píng)述了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慶蘭的《螢窗異草》、曹雪芹的《紅樓夢(mèng)》、西林太清的《紅樓夢(mèng)影》、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冷佛的《春阿氏》、松友梅的《小額》等滿族古代小說,一直論述到民國年間穆儒丐、老舍、王度廬、端木蕻良、舒群、李輝英、馬加、關(guān)沫南等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眾多滿族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通過如此梳理,可以得出一個(gè)結(jié)論,滿族歷來是盛產(chǎn)小說的民族。
第三章反觀培植滿族小說的民族民間文化土壤,指出滿人喜愛長篇敘事文學(xué)是由歷史深處帶過來的文化嗜好。研討滿族后來的書面文學(xué)尤其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到該民族民間傳承中,最具有自身特色和價(jià)值、最對(duì)該民族文化心理與精神態(tài)勢(shì)產(chǎn)生影響的,則當(dāng)推神話與“說部”。第四章論述滿族文學(xué)對(duì)于自我民族的精神文化、價(jià)值葆有和倫理型范所具備的天然承載責(zé)任,談及滿洲先民長久信奉原始宗教薩滿教,其親近自然、崇尚渾樸的思維理念對(duì)該民族傳統(tǒng)精神文化養(yǎng)成有著實(shí)難估量的意義和作用。類似薩滿教等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理念,在滿族小說創(chuàng)作中留下了深刻印痕。該章著重分析了《紅樓夢(mèng)》,由作品中暗自布排了很多滿洲元文化——薩滿教文化基因來看,曹雪芹的“既知今日,何必當(dāng)初”,并非只為了傾吐賈府的傷心往事,這位業(yè)已具備滿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達(dá)的是對(duì)于本民族進(jìn)關(guān)以來文化遭遇的辨思。薩滿教的文化精神,也在曹雪芹同時(shí)代作者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慶蘭的《螢窗異草》中,在民國初期穆儒丐的《福昭創(chuàng)業(yè)記》等小說里,都有展示。直至現(xiàn)代的滿族作家端木蕻良,薩滿教的文化精神,仍然被他表達(dá)得相當(dāng)濃烈。
第五章重點(diǎn)剖析滿族小說家對(duì)滄桑歷史、跌宕旅程、苦難人生的深切體察,他們寫出了飽含悲劇意蘊(yùn)的作品,從而形成凸顯悲憫情懷的滿族文學(xué)傳統(tǒng)。歷史對(duì)于人口寡少的滿民族來講,絕非只是榮耀和驕傲,本身所孕育的悲劇因素是多方面的。滿族文學(xué)家們沒有逃避自己的良知和責(zé)任,為那樣的時(shí)代和民族,留下了禍福之間相倚相生的悲喜描摹,留下了撞擊人心的悲劇備忘錄。滿族小說悲劇書寫居多,從曹雪芹的《紅樓夢(mèng)》到和邦額的《夜譚隨錄》,從冷佛的《春阿氏》到穆儒丐的《北京》《同名鴛鴦》、老舍的《駱駝祥子》《月牙兒》等等,悲涼之風(fēng)遍布其上。
第六章寫到,作為族別文學(xué)的特有展示,滿族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有著諸多的獨(dú)到提供,在中華多民族文壇上,構(gòu)成了與漢族以及各個(gè)兄弟民族作品在人物形象描繪上面的相異相輔,豐富了中華多民族文學(xué)的形象畫廊。和邦額刻畫的清中期京師旗人貧困家庭的人物,曹雪芹勾勒的寶玉、黛玉、寶釵、鳳姐、賈母等清代滿洲貴族階層人物群像,文康塑造的清代旗人老少男女,都展現(xiàn)出清代滿人特點(diǎn)。現(xiàn)代的滿族由于命運(yùn)變異,大多成員成為都市下層貧民大眾。出身于京旗社會(huì)的穆儒丐、老舍、王度廬等小說家,大量書寫這些處于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苦難同胞,將他們的形象鐫刻到中華文學(xué)的不朽人物畫廊之上。而遲至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滿族小說作者趙大年、朱春雨、葉廣芩等,繼續(xù)出色地摹寫著本民族的人物形象。第七章就滿族小說的語言風(fēng)格展開論述,滿族一代代的小說家將“京腔”、“京韻”等民族性語言天賦兌現(xiàn)到作品敘事中,為中華的文學(xué)與文明留下了富有價(jià)值的語言范本。第八章論及滿族小說的市井文化傾向,認(rèn)為平民世界的審美習(xí)尚、雅俗共賞的藝術(shù)追求、苦中含笑的幽默風(fēng)格,已經(jīng)構(gòu)成了滿族小說書寫中特殊的文化質(zhì)地,成為對(duì)傳統(tǒng)的中原文學(xué)“文以載道”原則的有效校正。
第九章講述歷代滿族小說家的北京情結(jié)及其在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投影——將京城的社會(huì)摹寫與民俗掃描結(jié)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北京是滿族的大本營與聚散中心,是他們的文化鄉(xiāng)土與精神故園。滿族文學(xué)家描畫北京和這座城市的一切,形成了傳統(tǒng)。第十章寫到,自我的歷史反思與文化反思,是滿族書面文學(xué)傳統(tǒng)及其流變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一部追悔過往的《紅樓夢(mèng)》,不單成了滿漢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動(dòng)摹本,更將參憑于歷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一舉激成洪波。自此,絞結(jié)于歷史、糾纏著文化的滿洲文壇后起之秀,在各自的時(shí)代,就此奉獻(xiàn)得愈來愈多。老舍在反思民族歷史教訓(xùn)方面有著格外重要的貢獻(xiàn),到了新世紀(jì),滿族小說界對(duì)民族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反思遠(yuǎn)未結(jié)束。
第十一章是本書的學(xué)術(shù)總結(jié),由兩個(gè)對(duì)應(yīng)的判斷組成,既充分肯定“離開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環(huán)境,滿族和它的一切既往文學(xué)績效,便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并明確指出滿族小說并不是“漢化”的產(chǎn)物,不是漢族文學(xué)的附麗物,其多方面獨(dú)到的個(gè)性化的藝術(shù)書寫,是對(duì)中華文化豐富與展開不可或缺的積極奉獻(xiàn),進(jìn)而完成了中華文化大格局下滿族小說的基本價(jià)值評(píng)估。
記 者:可以看出來,這本書完成的是中華文化大格局下滿族小說的基本價(jià)值評(píng)估,所以在研討會(huì)上,專家們認(rèn)為這本書的中華大文化的背景眼光特別突出。
關(guān)紀(jì)新:隨著種種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理念的深入人心,學(xué)界撇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存在而談?wù)撝袊膶W(xué),已經(jīng)不太可能和不合時(shí)宜了。中華多民族文學(xué)的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已然成為中國文學(xué)總體格局內(nèi)不可或缺的一個(gè)至關(guān)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創(chuàng)建并確立中華多民族文學(xué)史觀的任務(wù),歷史性地落在了當(dāng)代學(xué)人們的肩頭。這既是我們文學(xué)研究界的當(dāng)務(wù)之急,又是一項(xiàng)可能需要通過比較長久的努力才能達(dá)到的目標(biāo)。
網(wǎng)友評(píng)論
專 題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luò)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