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藝術家訪談 >> 正文
闡釋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歷程
http://www.fxjt168.com 2012年12月05日09:59 來源:新聞晚報 潘公凱/王雪瑛潘公凱主撰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回望中發現新的解釋框架
闡釋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歷程
 作者潘公凱
作者潘公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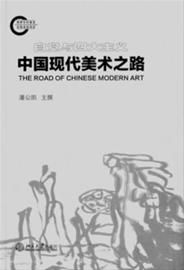 《中國現代美術之路》潘公凱主撰
《中國現代美術之路》潘公凱主撰
 潘公凱教授在創作
潘公凱教授在創作20世紀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既漫長又短暫的時代。整個國家經受了戰爭的創痛和巨大的變化與進步,而西潮又將其迅速卷入到統一的世界史視野中,中國美術現代性的歷史建構在全新的、變化著的社會情境中艱難進行。既有植入也有應對,既有融合也有抗衡,在變異中自覺地進行理論探索和藝術實踐,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美術現代性的中國美術現代性之路。如何看待和評價、理解和闡釋這段歷史,是研究中國現代美術首先面臨和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
著名中國畫家、美術史論家、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教授最近推出的力作 《中國現代美術之路》,以20世紀中國美術的性質判定作為中國現代性理論體系建構的起點,恰當、合理地闡釋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歷程,透視1840-1999年中國美術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的演進之路,就這部十年磨一劍完成的宏篇大作,本報記者王雪瑛與潘公凱教授開始了對話。
救亡圖強的民族意志和社會實踐,有力地塑造著中國近現代美術的線索和性格,由知識精英面對國情而產生的“自覺”出發,中國近現代美術表現為傳統出新、學習西方、中西融合、走向大眾等四種基本策略應對方式,即“四大主義”。 “四大主義”就是中國美術的現代主義。
編者語
王:潘老師我記得您說過,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術領域的經驗具有典型意義,美術領域的理論探索與其他領域的結合,有助于中國文化自主性的確立,并為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的現代性反思提供有益的視角、思路和參照。
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與西方或亞洲其他國家的美術史比較是不是有很大差異性?
潘:近代中國的現實境遇是決定近現代美術發展的根本動因。 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與西方或發達國家的美術創作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與亞洲其他國家也有不同。 20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革、社會動蕩所走過的曲折的道路,與中國人民在這個過程中所受到的苦難和所付出的代價,使得中國這段歷史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極具特殊性,也決定了整個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走向。中國美術的發展進程與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比西方近現代美術進程要明顯得多。
西方藝術史當中,尤其是20世紀西方現代美術發展史中,無論是馬蒂斯、畢加索還是波洛克、勞申伯,這些藝術家是有很大獨立性的,他們的創作風格、與藝術體制的關系、所受到的社會制約,跟中國藝術家所受到的來自于藝術本體之外的社會力量的左右和約束,不能同日而語。中國藝壇中即便是“為藝術而藝術”傾向比較濃厚的藝術家,都極大地受到了中國政治變革、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這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特點。
王:在對中國現代美術之路的探尋過程中,您是不是特別注重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中國問題的復雜性?
潘:對于20世紀中國美術的全局性判斷,要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中去尋找根據,藝術說到底只是其中的一個局部。我當然很重視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中國藝術問題的復雜性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傳統內部價值演進的困境與突圍,二是西方藝術移植過來以后的時空錯位,三是中西體系碰撞交融過程中所造成的價值碎裂,四是研究中本體論角度和社會學角度的復雜關系。它們不僅涉及形式語言問題,更與中西藝術體系不同、社會情境的巨大差異相關聯。
比如在西方顯得保守、過時的學院派寫實主義表現方式,在20世紀中國成為最先進的、最能為中國社會現實服務和最能解決問題的一套方法;而西方現代主義傾向于形式表現研究和個人感情抒發的手法,在中國卻難以施行。
同時,傳統和西方混交之后的復雜狀態,進一步造成了價值判斷的混亂。類似于“筆墨等于零”和“要守住筆墨的底線”的爭論,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價值判斷中的思想混亂。筆墨論建立在中國畫筆線的基礎上,而在西方藝術的主要流派當中,線是被否定的,從西畫體系和標準來看,筆墨當然等于零;同樣我們也可以站在中國水墨畫的角度來說“色彩等于零”。基于兩種不同標準、不同理論結構和價值立場的爭論,只能是各執一詞。
王:形式本體和社會功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在中國的情況很特殊,當社會功能的需求壓過了藝術本體的自律時,應該如何判斷一件藝術作品呢?
潘:一般來講,藝術作品或者說一個藝術體系,其本體性演進的前提是要跟短期的、眼前的、功利性的社會功能保持一定的距離和某種超然性,如果是緊緊綁在社會功能上,其自律性演進就無從說起。
在20世紀的中國,對于個人和國家、民族而言,生存問題比藝術問題更為基本、更為要緊,這是一個最為根本的事實。無論贊成與否,這一事實都是這樣發生并主導著藝術演進的。適應這種社會功能需求的作品應該怎么給予價值判斷,這可以說對藝術形式本體的單一性標準也構成了挑戰。
王:中國現實與問題的獨特性,中國美術的實際狀況是不是難以對應西方現代主義美術價值框架與審美語言?
潘:20世紀中國美術的實際狀況無法簡單對應西方現代主義美術價值框架,因為在西方價值框架的嚴格審視下,20世紀中國美術的大部分自然難以合乎“現代”的標準,無法成為西方標準衡量下的世界現代美術中的合法一員。
我認為,解決的辦法并不在于謀求得到世界主流話語的承認和接納,哪怕只是有限的承認和接納,這種不自信的做法絕非根本之道。關鍵還是要尋找切合自身現實和要求的新的價值框架和表達系統,切實明確自我的定位,對自己的歷史與現實能有一個自洽的解釋。因此,我們有必要,也有義務從自己的歷史與現實出發,拿出另外一種判定標準來。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現代”概念的含義,現代轉型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現代性研究的重心應該由模式轉換到事件,由研究已有的現代性模式轉換到研究突變傳遞中的現代性事件。課題引入了“未來視野”的概念,從未來視野中的人類巨變這個前瞻性思考入手,來獲取一種全新的思考角度,在對人類演進歷史的回望中發現新的解釋框架。
王:潘老師,1999年以來,您所主持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課題試圖由美術史出發理解現代性問題,從美術這一有限的人類精神與實踐領域中獲得更為宏觀和深刻的現代性基本問題的反思和嘗試性解答。
潘:整個人類正在經歷的轉變的總體面貌,比西方學者在現代性研究領域當中所描述的范圍和程度更為巨大,我們由此提出“現代化是人類巨變的序幕”的論斷,把人類現代進程整個地視為未來巨變的一個序幕。我們把現代性研究領域中關注的重心放到了未來,以此回望整個已經發生的變化,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整體地成為未來巨變的序幕。通觀現代轉型的進程,在未來巨變的這個序幕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突變。從最早突變的歐美地區向后發達地區進行傳遞,在短時期迅速形成連鎖突變的全球突變進程,這就是現代事件最基本的面貌。
王:在全球連鎖突變中,突變的傳遞成為您的課題研究的重點,而此過程最為關鍵的環節,就是作為繼發現代性標識的“自覺”。你的課題從位置和內容兩個方面對“自覺”做了界定。
潘:自覺既包括觀念意識層面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縱向上的自覺,也包括原發現代性的植入給傳統和社會所造成的沖擊和擠迫的橫向上的自覺,這種橫向自覺就是一種反思和應對。就原發地來說,更多的是縱向的自覺,而繼發地則兼有縱、橫兩種自覺,表現出更為復雜的局面。
作為一種反思性的意識并由此而產生出一系列策略應對,自覺就是一種現代性態度。以帶有社會心理學性質的“自覺”作為關鍵概念來梳理藝術史,而不是以藝術本體、形式語言的內在因素為標準,這是一種社會史與藝術史相結合的思路。
王:如何界定藝術家的創作是否符合現代性的標準? “自覺”是不是后發現代性的一種標識?
潘:“從事實出發”的方法論就是對近現代中國變革最基本的事實的正視和強調,并在中國變革的內在動力和外來壓力的復雜關系中找到“自覺”的棲身之處。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的曲折歷程和社會政治變革,都緊緊圍繞著落后挨打和救亡圖強而展開,落后挨打是起因,救亡圖強既是動力,也是民族意志,還是變革實踐。這一切就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最基本的事實和最大的社會歷史背景,對此有沒有清醒的意識,就表征著“自覺”的存在與否和深淺程度;對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最根本問題能否做出自覺回應并提出策略性路徑,就是藝術家的創作是否符合現代性的標準。
王:《中國現代美術之路》這個課題以未來視野、現代事件、連鎖突變等概念所構建的平臺為保障,使中國經驗能夠得到合理、公正的對待,希求為中國社會文化的未來打開自主性發展的廣闊空間。
潘:20世紀中國美術的藝術實踐,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政治變革緊緊相連。救亡圖強的民族意志和社會實踐,有力地塑造著中國近現代美術的線索和性格,由知識精英面對國情而產生的“自覺”出發,中國近現代美術表現為傳統出新、學習西方、中西融合、走向大眾等四種基本策略應對方式,即“四大主義”。以“自覺”作為評判繼發現代性的標識,以“四大主義”的構架來反映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基本面貌,這就是課題所希望完成的正名:“四大主義”就是中國美術的現代主義。
王:20世紀中國美術在整體上是否具有現代性這一問題,在剛過去的30年中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也是中國美術界的基本問題?
潘:在互聯網時代的今日,中國已經整體地融入世界,而且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已被裹挾到了歷史劇變的洪流之中,這一問題也已經轉變為另一個基本問題:如何認識全球現代性的傳遞及變異與人類巨變的大趨勢之間的復雜關系。出于對近現代中華民族為救國圖強所付出的代價的追思。我們需要一個精神家園!整個人類需要一個和諧共生的精神家園!正如同筆者在24年前所預見的那樣:一種綠色的繪畫,綠色的藝術,綠色的人類生存方式。這才是未來的藝術家們和理論家們所應該共同思考、策劃、探索和實踐的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